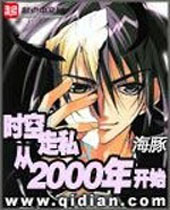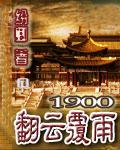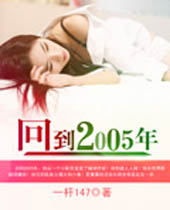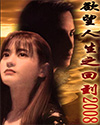当代-2005年第2期-第2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更令人震撼的是时间,时间比你想像的有力得多、无情得多,时间主宰着我们,像暴君。一位研究者曾经评论我的作品常常以空间的转移来写时间。是的,到日本使我想起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度过的。到新疆使我想起中年与壮年。而俄罗斯呢,一到俄罗斯青年时代的记忆就纷涌而来,浑若不胜思。
朋友告诉我,老G与这位俄罗斯女诗人的爱情是不可能实现的,双方政府都有禁令,后来,两国关系又敌对成了那个样子。所以,虽然八十年代初期老G曾经供职于我驻苏大使馆,也不可能与之见面,直到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老G费了老大的劲终于找到了女诗人。
还说什么呢?恩怨情仇,藕断丝连。又是近邻,又是第三国际,又是共同的理念,牢不可破、万古长青……本是同根生,这是历史?这是命运?这是天意?你永远不可能非常理智非常冷静非常旁观地谈这个“外国”,看这个国家。你为她付出了太多的爱与不爱,希望与失望,梦迷与梦醒,欢乐、悲哀与恐惧……这占据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上一代人特别是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一生。而后,错错错,莫莫莫;长已已,永恻恻。你老了,去了,她也老了。
七 波罗的海的夕阳
这次还去了圣彼得堡。这是这个城市的古老名称,源于耶稣的十二个圣徒之一的圣彼得。后来改成彼得格勒,是为了纪念彼得一世即力行新政的彼得大帝。十月革命后定名为列宁格勒,当然是为了永记列宁。现在又改了回去。城市的名字改了,但是城市所处的州的名称没有改,仍是列宁格勒州。而莫斯科的通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名为列宁格勒火车站。想洗净一段重要的,震动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震动了本国也改变了本国的历史谈何容易?当我与该城的汉学家们座谈时,一位女学者问我:“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改革得太慢了?”我说:“没有啊,你们连城市的名字都改了呀……”有同行者以为我语带嘲讽,实无此意!我怎么会觉得他们慢呢?明明太急切了嘛。
我不想再写这里的瓦河、冬宫、阿弗洛尔巡洋舰、购自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也不再写这里的大街了,有一首民歌叫做《沿着彼得大街》,抒发一个喝醉了酒的马车夫赶车的情景,歌曲里有车夫吆喝马的叫声。是我记错了吗?当我问导游哪里是彼得大街时,导游表示不知道。(后来才听说,这是莫斯科的彼得大街。)
感谢导游带我们去“木木餐厅”用饭,餐厅门口有屠格涅夫的小说中的狗“木木”的雕像,饭后老板送给我第一版“木木”的复制本。后来我们又到柴可夫斯基与科学院餐馆用餐。就冲这些餐馆名称也令人钦佩。彼得堡是全城性的博物馆,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屠格涅夫的坟墓都在这里。
最难忘的是11月21日我们碰到了风雪,可能没有普希金小说里描写的“暴风雪”那样激烈,但已经可观。风是白色的,雪是散漫无形的,风成了雪的力量,雪成了风的形体。街道与巨石建筑也在瞬间出现了白色,剩下的河流显得格外黝黑。我在风雪中踉踉跄跄地奔向也是普希金描写过的“青铜骑士”——彼得大帝铜像前留影纪念。那里有交通警察,近处不得停车。咯哒一声,摄影完毕,胶片也没有了。
由于当天晚上还要乘车返莫斯科,我们回旅馆休息。天昏地暗,疲劳的我们迅即躺下,合上眼睛。突然,一片火光使我惊醒,满室通红。睁开眼,得知红光来自窗户。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才知道天忽然放晴,夕阳就停泊在波罗的海上,夕阳傲视着我们,光芒四射,仪态万方,霞光千道。
我们住在波罗的海宫,隔窗望去就是波罗的海,芬兰湾。而过去,芬兰湾的风光只在列宾的油画里见过。现在看出去,已经没有当年的野生水生植物,却多了一个灯光昼夜眨眼的海滨夜总会。远处也有灯火,我开始以为是芬兰呢,后来导游告诉我那边是喀琅施塔得岛。这个岛的名称我也不陌生,因为苏联“七彩”电影《难忘的一九一九》中有这个岛的水兵叛变的故事,有一个镜头是斯大林乘着摩托快艇破浪前行,前来解决水兵叛变问题,像圣者下凡一样,一时全电影院的观众欢声雷动。
很快,夕阳落入波罗的海,天立刻黑下来,阴云重新弥漫,风雪再次接续。
谢谢你,波罗的海的夕阳,你是为了让我们短暂地欣赏一下,让圣彼得堡骄傲一下,也让太阳底下的人敬服一下才特意冲破乌云,一露真容。波罗的海的夕阳是灵验的,法西斯硬是拿不下这个城市来,历史早已证明了。
八 俄罗斯永在
这次去俄罗斯是应俄驻远东全权代表、俄中委员会俄方主席的邀请进行友好访问而进行的。而首先倡议这一安排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他们要利用此行我在莫斯科之际举行授予我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
仪式上,所长季塔连柯有两个提问:一个是“您是否准备为世界人民的和平、友好而继续努力?”一个是“……为科学的发展繁荣而继续努力?”我都回答了“是的”,然后将博士证书交到了我手里。
这让我想起了基督教的婚姻仪式与法庭上作证前的宣誓;还有来自苏联,而中国一样的少先队的誓言:“时刻准备着。”人们是需要许诺的,中国古人称之为“然诺”,李白的“古风”里盛赞鲁仲连的一诺千金的精神。我也应当记住这两项肯定的答复。
仪式后是我的讲演与学者们的发言。然后是午宴。在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后面,我致了答词。我说:“苏联,俄罗斯,莫斯科是我青年时代的梦。现在,苏联没有了,我的梦想已经比青年时期发展成熟了很多,但是,俄罗斯还在,莫斯科还在,中俄人民的友谊还在,而且一切会更加繁荣和美丽。”
我相信我的话打动了俄罗斯朋友,这从他们的目光的突然闪亮中完全可以看出来。
她们的歌德
□ 虎头
“谁是歌德?”
这肯定是全世界最多余的问题。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一生跨越德国文学史最为壮观的“狂飙突进”、“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三大文学潮流,不仅是“古典主义盛世”一骑绝尘的旗手,更是德国文学史璀璨星空中当之无愧的北斗。在世界文学史上,歌德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并称世界四大文豪。
作家,自然以作品论胜负。歌德一生写下52部诗文集、13部科学著作、15部日记、49部书信,共计129部,堪称才气横溢,卷帙浩繁。寻常人休说研究,就是读一遍,皓首也未必就能穷经。
歌德的伟大,还远远超越文学。恩格斯盛赞“歌德是最伟大的德国人”。著名哲学家谢林走得更远:“只要歌德在世,德国就非孤苦伶仃、一贫如洗;尽管它虚弱、破碎,但它在精神上依然伟大、富有和坚强。”
尼采在《人性,过于人性的》中说:“歌德不仅善良伟大,而且自成一种文化——在德国人的历史上,歌德是一个后无来者的插曲(Zwischenfall)。”尼采本人生于歌德之后,他说歌德“后无来者”,即是承认自己不如歌德。作为德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顶级狂人,我不记得尼采对第二个人有过如此称许。
要言之:歌德,是德国贵为世界列强的精神领袖。
下一个问题大概是全世界最难回答的问题:
谁是歌德的女人?
女人是歌德这部人生盛装大戏中的主角,是他所有鲜活生动的作品源头的那道清泉,也是点燃他写作激情原子弹的那一小块儿高爆炸药。女人,既是他的海水又是他的火焰。歌德一生爱情生活之绚丽多姿,与他作品之烟波浩淼,的确是相映成趣。全世界研究歌德的文章汗牛充栋,歌德的129部作品多以自己的爱情生活为背景,且有他亲笔所写15卷日记可供索引,饶是如此,到底歌德的女人有多少,她们都是谁,二十一世纪都过4年了,在德国文学研究史上,还是一个歌德巴赫猜想。我非歌德研究专家,当然更加数不清楚。只歌德的初恋,有案可稽:1764年法德七月战争结束,法军从法兰克福撤退之后,年仅十三岁的他,爱上了邻家女格莉琴(Gretchen)。歌德的初恋是典型的剃头挑子——一头儿热,终被格莉琴笑指为“姐弟关系”。歌德的初恋完全是青春期灵的狂想,与肉无涉。有些文章望文生义,公然说歌德与格莉琴“初尝禁果”,其实不过暴露了自己“看见白胳膊,想到全裸体”的传统狗仔文人嘴脸。
一篇文章,根本不可能尽数歌德所有的女人。那将是一部长篇。
但有三个女人,却是任何涉及《歌德》这部人类历史传奇的文章都不得不说的故事。
第一个是夏露笛(Charlotte von Stein)。
在歌德的所有女人中,夏露笛堪称歌德的精神教母,歌德可以说是踏着她的灵魂和肉体走出了“狂飙突进”的青年时期,继而登上了千古不倒的古典主义文学神坛。
纵观世界文学史,歌德可称举世罕见的幸福作家:出身世家豪门,少年一举成名,青年轻松入仕,成年盘踞要职,端的是美女与宴会齐飞,绯闻共作品不断,人到中年即誉满欧洲,步入老年更成为“德国历史上惟一一个还未辞世即已成神的人”(Jean Paul)。
但是,无论大小,每一粒露珠都注定要映射阳光的七彩。如果我们认为歌德的人生只有欢乐没有受挫,那我们的心智就还未成熟。作为长时期盘旋于人世巅峰的大天才,歌德的世界其实有着无数我们并不知晓的挫折、黑暗、沮丧、痛苦、失败和孤独。而女人,就是他生命这些无边暗夜中永恒的星光。
1775年,26岁的歌德带着《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巨大光环应18岁的魏玛公国君主奥古斯特大公之邀到达德国东部的魏玛。那时,33岁的夏露笛正处于一个女人水丰草肥的成熟季节。歌德出身豪门、饮誉欧洲,且相貌堂堂,英俊潇洒,正是众神争相眷顾的天之骄子。他人虽年少,却已曾经沧海,有过无数次惊天动地的恋爱,经过法兰克福、莱比锡、斯特拉斯堡和威茨拉(Wetzlar)一系列激情澎湃的人生驿站,他需要一个安静的边城来梳理自己狂放不羁的心境。
很多人称夏露笛为歌德生命中的“贵妇”,因为她丈夫就是奥古斯特大公的掌马大臣,所以她是正宗的宫廷命妇。但在漫长的婚后生活中,她丈夫不是陪大公吃饭就是陪大公出行,剩下的些许时间还要侍弄他的那些马。夏露笛虽然才华出众,精通法语,喜好跳舞、女工、钢琴、绘画和做诗,却始终无法赢得丈夫的注目和欣赏。33岁的夏露笛,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就此在孤独和寂寞中无声无息枯萎的整个过程。
如果齐默曼医生——她与歌德共同的朋友——没有把歌德介绍给她。
《少年维特之烦恼》风行德意志,夏露笛自然也看过。她写信要求齐默曼把自己介绍给歌德。后者马上将歌德的剪影寄给她,并写道:“您想让我谈谈歌德?您想见见他?我马上就向您详细报告。不过,可怜的女友,您这完全是轻举妄动。您想见他,可您根本不知道这个可爱的、令人神魂颠倒的男人对您有多危险!”
警告是好奇之母。夏露笛对歌德更加好奇。这齐默曼虽是男人,却深得媒婆三昧。他转身又把夏露笛的剪影给歌德看,也挑起了后者的好奇心。
所以,夏露笛与歌德的故事,始于“剪影剧”。
歌德在夏露笛剪影旁边的空白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看这世界如何倒映在这个灵魂中,将是一出精彩的戏剧。这灵魂看见了世界的本质。不过,它是通过爱情看见的。所以,更主要的印象是温情。”齐默曼写信把这些话告诉了夏露笛,同时又详细向歌德描述了夏露笛。据说歌德因此三夜没睡成觉。
尽管有齐默曼医生的十足铺垫,尽管到魏玛之后的前十年中歌德几乎就住在夏露笛家,夏露笛与歌德却并未一见钟情。歌德到魏玛后不久,夏露笛曾写信给齐默曼说:“我觉得,我和歌德永远也不会成为朋友。”歌德那时一直跟18岁的奥古斯特耽于冶游。直到一年之后,夏露笛都不相信他会留在魏玛这个弹丸边城。魏玛虽小,当时欧洲小国那些尔虞我诈的政治闹剧却一应皆全。歌德在他的作品《托夸多·塔索》中多次描写了魏玛的宫廷斗争,而书中的王妃,据说就是以夏露笛为蓝本的。
歌德对夏露笛的兴趣,产生于一年之后。
在歌德的所有爱情生活中,他都是主动的。同样,这一次夏露笛也是被动的,刚开始时甚至是婉拒和逃避的。作为一个宫廷命妇,跟歌德这样的疯狂作家成为情人,夏露笛有着诸多疑虑。她不能逆料的是,她的婉拒与逃避,却导致了歌德加倍狂热的追求。夏露笛很长时间都不让歌德以“你”相称,并且拒绝与歌德近距离接触。然而歌德的爱情之火却正因为如此而愈烧愈旺。1776年5月,歌德写信给夏露笛说:“你是对的,你想让我成为圣人。也就是说,你要把我从你的心中剜去。可尽管你是神圣的,但我拒绝让你成为圣人。我不想折磨我自己,而这就是我对自己最大的折磨。”同年七月他又写道:“我又陷入了命定的忧伤之中。我真想大声地嘲笑自己:每当我爱上一个女人时,她一定不爱我。”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让歌德如此狂热的夏露笛,长得却极一般,是个典型的“第二眼美女”。她不仅比歌德年长七岁,并且当时已有七个孩子(后来仅存活三个),距离窈窕淑女至少五十公里。可曾经无数美女的歌德却在1781年3月13日的信中写道:“我不想再说什么我与你永不分开,什么高山大川也不能让我却步。我只希望世界上能有什么誓言或者圣事可以让我在尘世中和法律上完全属于你。那才是对我最有价值的事情。”
夏露笛再次证明了一句话: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