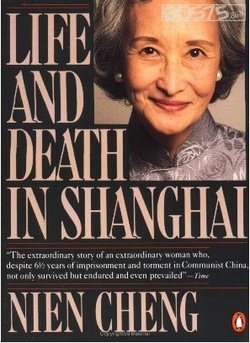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5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说得声音最高的是梅佐贤。
“幸亏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来一个三反运动,整整这些干部,再不整,干部的官僚架子更不得了,恐怕眼睛都要长到头顶上去了。”
“干部么,不可一概而论。”潘信诚伸出手来,指着徐义德,以他丰富的历世经验分析地说,“据我看,干部有三类:上级、中级、下级。一般的是上级好,中级差,下级糟。你刚才说的,是属于下级的干部,自然很糟糕。上级,那是无话可说。他们埋头苦干,艰苦朴素;办事认真,丝毫不苟;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你和他们在一道,感觉不到他是个大首长。我五十多年来,见过不少市面,接触过各式各样的大人物,从没有见过像中共这样的首长,他们可一点官僚架子也没有。”
“信老分析的也有道理,但是中、下级干部不能一概而论。”马慕韩想起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早上,他看到解放军睡在南京路两旁马路上的情景,叫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也根本没有听见过军队的纪律这样严明,入城以后,怕惊动老百姓,连门也不敲一下,就睡在马路上过夜,那些长官和士兵一样的睡在水门汀上。这样的好部队,老百姓哪能不喜爱?他不同意潘信诚对干部那种分类法,提出了异议,“拿解放军来说,进城睡在南京路上,没有惊动一家老百姓,这不能说‘糟’吧?”
“那是部队,那些干部真是好,无话可说。”潘信诚也同意这一点,“我不晓得见过多少部队,北洋军阀的也好,国民党的也好,英国美国的也好,可是从来没有像解放车这样好的部队,那么守纪律,讲道理,叫人见了一点儿也不怕,真是古今中外少有的部队。”
潘信诚并没有正面回答马慕韩的不同意见,马慕韩听出来他的意思:一般干部吗,还是他的意思:中级差,下级糟。马慕韩第一次正式见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是在外滩中国银行的楼上。那是上海解放没多久,陈毅市长召集工商界的人士举行座谈会,他心中有一种新鲜的异样的感觉:干部不论大小,一律穿着布衣服,有的穿黄色卡其布的军装,有的穿灰布的人民装。猛一下见到,叫你分不出哪一个是高级干部,哪一个是下级干部。上海解放快三年了,他们还是穿着朴素的布衣,生活也很节省,见了人和和气气,一点架子也没有。他最初觉得他们在农村待惯了,进城以后,一定会变,现在快三年了,可是还没有变。原来以为他们是所谓“土包子”,对于军事和农村工作有一套办法,城市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就不一定能行,上海许多公共事业和一些大型工厂,军管会接管以后,派去的那些军事代表和厂长这些人,摸索一个时期之后,居然也熟悉了。这样一来,他对干部看法有些改变:他们不单是生活朴素,态度和蔼,平等待人,而且还有本事。国家大事交在这样的人手里,那是大有希望的,会给中国人出一口气。他对潘信诚说:
“我虽然年纪轻,接触到政府的干部也不多,但不论上级也好,中级也好,下级也好,我觉得他们能力很强,经验丰富,尤其是生活朴素,不爱钱财,确实叫人佩服。他们那个完完全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真是天下第一!对我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
“我不大同意慕韩兄的说法。”徐义德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梅佐贤还代他送了两百万块钱给驻厂员方宇,怎么能说是干部不爱钱财呢?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生活朴素是真的,不爱钱财,我看不见得。钱,谁不爱?如果照信老的分类法来说,也有三种人:一种人是心里爱嘴上也爱;一种是心里爱嘴上不爱;第三种是心里不爱嘴上也不爱。现在的干部多数是第二种,如果你送上钱去,保证不让第二个人晓得,你看他要不要?我徐义德担保:他一定要。”
马慕韩摇摇头:
“德公,你这个说法,要考虑。”
“我有亲身的经验。”徐义德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看了梅佐贤一眼。
梅佐贤懂得他指的是方宇。梅佐贤说:
“我同意徐总经理的意见。”
“就是有亲身的经验,也不能以局部代替全部,更不能以个人的经验下结论。我们要从全面看问题,要从历史发展看问题,要比较的看问题……”
马慕韩在上海解放后就不断买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看,学了不少新知识。在工商界朋友当中,他是比较有点修养的。他这几个看问题的方法把徐义德说得哑口无言。他心里不服,可是弄不清那些新名词,有理也说不出。他不言语,只是对马慕韩一个劲地摇头,表示不同意。朱延年从马慕韩的沙发扶手上站了起来,向大家点了一点头,态度很谦虚,语气却坚定,说:
“借这个机会,我想向诸位报告报告福佑药房的具体情况……”
马慕韩一听到朱延年要报告福佑药房的情况,马上就预感到他又要大煞风景,在林宛芝三十大庆的日子来大力募股了。他厌恶地盯了朱延年一眼,想离开他远一点,书房里没有一个空座位,突然离开朱延年也容易引起旁人的诧异。他不动声色,把头转过去,注视挂在墙上的那幅《绔扇仕女图》。
朱延年没有注意马慕韩的表情,他兴致勃勃地说:
“福佑药房复业不久,从苏北行署卫生处来了一位张科长,刚开头,连根香烟也不肯抽我们的,吃饭更不必说了。我们送过去一双黑皮鞋和一套深灰色的哔叽人民装,起先一定不要,劝他先穿了再说,到后来就一直穿到苏北去了。送他礼物不肯要,我们把它放到火车的行李架上,他也带到苏北去了。最初不敢当面送饯,只说是借点钱给他零用,他就放手化用了。第二次,我们又送了一些钱放在他房间里,他化了,从来一字不提。到娱乐场所吧,比方讲跳舞厅,开头也不肯去,带他去一二次,以后就自动去了,跳完了,就把一个很漂亮的舞女——叫徐爱卿的带到旅馆去了。公家机关的干部总是这一套,心里爱钱嘴上不敢爱。以后,我们摸清了这个底细,不管他同意不同意,你照办,坚持做下去,只要不让人晓得,他们最后总是接受的。十拿九稳,没有一个干部不是这样的。”
徐义德的嘴上露出了笑容,说:
“我说的,对吧?慕韩兄。”
马慕韩听见朱延年并不说募股的事,而是谈了张科长的例子,这些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和兴趣。他没有正面回答徐义德的话,转过脸来,对朱延年说:
“你谈下去。”
朱延年见自己的一番谈话引起了马慕韩的兴趣,他扬起眉头,得意忘形地说:
“哪个干部到了我们福佑药房,总逃不出我朱延年的手。不但生意一定是给福佑做下来,而且人也会慢慢变成福佑药房的。他们自己单位的生意一定给福佑做自不必说,就是他们有联系的别的单位,也会介绍来的。每次介绍生意来,我也不亏待经手人,不是寄点钱去,就是送点礼物去。他们要办货,上哪一家都是一样,到福佑来,自己有油水,何乐而不为呢?老实说,我们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任你是哪一个干部来,只要跨进福佑的门,思想就一定会得到改造。因此,我们福佑的生意越做越大,经常联系的客户几乎遍及全国,有一千九百四十二家,今年六月份的营业额曾达到三十六个亿,现在还在发展……”
马慕韩听到这里生怕他又要拉到募股上头去,当着这些朋友的面,再要拉他入股,他是很难拒绝了。他连忙插上去说:
“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那么,你是所长了。”“不敢当,不敢当。”朱延年谦虚地说,“我不过在这方面多出点主意,具体的事情还是靠伙计们去做。”
韩云程工程师不大接触工商界的这些人物,平日尽在数字里过日子,今天听了朱延年的宏论,他暗自吃了一惊,深深感到自己晓得的事体太少了。拿朱延年和徐义德一比,显得徐义德大为逊色了。他感叹地说:
“想不到福佑药房做买卖还有这一手……”
柳惠光早听说福佑招待客户的一些情形,但是没有今天这般具体。早一会儿和马慕韩、韩云程一道听朱延年谈福佑药房发达的情形,当时的嫉妒现在已变为轻视,甚至是不屑一顾了。这样做法,风险太大,就是赚钱,将来也会出毛病的。他不再嫉妒福佑药房,内心安于利华药房的营业情况了。
他听到韩云程的感叹之词,接上去说:
“我们延年兄的花样经多的很,别人想不到的事体,他都做得出。”
这几句话说得朱延年心里不大舒服,在座的只有柳惠光知道他的底细最清楚,怕他再说,连忙顶过去:
“别给我高帽子戴,惠光兄,你也不推板。”
徐义德的意见得到朱延年的有力的支持,他指着挂在上沿墙壁上那幅《绔扇仕女图》说:
“金钱与美人这两关,谁也逃不过。你们看看这是一幅唐朝的古画,这几位宫女画得多美丽!谁见了能不动心呢?干部跳舞当然找最漂亮的舞女跳。有了金钱和美人,你要干部做啥,他不肯,才怪哩。”
潘信诚闭目遐思,想起他从香港回到上海,曾经看到上海解放初期英文《字林西报》的一篇社论,感慨万端地说:
“唉!英国人是有眼光……”
大家对金钱与美人这两个问题正有兴趣的时候,忽然听潘信诚说了这么一句,大家都以莫名其妙的眼光注视着潘信诚。宋其文问:
“信老,你怎么忽然岔到英国人身上去了?这和我们的谈话内容,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啊!”
“大有关系。”潘信诚说,“上海解放初期,《字林西报》有篇社论,说上海是一个大染缸,不管你啥政党来,都要变色的。那意思是说,就是共产党来,也要被上海改变的,也要变色的。我听了延年老弟的一番话,心里很有感触,要修正我刚才的看法。以我五十多年的经验来说,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当哪一派得势上了台,开头都是勤勤恳恳朴朴素素地办事,总是得人心的。可是,不久,政权建立起来,生活富裕了,过的写意了,就起了变化,慢慢失去了人心。我们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了百把年,统治阶级也不争气,尽和帝国主义勾结,一点可怜的民族工业总抬不起头来,老大的中国富强不起来,也独立不起来。自己捧着一个金饭碗在人家面前讨饭吃。我原先以为共产党不同,想不到上海解放还不到三年,干部已经起了变化。上海这染缸,……这可怕的染缸……”潘信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这一声叹息,使得大家都闭住了嘴,不知道说啥是好。书房里静静的,草地上暮色苍茫,打羽毛球的大人和孩子的叫喊声低下去,有些人就走进客厅里来。楼上徐守仁已经把电唱机关了,再也听不见世纪末的美国爵士音乐。客厅里的乱哄哄的人声比刚才更高。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中,稍为注意一下,可以听到西客厅里有人在唱《捉放曹》:“将此贼好一比井底之蛙……”此外,还可以听到搬动桌椅和放置筷子碗碟的音响……
梅佐贤坐在书房门口那边,伸过手去把电灯扭开。灯光照耀着古色古香的书房,给潘信诚叹息了一声因而沉闷起来的空气,让电灯一照,大家情绪又仿佛活跃了起来。肃静中,马慕韩开口,打破了沉默:
“信老,你是用旧眼光看新社会。我不同意。你说的情形,过去确是如此,那是反动统治阶级,改朝换代,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他们一定要起变化的,有的变化迟些,有的变化早些,但是一定要变化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不会的。”
“这件事,慕韩兄,你可不能给人打包票。”徐义德完全同意潘信诚的意见。
“不是我要给人家打包票,共产党硬是和别的党派不同么。”
“何以见得?”潘信诚不慌不忙地问。
“自然有道理,我亲眼看见的啊。”马慕韩回忆地说,他仿佛又回到朝鲜前线,“在朝鲜的志愿军,就是原来的解放军,他们住在坑道里,有时连水也喝不上,用雪化成水来喝,不怕多么强烈的炮火,个个争先恐后,受了伤也不下火线。过去只听说解放军生活艰苦,打仗勇敢,我却没见过。我在朝鲜前线慰劳,可是亲眼目睹的,他们一点也没有变。”
“共产党的军队确实管教的严。不过,军队在城市里住久了,也很难说。”潘信诚还是相信《字林西报》的论调。
“不,信老,我见到的志愿军,有的是从上海开去的,他们在上海驻防过。”
“哦?”潘信诚感到有点惊奇。
“信老担心的很对,一般干部就很难说了,有些干部,我也是亲眼看见的。”徐义德支持潘信诚的看法。
“当然,十个指头有长短,不能说每一个干部都很好,陈市长在一次会上,也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共产党早注意这个问题,可以防止,因为共产党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也就是毛主席说的每天要洗洗脸,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腐化的。”
冯永祥给朱延年“将”了一“军”之后,一直保持着沉默,他怕露底。马慕韩提到陈市长,他立刻支持他,表示自己也了解这件事,大声地说:
“慕韩兄的话对,我也听陈市长这么说的。我相信共产党不会腐化,有毛主席领导一定不会腐化,绝对不会腐化。”“现在还难说,”潘信诚的口气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走着瞧吧。我的眼光也许旧了一点,不过,我是一番好意,但愿共产党能把中国弄好。”
马慕韩坚持他的意见,说:
“目前正在进行三反运动,事实说明共产党不会腐化。这个运动就是为了挽救那些贪污、腐化、浪费的干部的。”
一提到整干部,徐义德的兴趣就来了。他说:
“对,这些官僚主义的干部是要整……”
徐义德的话还没有讲完,忽的,冲进来一个穿黄皮茄克的青年,乌而发亮的头发向前飞起。他大步跨到徐义德的面前,像个小孩子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