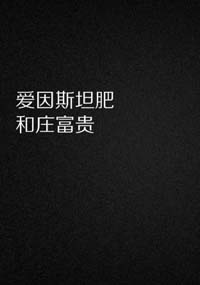爱因斯坦传 作者:聂运伟-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星球可以证明他的正确和伟大。爱因斯坦的理论唤起了人们心理深层的波澜。古往今来,男女老少都对星球和光线有着亘古不变的惊异和畏惧。人们的梦中,出现得最多的是遥远的星辰日月,人类的神话中,出现得最多的也是遥远的星辰日月。人们不理解,无法控制的对象就是神秘向往的对象。如今,有人来解释,有人来诉说。懂与不懂,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它和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愫有了共振,有了牵连。
“相对论热”引发的条件还有当时的文化心理背景。
《泰晤士》报记者就相对论问题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天体力学教授普尔,普尔说:
“过去几年整个世界处于骚动不安之中,精神和物质均如此。物质的骚动不安,如战争、罢工、布尔什维克起义等可见事件,实际上是以精神深处的骚动为基础的,具有世界性……。这种同样的动乱精神已侵蚀了科学……”
还有人解释:
“还有一个看来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现象是一位德国学者预言的,而英国的一些学者验证了它。不久前还属于两个敌对营垒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们又开始一道工作了。或许,这就是新的时代、和平时代的一个开端?据我看来,人们向往和平是爱因斯坦的荣誉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爱因斯坦一下成为世人崇拜的偶像,他的传奇故事有了普遍的世界性。请看德国外交部收到的各国对爱因斯坦访问的报告:
1920年6月,奥斯陆:“爱因斯坦的演讲受到公众和报界异乎寻常的好评”。
1920年6月,哥本哈根:“近来,所有不同观点的报纸均发表长篇文章和访问记,强调爱因斯坦的重大意义,‘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伟人’”。
1922年4月,巴黎:“……轰动一时的新闻是,首都的自以为学识高深的人都不愿放过机会”。
1923年1月,东京:“当爱因斯坦到达东站时,那里人群密集,连警察也无力应付这些危险的人群……,菊花节那天,天皇、摄政王、王子王孙都没有举行招待会,一切都围绕爱因斯坦转”。
1923年3月,新德里:“到处充满着极大的热情……报纸每天都设专栏报道他的行踪……”。
1925年6月,蒙得维的亚:“他是首都谈话的话题,他成为头条新闻达整整一星期之久……”。
“相对论热”使得爱因斯坦的每次讲演都是人山人海,讲演大厅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听众往往有上千人。要想知道爱因斯坦教授在哪里作报告,只要看一下这时人们朝哪里奔跑,就知道了。听众中,凑热闹、赶时髦的人当然是大多数,而且有不少外国游客。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人作了如下描述:
“报告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珍贵袭皮大衣的美国、英国阔太太,她们手举望远镜,仔仔细细地端祥着这位学者。”
报告一结束,这些外国游客就冲向黑板,为了抢夺这位红极一时的学者写字留下的粉笔头。他们想把这些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到处炫耀。
人们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到了顶点。1921年6月13日,霍尔丹爵士把爱因斯坦介绍给英国皇家学院。那是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英国,住在海尔登爵士家里。一进爵士家,海尔登的女儿一知道站在眼前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时,竟激动得昏了过去。
海尔登爵士后来回忆爱因斯坦的英国之行,说:
“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不希望自己被人注意,但是那无庸置疑的天才却驱使着他,不许他有片刻的休息。”
★ 名誉后面的苦恼
在举世瞩目的荣誉面前,爱因斯坦没有道理不高兴,可荣誉带给他更多的是苦恼。莫什考夫斯基说:
“荣誉也要求作出牺牲,而如果可以谈到追逐荣誉的话,那么在这种追逐中,在所有的场合中,爱因斯坦扮演的都是猎获物,而不是狩猎者。”
从1919年11月9日早晨起,爱因斯坦就成了新闻界与公众的“猎获物”。
记者们一拨又一拨地揿响了哈贝兰大街5号的门铃。谈话、采访、拍照、没完没了的追问、故作深刻的对话、添油加醋的渲染,还有廉价的吹捧,把爱因斯坦全弄糊涂了,也弄得紧张万分。
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邮递员;
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那真是可怕的场景!
每天早班邮件一到,围攻就开始了。他会收到成百上千封讨照片、讨亲笔签名的信。许多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收”几个大字。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有人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有人请他说明时间怎么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长缩短。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小问题,只要教授花费一分钟时间回答。也有请求帮助的信:一个青年学生没有考上大学,请教授在教育部说说情;一个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被埋没了,请教授在科学院里讲几句话;一位年轻妇女作为“天文观察者”自荐效力;一家雪茄烟厂厂主告诉他已把自己工厂生产的一种新型雪茄取名为“相对性”……
艾尔莎成了爱因斯坦的收发秘书。她每天得把信件分类,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复信,余下的交给爱因斯坦过目。这项工作要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时甚至整个晚上。
尽管艾尔莎已筛选过,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脑筋。在1920年,爱因斯坦说:
“我从不擅长说‘不’。但现在,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询间,邀请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邮递员变成了魔鬼,对我大声喝斥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掷来,就因为我对过去的信件未作答复。
“加上我的母亲有病,但为我的‘伟大时刻’即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会议又来了。简而言之,我差不多是只会作简单反射运动的一捆东西了。”
聪明的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对付信件的办法:请慈善机关代办讨照片和签名的信。谁捐了钱,就能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签名照片。这真是一举三得:既满足了那种名人崇拜迷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更节省了自己的时间。至于讨论问题和请求帮助的信,爱因斯坦都亲自回信,实在忙不过来,就请艾尔莎的大女儿帮忙。
麻烦的是找上门来的人:摄影家、画家、雕刻家,各个行当的艺术家都来找他。已经成名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作品目录,尚未成名的是为了借爱因斯坦的大名去闯出自己的名誉。亏得艾尔莎的能耐,既客气优雅,又不动声色地推掉丁一件件麻烦事,挡走了一位又一位客人。碰到那些能泡能磨的客人,艾尔莎也有挡不住的时候。每逢此时,爱因斯坦也只好亲自到客厅里来逢场作戏了。
全世界都在谈相对论。名式各样的哲学家、科学评论家、打油诗人、漫画家、无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爱因斯坦热、相对论热中推波助澜。
有人是正儿八经地谈,有人在瞎扯淡,更多的人是在赶时髦。
一个美国富翁出五千美元巨额赏金,征求一篇三千字的介绍相对论的文章。市场上的烟贩子在叫卖“相对论牌”香烟和“爱因斯坦式”雪茄。英国的一家报上登出一幅漫画,把相对论和英国人特别爱好的侦探故事结合起来了:
一个大侦探手拿电筒,照出一束强光,光线绕过两个大弯,落到正在撬保险柜的窃贼身上。漫画的标题是:
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
一位打油诗人描写相对论的尺缩效应:
杰克小位剑术精,
出刺迅捷如流星,
不料空间一收缩,
长剑变成小铁钉。
这已经是一场闹剧了。严肃的物理学理论竟被新闻媒体煽起的热浪冲击得面目全非。爱因斯坦深知人们在崇敬自己的同时,又是在填补他们自身的无知与无聊。和人家的赞誉对着干,板起面孔,作高深状?天性善良的爱因斯坦做不出来;顺水推舟,在人们浅薄的赞誉中欣欣然,乐融融?爱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会这么低。
怎么办呢?
盲目崇拜名人的风尚,是人类社会留下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有了崇拜,就有了时髦的风尚。
爱因斯坦式的幽默与诙谐又一次派上了用场。有一次,在一位渴望获得签名的年轻太太的纪念册上,爱因斯坦写下这样叫人哭笑不得的“诗”:
小牛和山羊在菜园里游戏,
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和它们同类。
又有一次,他写道:
我走到那里,我站在这里,
总看到眼前有一张我的画像——
在写字台上,在墙壁上,
在围着脖子的黑丝带上。
男男女女怀着仰慕的神情,
来索取签名留念。
人人都从那可敬的好小子那里,
讨到一个带钩的签名。
有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时刻我却想:
是我自己已经发疯,
还是我误入了牛羊群中?
爱开玩笑的爱因斯坦,写下如此打油诗之后,心里总又有些后悔,怕伤了人家的感情。好在名人效应总使得崇拜者们诚惶诚恐。他们即使受到爱因斯坦的讽刺,仍觉得是一种难得的荣光,还喜不自禁地说:
“看,这才是真正的名人!平常人谁有这份幽默?”
出名后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是爱因斯坦最为头痛的事。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人人彬彬有礼,说话温文尔雅,衣着得体大方。从政治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他们都会谈一点,可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场合,附庸风雅地向先生们微笑致意,向夫人们说两句情趣隽永的俏皮话,都让爱因斯坦头皮发麻。他嗯嗯地随口应答一切应酬,和蔼可亲地面对一切提问,但就是心不在焉,由此而获得一种传闻,即“爱因斯坦教授那种可爱的心不在焉”。
爱因斯坦的离群索居,多半是研究对象的超越琐俗人世而养成的。其实在生活中,爱因斯坦是相当善良可亲的。他不想为衣食住行花费时间,他留下的许多照片可以看出,他的穿着极其简朴,常常穿咖啡色皮上衣——艾尔莎送给他的礼物,很旧很旧的,天冷再加上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尔莎送的礼物,同样很旧很旧。还常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礼服。
对荣誉的漫不经心的反面,则是对研究工作的全神贯注。许多回忆录都谈到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阁楼式的工作室里写作、阅读,而更多是思索。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绺白发绕到手指上。爱因斯坦不时从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爱因斯坦脸色苍白,额前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的天性实际上是喜欢结交朋友的,尤其是他所喜欢的人。
爱因斯坦有一位医生朋友,名叫鲁道夫·埃尔南,他常和爱因斯坦在柏林郊外散步、交谈。在回忆录中,埃尔南对爱因斯坦有着如下的描述:
“他有一双天使般的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线,坦然地看着周围的事物——关于这一点许多同时代人都知道。但是不太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爱因斯坦比中等个儿略高,白皙的皮肤,结实的肌肉……。他不爱吃药,却喜欢医生……。爱因斯坦喜欢跟他们交谈,因为可以得到和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出生的人们交往的丰富经验。他在医生中间找到某种与自己特有的爱好相近的东西,因为爱因斯坦本人也可以认为自己是为使人类健康和得到改善而斗争的一名战士。”
巨大的荣誉和成就并未泯灭爱因斯坦善良的同情心。英费尔德深深铭记住这一点。英费尔德第一次会见爱因斯坦是在1920年。当时,他在雅盖斯基大学学习,而在第五学年时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那儿完成自己的学业。但是,出生在波兰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在普鲁士官僚机构中会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久久犹豫之后,英费尔德决定向爱因斯坦求援。英费尔德描述着这一次求援:
“我在哈贝兰大街5号爱因斯坦的住宅门前按了电铃。我又胆怯,又激动,怀着节日般的心情等待当面亲谒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夫人请我走进一个摆满了笨重家具的小房间。我说明了来意。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我的脸都发红了。最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和中国人道别后,便请我进去。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颗主要的纽扣。那张脸我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已经看到过许多次。但是没有一张照片能表现出他那炯炯的目光。
“我把自己事先认真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对我友好地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是我到柏林以来见到的第一次亲切的微笑。我结结巴巴地向他叙述自己的困难。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一封信给普鲁士教育部长,不过这一点用也不会有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开过许多介绍信了’,接着,他冷冷一笑,低声又说了一句:‘他是反犹主义者’。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沉思了一会儿。
“‘您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点。我写几个字给普朗克教授。他的推荐比我的作用大,这样办最好了!’
“他开始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草书了几句。他还不知道我对物理学是否有所了解,就已经把信写好了。”
轰动世界后的爱因斯坦仍然质朴、善良、乐于助人,这种品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