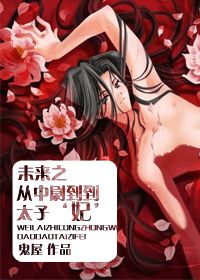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 创作随笔-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战,不仅对令人,也对古人,那么,在这一豪迈的进程中,就应该敢于建立起一种“无榜
样”的意识——这和妄自尊大毫不相干。
“无榜样意识”正是建立在有许多榜样的前提下。也许每一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超越前人
(不管最后能否达到),但首先起码应该知道前人已经创造了多么伟大的结果。任何狂妄的
文人,只要他站在图书馆的书架面前,置身于书的海洋之中,就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和可
笑。
对于作家来说,读书如同蚕吃桑叶,是一种自身的需要。蚕活到老吃到老,直至能口吐
丝线织出茧来;作家也要活到老学到老,以使自己也能将吃下的桑叶变成茧。
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读书过程。有些书是重读,
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
今中外的长卷作品。其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
同时也读其它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
著作,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
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等。那
时间,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以便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相当熬人的,就像长时间不间
断地游泳,使人精疲力竭,有一种随时溺没的感觉。书读得越多,你就越感动眼前是数不清
的崇山峻岭。在这些人类已建立起的宏传精神大厦面前,你只能“侧身西望长咨嗟”!在
“咨嗟”之余,我开始试着把这些千姿百态的宏大建筑拆卸开来,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体察大
师们是如何巧费匠心把它们建造起来的。而且,不管是否有能力,我也敢勇气十足地对其中
的某些著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去鉴赏它们的时候,也用我的审美眼光提出批判,包括对
那些十分崇敬的作家。在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
甚至有意“中止”了对眼前中国文学形势的关注,只知道出现了洪水一样的新名词,新概
念,一片红火热闹景象。“文坛”开始对我淡漠了,我也对这个“坛”淡漠了。我只对自己
要做的事充满宗教般的热情。“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只能如此。这也很好。
有我所有阅读的长篇长卷小说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部分。从现代小说意义来观察中国
的古典长篇小说,在成就最高的《水浒》、《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四部书
中,《红楼梦》当然是峰巅,它可以和世界长篇小说史上任何大师的作品比美。在现当代中
国的长扁小说中,除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他是我的同
乡,而且在世时曾经直接教导过我。《创业史》虽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但无疑在我国当代
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次,我在中国的长卷作品中重点研读《红楼梦》和《创业史》。
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
无论是汗流浃背的夏天,还是瑟瑟发抖的寒冬,白天黑夜泡在书中,精神状态完全变成
一个准备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个纯粹的“书呆子”。11为写《平凡的世界》而进行
的这次专门的读书活动进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况下,就立刻按计划转入另一项
“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
根据初步设计,这部书的内容将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
会生活。
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
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序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当然,我
不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这些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
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
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哪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
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克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
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
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人性。正如传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在任何艺术作
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
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
人物的雕琢,以及其它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
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作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
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契尔特科夫笔录,一八九四年)。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完全掌握这十年间中国(甚至还有世界——因为中国并不是孤
立的存在,它是世界的一员)究竟发生过什么。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
因为庞大的中国各地大有差异,当时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种做法和表现。这十年间间发生的
事大体上我们都经历过,也一般地了解,但要进入作品的描绘就远远不够了。生活可以故事
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
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
较为可靠的方式是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地查。报纸不仅记载于国内外
第一天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有当时人们生活的一般性反映。
于是,我找来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
《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计本。
房间里顿时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
我没明没黑开始了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页一页翻看,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
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
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靡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
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的人工作
做完。以后证明,这件事十分重要,它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任何时候,我都能
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国、一人省、一个地区(地区又直接反映了当时基层各方面的
情况)发生了什么。在查阅报纸的同时,我还想得到许多当时的文件和其它至关重要的材料
(最初的结构中曾设计将一两个国家中枢领导人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我当然无法查阅国
家一级甚至省一级的档案材料,只能在地区和县一级利用熟人关系抄录了一些有限的东西,
在极大的遗憾中稍许得到一点补充,但迫使我基本上放弃了作为人物来描写国家中枢领导人
的打算。
一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但是,似乎离进入具体写作还很遥远。所有的文学活动
和其它方面的社会活动都基本上不再参与,生活外于封闭状态。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笔会时
有邀请,一律婉言谢绝。对于一些笔会活动,即使没胡这部书的制约,我也并不热心。我基
本上和外地的作家没有深交。一些半生不熟的人凑到一块,还得应酬,这是我所不善长的。
我很佩服文艺界那些“见面熟”的人,似乎一见面就是老朋友。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别人抢
着表演的场所,我宁愿做一个沉默的观众。
到此时,我感动室内的工作暂时可以告一段落,应该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
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所谓“深入生活”。
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与“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一样,一直是我国文艺界长期争论不休
的问题。这一点使我很难理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问题值得百谈不厌。生活
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至于每个作家如何占有生活,这倒大可
不必整齐一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受生活的方式;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同一作家体
验生活的方式也会改变。比如,柳青如果活着,他要表现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的“生产
责任制”,他完全蹲在皇甫村一个地方就远近不够了,因为其它地方的生产责任制就可能和
皇甫村所进行的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
是的,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中国大转型期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
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又交叉惨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
的局面。而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
去全面体察生活。
我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开始在生活中奔波。一切方面的生活都感兴趣。乡村
城填、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
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
入进去——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陪努力,争取短时
间内熟悉。对于生活中现成的故事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故事我自己可以编——作家主要的
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且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
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详细笔记下来。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到的特定地域环
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
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
新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在占有具体生活方面,我是
十分贪婪的。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自信,自由度也就会越大。作为一幕
大剧的导演,不仅要在舞台上调度众多的演员,而且要看清全局中每一个末端小节,甚至背
景上的一棵草一朵小花也应力求完美准确地统一在整体之中。春夏秋冬,时序变换,积累在
增加,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奔波到精疲力竭时,回到某个招待所或宾馆休整几
天,恢复了体力,再出去奔波。走出这辆车,又上另一辆车;这一天在农村的饲养室,另一
天在渡口的茅草棚;这一夜无铺盖和衣躺着睡,另一夜缎被毛毯还有热水澡。无论条件艰苦
还是舒适,反正都一样,因为愉快和烦恼全在于实际工作收获大小。时光在流逝,奔波在继
续,像一个孤独的流浪汉在鄂尔多斯地台无边的荒原上飘泊。
在这无穷的奔波中,我也欣喜地看见,未来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轮郭已经渐渐出现在生活
广阔的地平线了。
这部作品的结构先是从人物开始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群体。然后是人与人,
家庭与家庭,群体与群体的纵横交叉,以最终织成一张人物的大网。在读者的视野中,人物
动动的河流将主要有三条,即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
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这三条河流都有各自的河床,但不时分别混合在一起流
动。而孙少平的这条河流在三条河流中将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当然,在开始的时候,读者
未见得能感觉到这一点。
人物头绪显然十分纷乱。
但是,我知道,只要主要的人物能够在生活和情节的流转中一直处于强有力地的运动状
态,就会带动其它的群体一起运动,只要一个群体强有力运动,另外两个群体就不会停滞不
前。这应该是三个互相咬接在一起的齿轮,只要驱动其中的一个,另外的齿轮就会跟着转
动。
对于作者来说,所有的一切又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整个生活就是河床,作品将向四面
八方漫流——尽管它的源头只是黄土高原一个叫双不村的小山庄。
从我国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结构看,大都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因此作品对社会生活
的概括和描述都受到相当大的约束。某些点不敢连接为线,而一些线又不敢作广大的延伸。
其实,现实主义作品的结构,尤其是大规模的作品,完全可能作开放式结构而未必就“散
架”。问题在于结构的中心点或主线应具有强大的“磁场”效应。从某种意义上,现实主义
长扁小说就是结构的艺术,它要求作家的魄力、想象力和洞察力;要求作家既敢恣意汪洋又
能绵针密线,以使作品最终借助一砖一瓦而造成磅礴之势。
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
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而这种才智
不仅要建立在对生活极其稔熟的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对这些生活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的基础
上。我一再说过,故事可以编,但生活不可以编;编选的故事再生动也很难动人,而生活的
真情实感哪怕未成曲调也会使人心醉神迷。
这样说,并不是不重视情节。生活本身就是由各种“情节”组成的。长篇小说情节的择
取应该是十分挑剔的。只有具备下面的条件才可以考虑,即:是否能起到像攀墙藤一样提起
一根带起一片的作用。一个重大的情节(事件)就应该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