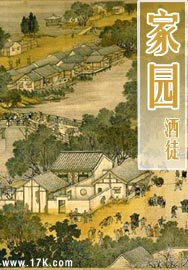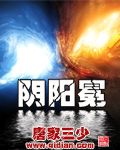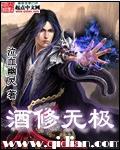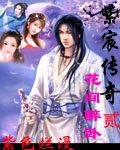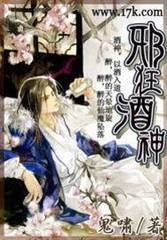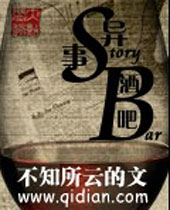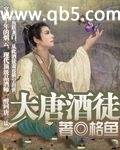花间一壶酒-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武帝死后,遗命封侯,不受,与霍光共同辅佐汉昭帝,地位极其显赫,死葬茂陵,谥曰敬侯。我到茂陵参观,见过他的墓。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4)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很好奇,古人为什么常常用自己过去的敌人或敌人的后代做近侍或养马?难道他们就不怕孙悟空(官封弼马温,就是养马)大闹天宫,勾践(他也为夫差养马)卧薪尝胆,一洗会稽之耻吗?看来,政治家是要有点胸襟和魄力的,就像人能驯服猛兽,豢养役使之。他们懂得,“奴才”比本来意义上的“自己人”要更为可靠。“奴才”是“丧家之犬”,对主人最有依赖性,不像“自己人”,各有地盘和势力,盘根错节,反而难以驾御。
古人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器量。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混乱世界,虔诚有余、宽容不足,以巴冲突是其缩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圣地都在耶路撒冷,一地难容三教。他们根本不能想象,甘泉宫是把汉胡之神搁在一块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靠武力输出一切的世界,声音太小。它使我们不能不对历史上的民族融合进行重新思考。
世界上的国家形态,一直有两条路子。一种是部族纷争,小国林立,长期分而不合,或只有松散的联合,管理水平低下,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权力中心。一种是大地域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科层管理非常系统,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前者如雅典,后者如亚述、波斯和中国。由于取径不同,政教关系也不同,造成两种“大一统”:一种是有统一宗教,没有统一国家,宗教管国家;一种是有统一国家,没有统一宗教,国家管宗教。前者的典型是欧洲各国,后者的典型是中国。
两种国家形态,两种大一统,哪种更好,这里不必谈。很多问题,短期里还看不清。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国家形态的研究上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知道,国家的产生是为了制止和控制人类的流血冲突。我们人类比任何动物都更爱自相残杀,也更会自相残杀。对这个物种来说,杀人是最高科学。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怎么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和平共处,这是一个难题,至今还困扰着人类。在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上,我们能看到的最普遍,最简单,也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既消灭其肉体,也消灭其精神(主要就是铲除对方的信仰),挖对方祖坟,毁对方宗庙,灭对方社稷,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如亚述帝国和蒙古帝国,马蹄所到,剑锋所及,经常是血腥屠城。近代列强瓜分世界,也充满野蛮杀戮,遗风被于今日。征服者为了获取其可怜的安全感,他们觉得,杀死对方居民,真是太有必要。即使留下妇孺老弱,也只限于女性,所有男人,必须全部杀光,西周铜器铭文叫“无遗寿幼”。为了防止意外,坑杀降卒,在古代也极为普遍。
这些都是笨办法。
梁惠王问孟子,什么样的人才能统一天下,古代的聪明人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即不是杀人成瘾乐此不疲的人才能统一天下。他的话,并不等于说,不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这样的“好帝国主义”,从来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杀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更杀。他们都靠杀人取天下,我们不能忘记。忘记这一条,少数民族不答应,周边的国家也不答应。但光靠杀人不能统一天下,孟子的说法完全对。
还有一个聪明人,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文革”批林批孔,这话批得最多,但是孔子思想中的闪光点。他的意思是说,最好的统治办法还是笼络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家的国家亡了,要想办法把它重建起来;人家的国君死了,要把他血缘最近的遗属找出来,让他接续香火,保持该国的祭祀;人家的大臣和贤人躲起来,不敢露面或不肯露面,也要三顾茅庐,把他们请出来做事,共襄盛举。
这样的办法,很好,但绝不像有些人以为,全是孔孟发明、儒家传统。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孔孟之前就有,孔孟以后也没断。它们的真正发明者全是铁碗政治家,发明物也不是道德,而是制度。如武王克商,把商纣斩首示众,血淋淋,但下马之始,即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请商朝遗老出来做事。商王的后代,也授土授民,初封于殷,后封于宋。商的与国也各有分封。就连商的军队殷八师,也被周人全盘接收(当然,同时要移民设监,编户齐民,类似后世的“徙豪强”)。特别是周之“百姓”,传出五帝,各有自己的祭祀系统,春秋战国以来,散处各地,每个国家都不能一族独大,必与他族共存,兼并各国,统一天下,就更离不开这条。因此,出现五帝并祭的局面(秦最早,也最突出)。
五帝并祭,就是中国最早的“五族共和”。
中国的大一统肇始于秦,但民族矛盾太激烈。制度统一较顺利,思想统一(学术统一和宗教统一)不成功。专恃武力和法律,不足以收拾人心。汉代的办法还是西周的办法,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但对外宣传,还是强调“软”。如《尚书》和西周金文都有一个词,叫“柔远能迩”。对待前朝遗臣,越是地位尊显,越是手下留情(杀小留大,是我们的传统)。汉高祖取天下,不但为七国绝无后者寻找后代(包括秦始皇的后代),维持祭祀,还为造反失败的陈涉置守冢,奉祭血食。汉武帝整齐学术,可以团结当时的精英,但光靠这一条,还不足以收拾人心。收拾人心,还得整齐宗教。他到处修祠立庙,干什么?就是为了整合各地不同的信仰。一国多教,很符合现代趋势。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5)
汉以后,中国的大一统,内部融合比较成功,但边患无穷,始终头疼。“蛮族入侵”,世界各国都抗不住,只有中国,胡汉之争两千年,各有胜负。中国的领土,就是借这种你来我往,我化你,你化我,而成就其大。单就领土而言,双方各有贡献,但“蛮族”的贡献更突出。历代版图,蒙元最大,满清次之,民国、唐、汉又次之,遑论其他。元代和清代,统治者都来自塞北,世界历史上,除近代欧美列强,他们是最大征服者。有清一代,虽受反清复明的革命党人诋毁,包括章太炎和孙中山,但平心而论,他们能以少融多,把横跨欧亚大陆的众多国家和民族纳于同一个国号之下,反客为主,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边疆政策,它是两种“大一统”并用:汉族是以政统教(延续传统),边疆是以教统政(类似欧洲),远比汉族成功。民元以来,孙中山倡“五族共和”,是继承清朝。再向上追溯,则是元朝。这点对现代政治很有启发。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东亚共荣圈”,也是模仿清朝和元朝,幸好未能如其愿。
蒙古族,在中国的边疆地区,除蒙古本部,在青海、西藏、新疆,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深刻影响,居民也散居各地,青海、新疆和西藏,到处都有。清朝在统一政策上,最能认同的是元朝。他们的边疆政策,首先就是整合蒙古各部,蒙平则回定(北疆定则南疆定),青海、西藏也迎刃而解。他们是从蒙古手下接收整个西北边疆,然后借广阔的西北边疆,内控汉地,外纾列强包围的外部压力。
前些年,我到青海访问,去过青海湖、日月山、瞿昙寺,到处可见“五族共和”的痕迹。如青海湖边有共和县,共和县里有海神庙,雍正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叛,在此与蒙、藏、汉、回会盟,改遥祭为近祭,就是五族共祭。庙中有碑,原题“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民国改为“中华民国万岁”,仍袭其礼。日月山,是唐朝与吐蕃会盟,分疆划界的地方。如今,山南山北,还是两幅景色:山南是遍地牦牛,山北是汉式村庄。日月山以北的居民,即使是藏民,也是汉语汉装。瞿昙寺,是喇嘛庙,也采用汉式。
北京居庸关,有个云台,券门内有《陀罗尼经咒》等题刻,是用汉、藏、西夏、梵、维和八思巴六种文字刻成。它说明,蒙元才是“五族共和”的更早源头。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强调世界市场的形成,本来中国才是老大。其实,世界市场的形成,海路,是欧人开辟;陆路,是蒙元开辟。这才是世界市场的本来面目。
清朝认同元朝,背后的原因很深刻。
2004年11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从“五族共和”想起的(1)
读《洪业传》(陈毓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想起一件事。
洪业先生晚年侨居美国,每于故土作远人之思。他去世前一年,即八十六岁时,有一天,大陆来了客人,先生性起,亲自下厨烧菜。菜成,而略分五色:红的是龙虾,绿的是芥菜,黑的是豆豉,黄白是鸡蛋。先生戏称为“五族共和”。
洪业先生的菜是模仿中国废君权、行共和之后的第一面国旗,即所谓“五色旗”。五色旗是怎么发明,其详细过程,我没有查考。从外观看,当是模仿“万国旗”的流行式样(如法、意、德、俄等国的国旗),属于当时的“国际接轨”。这面旗,孙中山在南方没打几天,主要是在北方打,先是北洋政府,后是伪满政府,名声并不好。但它以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在民国历史上还是有伟大意义。因为辛亥革命,要按革命初衷,本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如果大家真像章太炎出狱在日本演说那样,仇满恨满,慨当以慷,一定要替明朝报仇雪耻,把这场“种族革命”进行到底(和现在满世界的清宫戏真是大异其趣)。那结果只能是,驱满则蒙离,蒙离则回、藏去,四土不守,列强瓜分之势成,中国的形势将危若累卵。
民国初建,中国政治家考虑的满、蒙、回、藏问题,表面上是民族问题(论人口,它们都不如壮族多),实际上是边疆问题(古语叫“藩”,是与地缘政治有关的概念,清朝有理藩院司其事)。“满”是东北,“蒙”是蒙古(包括外蒙古),“回”是新疆,“藏”是青海、西藏和西康。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Richmond Lattimore)在这些地方跑过,对中国历代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政策有深入了解。他所论述的“中国边疆”就是指这四个地理单元。
中国大地,西北高而东南低(《淮南子》借神话有生动描述),从爱辉到腾冲画条线,正好是两大块。东南多江河湖海、丘陵平原,为农业区,华夏居焉,这只是中国历史之半。另一半是满、蒙、回、藏及其前身。它们的居住区是所谓“骑马民族”(其实多是游牧、狩猎兼农业)的游栖之所,从东北到西南,或为森林、平原混合区,或为草原、沙漠混合区,或为沙漠、绿洲混合区,或为崇山峻岭与草原平原交错的复杂地形。四个单元是四种环境。中国历史主要就是通过这四个单元而溶入世界(首先是东北亚,其次是中亚,又其次是西亚和南亚),真不知有多少秘密埋藏其中。
“野蛮”与“文明”相互依存。“蛮族入侵”在西方,在东方,在东西方之间,一直都是世界性的大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如此,如汉代的匈奴,元代的蒙古,即其著称者。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西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中国自汉以降而有南北朝(在我看来,商周时代的格局也无异于南北朝),自隋唐以降而有突厥、吐番和鲜卑,自宋以降而有辽、金、西夏、蒙元、满清。东南一次次被西北征服,西北一次次被东南腐化。中国的国土是这种历史冲突的结果。
地坛是郊祀之礼中的祭地之所,当然也是领土的象征。
明清时期的地坛,我是说北京的地坛,它的主体建筑是方泽坛和皇祇室。坛室所祀,除地祇之外,还供五岳、五镇、五陵、四渎、四海,实为“天下”之缩影。清朝灭亡,郊祀之礼不行,北京六坛(即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先蚕坛,如果加上社稷坛,则是七大坛)大多荒废,墙屋倾圮,野草丛生。这里驻过军,养过马,种过庄稼,后来“废物利用”,辟为京兆公园(当时北京叫京兆),简直面目全非。不但原来的方泽坛成了讲演台,皇祇室成了图书馆,还搞了世界园、体育场和其他许多现代化的名堂。园中多格言标语,宣传“爱国思想”、“国家主义”,和满园的“西化”适成对比(注意:“公园”本身就是西化的产物)。它的世界园是按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做成的微缩景观,比现在那个世界公园早得多,园中有联,曰“大好河山,频年蚕食鲸吞,举目不胜今昔感;强权世界,到处鹰瞵虎视,惊心莫当画图看”。“天下”概念为之一变。更有趣的是,它还在东西大道临近方泽坛的门口盖了一座“共和亭”,亭分五面,瓦分五色,左右挂着两块匾,一作“共和国之主权在人民”,一作“共和国之元气在道德”,亭中悬挂“五族伟人像”,每面一幅,汉族伟人是黄帝,满族伟人是努尔哈赤,蒙族伟人是成吉思汗,回族伟人是穆罕默德,藏族伟人是宗喀巴。正是“五族共和”的象征。这些都是1925年任京兆尹的薛笃弼创造发明,现在是什么也看不到了。
读薛笃弼《京兆公园纪实》(1925年),心中有个想法:近代以来,中国的“天下”概念变了,但“五族共和”的想法却相当古老。
1997年1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过一个中国古代艺术、宗教的讨论会,与会者大谈Shamanism(这是他们的流行话题),让人觉得空洞。我的发言题目是《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这篇讲话本来是用考古发现重读《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但为了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