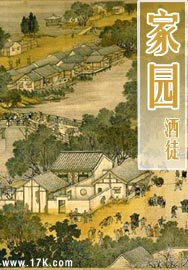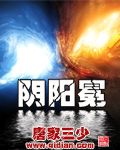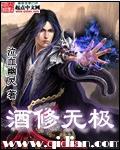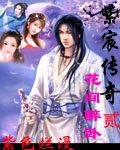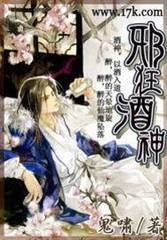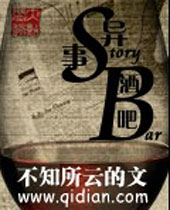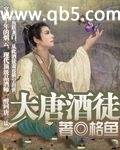花间一壶酒-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军印守衡州,王屏藩挂破朔将军印攻四川,方光琛巡抚湖南。吴世琮挂大将军印攻广西,全省俱陷,擒李棠、傅宏烈送桂,桂赦之,用宏烈为监军道,棠及方孝标为承旨学士。遣使潜至徽州聘谢四新,四新辞不赴,答一诗曰:“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使回,桂怒骂曰:“薄福小人!”王屏藩报四川全省俱平,桂即以为四川总督将军守保宁,而以来度为四川布政使司。聘故明少卿李长祥,延以宾礼,问方略。长祥曰:“亟改大明名号以收拾人心,立怀宗后裔以鼓舞忠义。”桂以其言问方献廷、胡国柱二人,曰:“昔项羽立义帝,后又弑之,反动天下之兵。今天下在王掌握,他日又置怀宗后裔于何地?”长祥知桂意,遂谢去。桂以夏国柱挂殄朔将军印,由衡山出萍乡。上差和硕安亲王为征南大将军,由江西至袁州,攻萍乡。
是年二月十五日,福建耿精忠亦起兵应桂,称“甲寅”年。上命和硕康亲王为奉命大将军,与将军赉塔领满兵二十万,攻福建。又差顺承郡王为宁南靖寇大将军,领满兵十万,由武昌攻岳州;川湖总督蔡毓荣领汉兵十万,由荆襄攻松滋;(《平吴录》)……其侄某出首,云尸已焚化,匣骨藏安福园石桥水底。戽水掘骨,并世首尸解京,亲诣祭告诸陵。判其尸骨,传示各省,悬之通衢示众。此逆藩吴三桂不忠不孝之终事也。(《平滇始末》)案:吴三桂这一生,选择套着选择,每一步选择都受制于上一步选择。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云南,是吴三桂的最后一次选择。这次选择,同样是被逼。他是打前明的旗号,还是打自己的旗号;是北上中原,与清兵决战,还是据守西南,维持割据局面。他是选择了割据称王,后来还称帝。这一选择,今天多以为是不智之举,因为没有合法性,也失去人心。但当时什么是有利,什么是不利,他该选择什么,他能选择什么,实在很难说。我在《汉奸发生学》中说,谢四新的诗写得真好,它把吴三桂的人生矛盾揭露无遗。吴三桂哭陵倡乱,三军失声,气氛十分悲壮;誓师校场,弓马娴熟,威风不减当年。但他的再度反叛,使一切都成谎言。吴三桂戎马一生,最后暴死衡州,下场很惨。三桂诸子及其家人,还有他从东北带来的部将,不是死于战乱,就是被枭首凌迟。幸免一死的余众,后来被流放于边塞,特别是天寒地冻的东三省,成千上万,在驿站当差,在行宫服役,永世不得翻身。悲惨的故事在反复传唱。
荣辱只在一念之差。
2005年1月16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附记】在《汉奸发生学》中,我老实交待,“‘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不知道”。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提醒我,清朝是把汉族的奸细叫汉奸,和后来的用法正好相反,我没查过原始材料。去年秋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是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王柯教授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会议(会议是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举行,名称和时间忘记了)提交的会议论文,题目是《“汉奸”的民族国家语境——从一首康有为诗看近代民族主义空间》。王教授的文章正好是讨论这一问题。他的结论是,宋代并没有“汉奸”这个词;“汉奸”是从清朝才叫起来的,本指汉人通夷者,如妨碍满清政府在苗地改土规流,与“苗顽”勾结的汉族奸商;道光年间,出于反帝,才把这个词当成背叛中国、勾结西夷的败类,更接近后来的用法;同盟会反满,也把拥清的康、梁称为“汉奸”。案清代朝议和笔记,“汉奸”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道光以前是满、汉有别,以后是中、外有别。清末民初,是满、汉有别。抗日战争,是中、外有别。它既和“国”有关,也和“族”有关。现在的“民族主义”,“民族”是国家(nation),不是汉族、满族的族。小国变大国,弱国抗强国,这样的民族主义,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不能等同于殖民战争的以强凌弱,两次大战的以邻为壑,或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有个问题老说不清,即它宣扬的“爱国主义”,明明爱的是国家,但“国”和“族”总是打架。2002年有一场争论,是围绕“民族英雄”,有人说,戚继光、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不是,就是因这个混乱而起。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边疆》(收入《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2页)一文中也为此事费过不少笔墨。其实,国、族的概念在历史上是时有变化,时有交叉,就像逝者如斯的河流,刻舟求剑,必然搞不清。中国学者有一种习惯,就是老把今日中国版图内的中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非把宋、明爱的中国和汉族等同于现在的中国和汉族,这当然不对。但近年来,有些美国汉学家说,只有说汉语的人才是中国人,这个定义更荒唐。在英语里,Chinese既是汉语(或中国语)也是中国人,好像就是一码事。然而,从希腊时代到现在,西方国家的国籍认定,也不能这么简单。起码我们不能说,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英国人,或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美国人,或说英语的人就一定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与“爱国”的概念相匹配,“汉奸”的概念也很复杂。
且教儿诵花间集
说校园政治(1)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缩小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这些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它们当中,有些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过渡的性质而造成,实出无奈,但也有些是人为造成,则属火上浇油。比如工资统配、职称统配,这些都是早已有之,是体现计划经济特点的东西,带有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性质,就还没有医治的良方。铁饭碗,国外也有,比如美国大学的“终身职”(tenure),就是吃教书这碗饭人的梦寐以求,只有把它拿到手,屁股才坐得稳。我们这儿穷归穷,但位子多,一水儿都是“终身职”,课程满打满算没多少,剩下一大堆时间可以搞科研(当然也可以让某些人睡大觉或干其他什么事儿),我跟外国的同行吹,他们甭提多羡慕。这样的铁饭碗,我看还是有好处,或者至少在眼下有好处。它是保障知识分子生存,防止他们被商海淹死的“救生圈”。说穿了,是一种保险制度。
大锅饭吃着,铁饭碗端着,有些事,咱们就得忍着。比如“职称”,明明就是个“猪肉票”,怎么匀也匀不过来,怎么评也评不合理。“二级评审,系为基础”,多少人的命攥在几十个评委手中,他们是如今的“文章司命”。这些人要是老板,雇谁开谁,大家没脾气,但非得挂上个“评”字,问题就多了。一堆不同学科搁一块,萝卜白菜怎么比?论资破格,双轨并行,往往导致某些人用前者评自己或自己的朋友,用后者评自己的学生或自己朋友的学生,造成“托孤寄后”(而且往往是“祖孙相继”),关系学的影响太大。量化管理,靠刊物分级,靠引用率,靠表格,靠打分,靠统计,表面上很科学,实际是为了堵别人的嘴,叫你有火没处撒。有人“五项全能”,科研立项、教学量、获奖、著作、社会工作,样样行,只因没有“大树”(强硬的导师),照样淘汰出局。本来就“僧多粥少”,还一个劲搞“二桃杀三士”,弄得一帮知识分子比范进还范进,老脸一抹,什么都不顾。弄虚作假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者有之,投书诬告他人者有之,提点心匣子到评委家走动苦苦哀求乃至下跪大哭者有之,甚至赌气轻生搁一摞书在路边扬言到轮下讨公道者也有之。汰优存劣,以中国之大,也许只是局部,但埋没人才绝不是少数。比如我的同行,考古学家卢连城,古文字学家何琳仪,他们都比我年长,在同辈中成绩很突出,无论横比竖比,论年资,论水平,我都看不出有什么道理,非把他们压在下边。当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第一届院士,有些人,如李济先生,对郭沫若看法很坏,但讲学问,还是承认郭的贡献,照样推选郭先生当院士,虽然郭先生自己不接受。我们的评委怎么就这么没气量也没眼光?对评职称一事,现在大家都习惯于拿“看开”二字安慰别人或自我解嘲。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拿眼睛“看”就能“看开”,也不认为“骂”就能解决问题。因为骂归骂,套摆在那里,谁都得往里钻,只要钻进去就不骂了。但自己的看法也未见其高明,还是两字:没辙。
给现在不合理的制度“火上浇油”,突出问题有三个,我看,这才值得请名医会诊,下良方猛药狠治一下。
这三个问题,头号问题是“工程热”。知识分子搞科研,有人送钱,甭管国家的钱,死人的钱,外边的钱,谁说不是好事。问题不在钱。钱是“好东西”,但一跟权力挂钩,成为控制财力、人力,定人生死祸福,当“学术寡头”的东西,就是一种腐蚀剂。再清高的人也趋之若骛,“人文精神”全都掉钱眼里去了。本来文科和理科不同,不一定非得强调集体协作,非得拿“修四库”当学科建设,好像只有资料长编式的大丛书(可配合图书市场)才算成果。在这个领域中,恐怕更应提倡的还是独立研究、创造性的研究,当教授的和当学生的都要有这种精神。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越是年纪一大把,劲头不够使,还越是热衷“修长城”,非巧立名目,弄一大把钱,拖一大批人,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跨”上一个“世纪”,这一堆人就埋在“长城”底下了。现在,大家一窝蜂地上大项目(有些项目可以高达上千万),效益如何,值得怀疑。据说全国结项,大部分都完不成。这要搁在经济领域,至少也是渎职罪。大量资产流失且不说,还影响安定团结。我的一位参加项目设计的朋友讲,现在是花国家的钱不干事,评这评那,样样占先;不拿钱照样出成果,反倒吃亏倒霉,样样没份。特别是有些人简直贪得无厌,旧项目啃两口丢一边,又冲新项目去了,自己报不成,就打学生的旗号,能霸一个算一个。这样的风气,我看是该杀一杀了。
其次,和上一问题有关,还有一个问题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叠床架屋,人为制造的层次太多。现在提倡竞争机制,不但人与人比,系与系争,就是学校和学校之间也要一决雌雄〔零案:现在国家已明令禁止企业评比〕,胜者大名大利、大权大势集于一身,败者只能自认倒霉,这未必真有好处。比如一个学校,本来有教授、副教授、讲师三个层次也就够了。但现在因为新老代谢太快,新教授一上市,老教授就不值钱,非得多加几顶帽子在头上,不足以显示其身份与他人有别。我们不但把教授分成普通教授(新教授)、碩导教授(现在也多半是新教授,在概念上已与前者合一)和博导教授(老教授)好几种,而且还设了“政府津贴”、“突出贡献”、“跨世纪人才”等各种名衔,经常评这评那,连死人都参加评奖(只能让家属领),如果再加上各级学术评委以及首席科学家(这是从科委系统套来的)、院士(听说正在酝酿),实在是一种“爬不完的坡”(活到老,爬到老)。现在时兴讲“国际接轨”,其实这类东西大部分都无法接轨。比如“博导”,美国的正教授叫full professor,是做到头的教授,下面的副教授和助教授(相当我们的讲师)也都叫“教授”,他们统统都可以当“博导”,比我们简单得多,也平等得多,绝不会像我们这里把所有头衔都印在名片上,就连到国外转了转,也能写进百科全书。现在我们把教授分成“碩导”和“博导”,当然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我们把研究生分成两道坎,硕士、博士接不起来。国外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一般都是以博士为主。特别是文科,那是“自古华山一条路”,险得很,既不好找工作,也没有退路。你要不想死心塌地做学问,清清苦苦当老师,就趁早别进这个门。这样的课程不但不限年头,什么时候读完什么时候算,而且往往是硕士、博士一条龙,主要是冲博士去的。可见要废“博导”,也应对研究生的培养制度做相应的改革。“博导”是国际丑闻,政府已宣布废止,明确声明一切正教授都有资格带博士生,但利益所在,难免死灰复燃。最近我的学校又搞“老博”评“新博”,其实还是老一套。我们的评职称、评头衔是“水涨船高”,从前的行情,当个副教授、教授,大家就满足了;现在不行,好像不当博导就誓不罢休。乱加头衔的结果是头衔贬值。我想,现在做社会学研究的人,不妨调查一下,做点time study,看看大家是怎么分配时间。现在的大牌学者,学问大了,“浑身都是宝”,难免挨人宰。别人宰倒也算了,还自己宰自己,整天评这评那,什么会都开,什么书都序,这种“充分利用”,其实是既毁自己,也毁别人。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没当过“博导”、“课题主持人”,也没搞过“大项目”,但他们是真正的学者。学者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官员和承包商。他们靠本事吃饭,靠著作讲话,比什么都强。正如太史公讲李将军,“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们当老师的,如果日事钻营而无心学问,将何以为人师表?何以鼓励学子从教。
说校园政治(2)
第三,现在的广大教师,不包括上面所说帽子很多的那些人,谁都知道待遇很低。比如我所在的学校,要说名气,在全国要算很大了,但很多人一月才拿二三百元,菜篮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