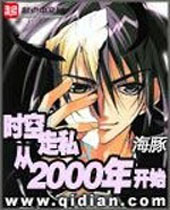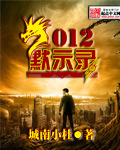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_下-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贺教授的“抬杠”很有力度,从字面上讲理所应当,完全成立。不过,若仔细琢磨,则并非如此,贺教授是把问题搞混淆了。
我的问题是:“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立法本意是什么?以“个人”为例,这里的“个人”是泛指所有的人,还是特定的、手握权柄的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事情就明确了。
就一个普通公民而言,一个乡村的农民,一个城市的普通市民,他能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吗?他干涉得了法院的独立审判吗?或者说,法院会因为一个普通农民、一个普通市民的“干涉”而丧失其独立审判的地位吗?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无论何时都不可能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地位。如果宪法第126条是针对此而规定,岂非多此一举?
所以,宪法第126条中法院“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立法宗旨是针对掌握公共权力、有能力干涉法院独立审判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的。
行文至此,贺教授所说企业未被列举在内因而和人大、检察院一样具有个案监督权力的推论便不能成立。人大、检察院未列举在内而具有个案监督的权力,是因为人大、检察院拥有特定的国家权力;企业未列举在内而不具有个案监督的权力,是因为它们不拥有特定的国家权力。可见,如果对宪法条文简单地望文生义,难免会因文害义。
另外,我引用宪法第71条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规定,说明人大可以借助启动这个程序来实施个案监督,贺教授说我“更是明显的误导”。
“特定问题”是否包含“特定的个案法律问题”,宪法确实如贺教授所说没有给出明确规定。不过,从逻辑上的种属关系讲,“特定的个案法律问题”当然是包含在“特定问题”之内的。除此之外,还有特定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等等,这有什么疑问吗?好比提到民法中的自然人,我说某大学的教授是自然人,这在逻辑上有错吗?这是否也需要《民法通则》给出明确规定呢?
如果因为没有宪法明确依据,而认为我之所谓“特定问题”包含“特定个案法律问题”是“明显的误导”,那贺教授所主张的人大不具有个案监督的权力,宪法中同样没有明确依据,我可不可以说贺教授是“误导”呢?
二、关于“作为例外的弹劾权和特赦”
我在《从》文中,以立法机关对弹劾案的审理和特赦为例,说明人大可以分享审判权。贺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类常规制度中的例外恰好是对于制度合理性的维护,而把例外当成常态,让立法机关也变成司法机关就不免阴错阳差了。仿佛有病吃药,但是我们却决不可以一日三餐以药为饭。”
对上述文字,我有必要重申我在《从》文中关于这一部分的观点。我谈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问题,是在“许多一般的原则往往都有例外”这个陈述下进行的;我谈特赦问题,是在“人大有权行使审判权的另一个特例是特赦”这个陈述下进行的;至于弹劾案,我说的是美国和菲律宾的例子,当然更是例外。
可见,我并未说过要“把例外变成常态,让立法机关也变成司法机关”。何况,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就从来没有行使过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权力。借用贺教授的比方,我说的是把“个案监督”当药来吃,贺教授却说我要一日三餐把“个案监督”当饭来吃。
我想,贺教授是误读了我的文章。因此,我不把贺教授的这部分文字视为对我文章的不同意见。
三、关于“不知所云的限制”
关于对人大代表个案监督权的限制,贺教授认为我在“这里的逻辑仍然是非常混乱的”并认为,“按照监督的惯常话语逻辑,对于司法加以监督的目标就是为了司法公正,那么代表所进行的任何监督都是有助于社会公益。”
此言不确。监督的目标是为了司法公正,此话不错;但据此认为,“代表所进行的任何监督都是有助于社会公益”,则是贺教授的自我推理。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并不总是一致的。善花往往会结恶果。正如“大炼钢铁”不能“赶英超美”,“一大二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吃人参是为了调养身体,但吃得太多则会鼻孔流血。
所以,限制人大代表个案监督提案权力,是应当给予认真对待的,否则反倒会有损社会公益。
关于外行监督问题,贺教授认为,人大之所以享有监督权,“它的合理性基础在于代表由民选产生,是司法民主的体现。”从这一点看,人大代表是否内行,是否具备专业知识,并不重要。
不过,对于人大仅仅以民主相要求是远远不够的。近些年来,提高人大代表素质,特别是法律素质,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没有必要的法律素质,很难当好一个人大代表,也很难不“辜负人民的嘱托”。十个外行加一起不一定变成内行,但在人大代表法律素质普遍有待提高而使十个内行联名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十人联名总比一个代表的提案要审慎得多。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拆衷。
关于以“穷尽司法救济”为个案监督前提的问题,贺教授认为“根本不具合理性”,理由是,“我们这里的司法救济竟是永远不可能穷尽的。”
司法救济永远不可能穷尽吗?其实,“穷尽司法救济”又叫“用尽司法救济”,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构成对外交保护的一个限制条件。就在与贺教授发表文章的同一期《南方周末》C17版就有一篇关于《华盛顿公约》的文章,该公约就涉及到“用尽当地司法救济”。其基本含义是,受到东道国侵害的外国投资者在未用尽东道国法律对其适用的所有救济手段之前,其本国政府不得行使外交保护权,到国际法院诉讼,追究东道国的国际责任。
“用尽”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程序上用尽,必须使用完东道国所有可适用的司法和行政救济程序,包括上诉程序,直至最高法院或最高主管机关的最终决定;二是手段上用尽,不仅用尽东道国行政、司法中的某一种手段,而且用尽上述所有手段。
如果照贺教授所言“司法救济永远不可能穷尽”,那么《华盛顿公约》对中国就不存在什么约束。同样,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启动也存在以“用尽当地救济”为前提的情况。照贺教授的观点,只要是发生在中国的贸易争端,只要是适用了中国的司法程序,那么永远也不可能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若是这样,那些与中国签署WTO协议的国家岂不全是傻瓜?
我能理解贺教授的担忧。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二审结束后,当事人不断申诉,检察院不断抗诉的情况,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案件还是穷尽了司法程序的。既然如此,我所提以“穷尽司法救济”为个案监督前提的限制条件,自然就不是“根本不具合理性”的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宪法学博士,中山大学管理博士后研究人员)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越来越热闹的香港 越来越寂寞的黄霑
南方周末 2004…12…02 15:42:28
黄霑,1941年生于广州,2004年11月24日逝于香港 象牙黑·李钺制图
《酸酸甜甜香港地》是第一部,也是惟一的“黄霑音乐剧作品”
黄霑与顾嘉辉40年的合作,改变了英文歌曲占据香港乐坛的局面
□梁文道
在他心爱的广东话占据了文化主流之后,他的战斗就像唐吉诃德对着风车舞剑一般,寂寞、徒然,也难免可笑……
可以容纳三百多人的演讲厅竟然坐不满,香港的读书风气就这么差吗?更何况还是我做主讲嘉宾。
两三年前我在香港某家电台和一个朋友共同主持读书节目。谈书的电台节目,对香港主流商业电子媒体来讲,好一个标准票房毒药。为了推广,我们不时得搞些讲座,请一票名人助阵。有一次我们介绍推理小说和侦探小说,就找来特级名人黄霑。请霑叔讲推理小说,是因为我常在他们的专栏里看到他推介推理女王阿加沙·克丽丝蒂(Agatha Chistie)的作品,看来是个侦探小说迷,我想有他到场,题目又是这么大众化,这回听众数目肯定可观。结果真有150多人来了,我那拍档是个比我还小众的文化人,没见过什么大场面,见这排场就兴奋得要命。
可霑叔到达之后就一直有点不悦,直到开场时间过了十分钟,他才有点不情不愿地清清嗓子对着麦克风说话:“我真不敢相信,这么吸引人的题目居然只有这些听众。可以容纳三百多人的演讲厅竟然坐不满,香港的读书风气就这么差吗?更何况还是我做主讲嘉宾。”大伙们听了只好尴尬地笑笑,都知道这就是他说话的方式,完全用不着客气,而且该被批评的是那些没有帮忙坐满讲厅的一百五十人,而非现在坐在这里的一百五十人,除了陪笑,我们还能怎样?后来霑叔隔不了几句就又发点牢骚。私下对我抱怨的时候仍是他一贯粗话满篇的本色:“梁文道,你们都算好××,人这么少还要搞,真他妈的××××,我服了。”
在我和黄霑的有限接触经验里,这一段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觉得那天那个场面最能说明霑叔这个人,和他留下来的东西。他很直接,有什么说什么,觉得不爽就不爽出来,一点都憋不住。他喜欢群众,需要他们的目光、掌声和喝彩。如果失去了大众的欣赏,他会很寂寞。但黄霑到底是个读书人,喜欢别人读书也喜欢读书。那一次讲座正是他回到香港大学念博士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古怪,以黄霑的身份地位,又何苦回到学院补课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写一份肯定辛苦但没有太多欢呼声的粤语流行曲论文呢?读博士难道不寂寞吗?要一个见惯了香港体育馆上万群众吹哨子的大人物,对着150个文静的听众,自然不是味道。“可是黄霑,”事后我也不客气地问他,“你可曾想过,你这么讨厌香港如今的反智气氛,这种气氛是你也有份造成的。”他不同意,又嘟囔了一会儿。
他的电视电影和音乐在这些外埠市场赚回来的钱要比在香港还多。说到中国,南洋年轻人想到的就是香港
这事得从将近40年前说起。1960年代初的香港,电视是有钱人的新鲜玩意,连无线电视都还没成立。港大中文系毕业,师承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的黄霑就进了令人艳羡的“丽的呼声”这个香港最早的电视台(即后来亚洲电视的前身),担任创作构思,是香港第一代的电视人。当时的香港传媒人喜欢在下班之后去夜总会听歌跳舞,而黄霑时常光顾的那家叫做“仙掌”。说到夜总会,不可不提东南亚次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有很多菲律宾乐手出入到各个港埠城市,在酒吧和夜总会里弹奏音乐,从黄昏奏到清晨。他们的音乐细胞很好,虽然没有多少自己的创作也没有自己的国际红星,但还是占据了香港各大舞台,翻唱欧美巨星的歌,每晚以歌声和目光迎送醉醺醺的客人。至于中国乐手,技术不及这些南洋高手,好赌好玩的习惯却犹有胜之,所以总是纪律散漫,当不了一流夜总会的乐队领班。惟一例外就是“仙掌夜总会”的乐队,领班竟然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顾嘉辉。也就是在“仙掌”,黄霑遇上了这个他命中注定的搭档,一起写出了《上海滩》等无数名曲,建立了今天人们所知的“港式流行曲”(Canton Pop)。
但那是1960年代,广东歌根本不入流,第一流的听众到第一流的夜总会听英文歌和爵士乐,土一点的去二流夜总会听老上海的时代曲和时兴的黄梅调。用广东话唱的歌只有民间流传的“粤讴”,内容不外是青楼女子忆述恩客或者自怀身世,怎上得了台面?黄霑最早填的词,是为了配台湾的电影主题曲,所以都是用国语演唱。直到1970年代,情况才开始有了变化。顾嘉辉和黄霑第一次合作广东歌,为电视剧《家变》写主题曲,罗文以独特的唱腔唱出了它的头两句:“须知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自此之后,香港终于有了它自己的流行曲,广东歌终于不再受到歧视。
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末,顾嘉辉那种从中国小调曲式发展出来的独特曲风,加上黄霑用粤语填写但饱蕴传统中文色彩的歌词,二人“辉煌”的合作称雄香港大众音乐20年。一般香港人对传统中国文学是没有什么认识,但在内地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候,几代香港人却在黄霑和他同期的几个填词人的笔下粗略得到了一种中国印象。例如《楚留香》“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又如黄霑自己作曲作词的《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江山笑,烟雨遥,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竟若寂寥,豪情还胜了一襟晚照”。然后到了《上海滩》,内地观众也终于认识到殖民地香港所诠释出来的中国风:“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顾嘉辉与黄霑的作品,唱红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头几代歌手,从罗文、张国文到梅艳芳,共同驱逐了英文歌的白色阴影。香港人听广东话从此不再是一件叫人羞愧的事,甚至还令人骄傲。不只台湾和内地有人为了唱港式流行曲学来一腔广东话,远到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有孩子们是在《小李飞刀》等中文歌曲的背景声中成长。那年头的香港是东南亚最重要的流行文化输出港,他的电视电影和音乐在这些外埠市场赚回来的钱要比在香港还多。说到中国,南洋年轻人想到的就是香港。
香港人是透过看电视剧和听主题曲所团结起来的想像社群
今天当大家纪念黄霑,说他的作品陪伴香港人成长,除了他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