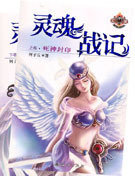卡夫卡 灵魂的城堡-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恒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在此看到了双向的追求:K追求的是活下去,在生活当中理解那不可理解的法;律师追求的是让法在的生动案例中得以鲜明的体现。两人的目标实际上是一个。
法与执法人
执法人身上体现着法,仅仅因为这一点而十分傲慢,不可一世。在其它方面,他们往往都是不可救药的下流坯:受贿。淫乱、说谎、吹牛、势利。说到底,人所具有的他们都具有,又由于执法者的身分而使这些弱点更为醒目。他们是同【同样的有弱点的人,但法律毕竟是通过他们来执行了,否则又能通过谁来执行呢?充斥在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法别无选择。只有一点是值得赞赏的,那就是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对法无限忠诚,他们的行为教育着儿也使K感到非常害怕。就这样,神圣的、看不见的法居然奇迹似地从这些恶棍。流氓身上得到体现,就连摆在审判台上的法典,也是几本不堪入目的淫书。艺术家的魔杖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呢?其中的奥妙只在于意识到法,所有意识到的人,全都蒙上了圣洁的光芒,皈依到法的无边的麾下。
法的严酷不允许同情,每一件恶行都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绝不姑息。正在废物储藏室里看到的那恶心的一幕也可以看成K本身变相的自审。看守们下流卑贱,完全丧失了人格,面对法的惩罚,他们像鼻涕虫一样求饶。但求饶也不起作用。为什么会到这一步呢?只因为法高高在上,根本不承认人格。身分之类的表面规定。人在犯法时胆大包天,一旦惩罚来临则魂飞魄丧。提前预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执法者看上去都像儿童,不知道要如何预防自己犯罪。作为具体的生活在世俗中的人,法只是在执行任务或受罚时才被他们意识到,平时,他们与一般人无异,每一天,他们都在逃脱法的制裁的侥幸心理下苟且过去,大部分时间都是洋洋得意的。“苟且偷生”正是这些执法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写照,他们偷鸡摸狗,钻来钻去,只是为了得点小便宜罢了。当他们意识到法的时候,他们身上的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弱点就都消失了,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些面具,除了那干巴巴的几句例行的话语之外,再也说不出什么。说什么呢?那种事本来就是说不出的,只有抽在身上的皮鞭倒是实实在在的。法只停留在卑贱的执法人的脑海里,卑贱者仍然卑贱,常常在无意中践踏了法,这种情况下,法并不抛弃他们,这又是法的宽容所在。法力无边,包容一切。就连那可怜的听差,位置最低的仆役,戴绿帽子的家伙,不也受到被告们的尊敬吗?这个被法律阉割了的家伙,内心也深藏着复仇的火焰呢。只不过那复仇只能于幻想中实现罢了。法的宽容也来自于法本身的弱点,法不可能脱离大众独立存在,只有这些卑贱者的脑海是它的栖息之处,于是法不得不迁就他们,显出它仁慈的一面,让这些家伙像小孩一样乱来,只是牢牢地保留着最后惩罚的权利。生活在法的控制中的所有的执法者都显出鲜明的二重人格。
执法者全是一些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同样自欺),执法者在对法的理解方面明显高于K,他们对K的所做所为都是为了教育他,告诉他法的存在及其威力。顽固的K却一直生活在表层,死抓住虚幻的根据不放。执法者与K的这种关系揭示出人的启蒙是何等的艰难,完全的启蒙又是如何的不可能。在尘世的大舞台上,半睛的K只能凭本能向前摸索,用皮肤感受光的所在。
如果K不被捕,K与执法者们就会一直互不相干地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这是种不能成立的假设)。由于这没有先例的逮捕事件,一条昏暗狭窄的通道便在那破破烂烂的法院楼上出现了,K稀里糊涂地走在这唯一的、为他而设的通道上,似懂非懂地与法相遇,开始了重新做人的历程。执法者是这条通道上的一些标志,路还得靠他自己走。不如说,K在尘世中生活了三十年,这条隐秘的通道从来就在那里,这通道是为他而设的,执法人也是为他而存在;他们一直在等,等一个契机,他们终于等到了他的被捕,等到了将两个世界联接起来的这一天。法律决不是从一开始就要消灭K的生活,法只是要在K的生活中设置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强迫他意识到它的强大。
艺术家与真实
由于画家与法的特殊关系,K在别人的劝告下决定去找他帮忙。这位穷困潦倒的画家居住在很高的阁楼上,阁楼又破又小,里头空气污浊,周围环境坏到不能再坏。种种描述都使人联想到居住在人群之上的艺术家的真实的精神状况。画家早就等着K的到来,但他对待K的态度既傲慢又不动声色。K首先在他那里看到了一幅画,画的是一名威风凛凛的法官,法官所坐的椅背上画有一名正义女神。女神托着天平,眼睛上蒙着布,正在飞翔。K大惑不解:女神的这种姿态又如何能保证天平作出公正的判决呢?这不是违反常情的吗?画家解释说,法官正是要求他将女神画成这种样子,他是遵旨办事。最后,他在法官的头部画出了红色的光环,将正义女神画成了狩猎女神。无疑,这也是法官的意旨。K不明白,在这个特殊的法庭里,正义决不是放在不动的天平上来衡量的,正义女神就是狩猎女神,她不用眼睛寻找罪,猎物(罪)自会将她吸引过去。这位为法所雇用的艺术家,不过是将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画了出来。身处世俗而又长着特殊眼睛的K被他的画所吸引住了,但是没有看懂,因为他眼前有障碍物。
画家首先问K是否清白无辜,得到K的肯定回答之后,画家便心中有数了。一个自认为清白无辜的人,肯定是对法一无所知的人,这样的人注定要一辈子进行无望的反抗。画家告诉K,他的辩护是绝不可能成功的;虽然这样,画家还是决心要帮K的忙(也许K正是他的创作的永恒主题之再现?),他打算利用自己与法官的私人关系来对法官施加影响,使他们作出符合K的心愿的判决。关于K的选择范围,画家提出了三种可供他选择的出路,然后分别对这三种出路加以解释。解释完毕之后,K才知道对他来说这三种出路在本质上全都一样,都不是他所愿意的。第一种出路形同虚设;第二、第三种则都是将他永远置于法的铁网之内,并时时感觉到惩罚临近的逼迫,于是不得不尽力挣扎,直至最后。原来就是为了让K获得这三种判决中的一种,画家打算为他奔忙。画家对K的前途的分析比律师更直露,这无异于当头一律,打得K昏头昏脑。在那狭窄的阁楼上,真实以稀薄污浊的空气的形式体现出来,画家在这种空气里很自如,很活跃。但K却不能赤裸裸地面对这种可怕的真实,这种真实使得他不能呼吸,他急于摆脱画家,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也就是回到他所习惯了的自我欺骗的世界里去,把这一切不痛快通通忘掉。然而画家还不放过K,好像非帮他的忙不可,甚至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来找他他就要亲自去银行。在此处二人的关系又颠倒过来,使我们再次想起罪吸引着法,想起椅背上的狩猎女神。可以在K的案子里帮得上忙的人就是些这样的人,他们使K心中虚幻的希望完全破灭,他们通过清楚的分析将真实描绘给他看,他们身上体现出法的冷峻而飘逸的风度。生活在尘世中的K不能接受他们,每次交往的结果都是一心要远离他们。
从画家的家中出来,K才弄清楚画家的住处正是法院办公室的一部分,这个发现使他更加沮丧不已,像贼一般地逃离了现场。K的害怕表明了他其实是感觉得到真实的,感觉得到真实并不等于就可以生活在真实之中。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完全的真空里,即使是如画家那密闭窒息的阁楼上,也会有充满煤烟味的稀薄空气渗透进去的吧。像K这样的凡夫俗子,他的肺和心脏都绝对适应不了那种环境。
初出茅庐者与老运动员
商人布洛克是个有五年官司经验的被告,接手他的案子的律师就是接手K案子的同一名律师。K与布格克在律师家里相遇,布洛克向K介绍了自己打官司的经验。从对话中可以看出,K自以为是,狂妄到了愚蠢的地步。他用世俗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案子,对于法律方面的事务一窍不通,又不听劝告。与K的愚蠢形成对照,布洛克十分精明,谦虚好学,又有耐心,五年的被告生涯甚至使他对自己的官司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兴趣,为打官司他用掉了全部的生意资金,也丢掉了从前的地位,这一切换来的只是对于自己官司的一些经验以及案子的拖延。布洛克沉浸在自己为案件所做的努力中,毫不怀疑自己的每一项行动都是必要的,他的信念使他彻底抛弃了过去的生活,而自己并不后悔。他的例子就是自审导致人性升华的例子。然而布格克的经验只是给K带来更深的绝望。一想到自己要像布洛克那样活着,K觉得自己还不如死了好。布洛克也有羡慕K的地方,他说K的案子刚刚开始,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为这一点大律师才特别重视他的案子,而他自己,已经没有太多的可能性了。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隐藏在黑暗的记忆深处的那些原始的能量吧?五年马拉松式的官司已耗尽了商人身上的这些能量,他的前途差不多已清楚了,他本人也干瘪了,乏味了,律师对他的兴趣也就不如对K那么大了。布洛克还提到,在K这个初犯的被告身上,就有某种神秘的迹象(嘴唇的线条)暗示了他那暗淡的未来,所有的人都看出了K的罪是死罪,而且担心他身上的晦气沾到自己身上来,这一点谁也救不了K。布洛克的描述是想说明法正是被神秘的、迷信似的能量启动的;身上这种原始能量越多的人,罪也就越重,法也就越被他所吸引。
K虽然觉得布洛克的经验介绍使他大长见识,可是对他的官司毫无用处,他急于在官司上获得看得见的进展,并且最终摆脱官司。布洛克似乎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其实是他知道摆脱的不可能,于是转而着眼于过程本身。他的这种泰然处之的态度使得K不耐烦了,同时这种逆向的思维还威胁着要动摇摧毁K的那些支撑,K于冲动之下终于不顾一切地做出了不可挽回的冒失举动。
布洛克最后在大律师面前的表现不但让K绝望,还使他丢尽了脸。他就同律师的一条狗一样,以身作则在K面前表演对法的驯服,他的举动令K恶心。奴颜婢膝并不是布洛克的本性,仅仅只是在法面前他才如此自觉有罪;他已经完成了改造,变成了工具。在还没有完成改造的K的眼里,他是不可理解的、陌生的异类。大律师让布洛克表演的目的就是要向K表明:布洛克的现状将是他的未来,K必须习惯这一切。如同意料的那样,K身上蕴藏的活力是要与这一切对抗的,他决不能习惯做一个工具。在法的面前,他是浑身沸腾着热血的初出茅庐者,而市语克是已耗尽了心血的老运动员。K的冒险倾向与莫测的未来使大律师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他对这个青年的爱和无可奈何让他长久地叹息。
囚犯的自由
从被捕那天起,K成了一个特殊的囚犯,一个自由的囚犯。又由于法的存在,更使他不断地体验到这种自由。短短的时间里,他做出了一系列不顾后果,违反原则的事情,例如在法庭上大吵大闹,蔑视官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甚至发展到一意孤行解聘律师。被捕以前,K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遵纪守法,谦虚谨慎,工作勤奋,但似乎是,他从未体验过自由的滋味。他有时与妓女稍微胡来一下,不过那种行为是受到尘世中的法律的保护的,因此也谈不上自由。是被捕使他丧失了理智,还是法本身就带给人自由呢?
K虽然被捕了,他的案子却没有作出判决,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延缓的判决使得他的生活失去了意义,在游离的状态下无论他干什么都是可以的,他处处面临着选择,而他的选择又没有任何参照。既然没有参照,K的选择就完全遵循惰性,遵循从前生活的标准来进行了,这种选择是最糟糕的。法的确带给人自由,但这自由是一种克服不了的困难——即无论怎样选择都是错误的。人只好在错误中体会自由。书中多次提到法对于K的优待,因为他的被捕,他差不多是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凡是别人提醒他不可以干的那些事(看守、律师等人的警告),都是种虚张声势,只不过是为了唤起他对法的意识。自始至终,法从未要求、鼓励过他去干什么,也从未真正阻止过他去干自己要干的事。法,由于其本身的抽象和空洞,似乎可以被K忽略不计。然而,即使在忽略不计之际,也会不断体会到这种可怕的自由的隐约威胁。法总是在他的意识深处提醒:犯法吧,犯得越多,最后的惩罚就越重,不过惩罚还不到时候,继续犯法吧!
神父对K说,法院是不会向他提要求的;K来,法院就接待他,K去,法院也不留他。所以K第一次得到法院含糊的口头通知,赴法院参加了开庭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通知了。K第二次再去法院是出于内心的意愿,也就是说他是主动去的。他这种自愿是法于无言之中教会他的。K的那些自由的举动并不地道,往往十分笨拙可笑,时常是气急败坏的、短视的。不过那毕竟是某种选择,自由的选择,与他从前那些胸有成竹的举动,那种按既定目标的努力有天壤之别。作为普通人的K一点也不习惯这种自由,总想回到先前作为伪装的外壳里去,可惜那外壳已被法的无情的手剥去了,粉碎了。是不是可以说,K的被捕也是自愿的,是潜意识深处的一种选择呢?法是先验的,你意识到它,它就存在。这是K的案例告诉我们的。
选择了被囚的生活方式的K,每天仍然过着一般人的生活,这生活由于意识深处法的存在而变成了行尸走肉。似乎是,法要把K变成一个工具,一个彻底行尸走肉的人,同时法又在踌躇,因为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完全做到的,如果做到了,法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法总是挑选那些生命力旺盛,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