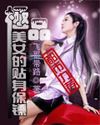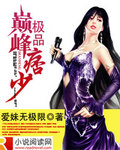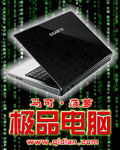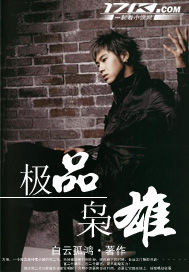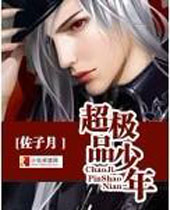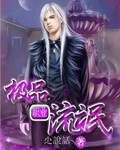极品少帅-第17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被秋临江变法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秋临江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贯与告贯制度,算贯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贯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贯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其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
以云铮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从历史记,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眼下秋临江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云铮所知道的历史中,有一本现在可能不会再出现的巨著《资治通鉴》,在这本书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眼下秋临江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等人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云铮这个后来人的眼光去看待,如何不能看出其中的危害来?所以他不可能对这种做法报持希望。
顾恒和秋临江从朝堂开始争论,下朝之后又在内阁文华殿里争论,直到万昌皇帝来了,依然在争论。但万昌皇帝只是一边面无表情地听着他们你言我语往来不休,却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奏折,看得十分仔细。
奏折是户部右侍郎、清查江苏吏治钦差大臣云岱星夜呈上的。
奏折很长,洋洋洒洒几近万言,其中很详细的谈论了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云岱认为,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变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大家都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恢复,达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当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盖老先生核心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此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从此,曹参名声大盛,当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拾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安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后来,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狂饮,喝的高兴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古板一点的官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当场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不料,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酒杯立即溶进了狂欢的人群。
当时的皇帝,是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作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管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
结果,儿子回到家,话刚刚出口,曹参便大怒,把儿子摁在顿痛打,据史书记载:在**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皇帝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刘盈责备曹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
曹参脱帽,道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
刘盈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参又问:“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
刘盈回答道:“先生好像要差一点。”
曹参说:“对呀。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您无为而治,我们守住职责不乱来,这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听后放心了,说:“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以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云岱说到此处,话锋一转,说翻检这一段史料,会给人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而是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云岱把这样一篇奏折呈上去,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
他虽然也秉承云家的一个大宗旨,就是让皇帝忙点,别闲着没事就找自己的麻烦。但是和云铮一样,他的心里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能严重到天下大乱,伤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元气。
皇帝手里捻着云岱的奏折,有些出神地看着秋临江和顾恒,久久无语。
第140章 君子临江
文华殿的争论仍在继续,并且战局还有逐渐蔓延开来的趋势。现在只是秋临江与顾恒两人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互相驳斥,现在秋临江这边的方谦然和余众乐两人也加入了“论团”,而顾恒作为名门派的四大巨头之一,现在也取得了秦霆和杜凡的支持,只有沈城依旧老神在在地眯着眼,捻须不语。
万昌天子林宥看得一阵心烦,竟然有一种把他们全给拉出去各打五十大板的冲动。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但林宥却皱起了眉头,为什么自己最近心态越焦虑起来,连容人之量都小了许多呢?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把云岚的奏折放下,闭了闭眼,好像酝酿了一下,忽然睁开,低沉但有力地道:“够了!文华殿内,堂堂阁老,吵吵嚷嚷,成何体统!”
正争得差点面红耳赤的几位阁老们立即闭上嘴,互相不屑地哼了一声,看也不看对方一眼,好像多看一眼都会让自己染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般。然后却又十分“默契”地一起朝林宥请罪:“臣君前失仪,请陛下降罪。”
林宥有些恼火地一挥手:“降罪降罪,降什么罪?君前失仪?哼,又‘罪该万死’了是吧?——都不知万死过多少回了,这会儿还不是在这活蹦乱跳,朕……朕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就不能换个词儿。”
不出意外,林宥这话一出口,六人顿时又是一阵“臣罪该万死。”噎得他越不喜,当下一挥手:“都起来了,跪在那可怜巴巴的,你们跪得不烦,朕看着都烦了。”等六人谢恩起身,才又道:“方才你们的话,朕都听了,也仔细想过了。顾相和秦阁老、杜阁老的意思,自然是顺着祖宗成法而来,此乃老成持重之言,朕当然理会得。秋阁老、方阁老和余阁老的意思,朕也听明白了,无非是为朝廷增加收入,以期使朝廷用度开销可以收支平衡而已,这也是当下朝廷症结所在,算是当务之急,无可厚非。”
稀泥巴一和,林宥没等他们表看法,继续往下说道:“朕最近这段日子一直在想,秋爱卿所提出的新法,究竟好不好,如果好,好在哪里?如果不好,坏在哪里?朕不知道诸位爱卿有没有去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依朕看来,先秋爱卿提出变法的本意就是好的,是看到了朝廷现在存在的问题,并且殚精竭虑想要为朝廷解决这些问题的,对于这一点,朕以为先便该给予肯定。那么他这个新法是好还是不好呢,朕觉得大体是好的。顾相,你先别急着说话,听朕来。朕以为秋爱卿的新法,在几个关于财货的问题上,都是从‘开源’上考虑的,因为这个‘开源’,所以使顾相想到了先汉(指西汉)桑弘羊之流的伎俩。朕觉得这大可不必,譬如说……秋爱卿,你说的那个均输法,说来听听。”
秋临江微微躬身,道:“是,陛下。今天下财用窘急,各地官员拘泥于原先就不完善的办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各省上供,内年都有定额,丰收之年不敢多取,歉收之年又不敢不足。三司、运使按簿书征收,无所增损。如果遇到军国郊祀的大开支,又要遣使去刬刷(搜括。刬音产,第三声),几乎没有余藏。各省藏匿财富而不照实报予朝廷、户部,同时又以‘支移’、‘折变’等名目加倍收税。朝廷需用的物品,大多不按照产地和时令,结果是民间纳税加多,朝廷还是财用窘急,但富商大贾却得以从中取利。臣所提出的均输法,其要点是:设运使官,总管东南六省赋税,有权详细过问六省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运使同时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如此就可以减少那些人投机倒把的可能,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
顾恒忍不住道:“陛下,臣先前便已说过,此法原本便是从桑弘羊处而出,若有此一运使,则天下财货皆被其垄断,如此运使之处固然收入颇丰,然则天下商贾毫末之利亦被其夺,却该如何谋生?”
林宥不以为然,摆摆手:“此运使若说可以使那些大商富贾少一份敛财之法,朕是相信的,但此运使毕竟也不能纤毫必算,一般行商所做的那些小量生意,是受不到多少影响的。再者,有此运使,对于此前所言各地每年丰歉有别,该当有所上下,还是颇有好处,所以朕以为这个办法还是不错的。”
顾恒眉头一皱,皇帝这话可就是明显的要牺牲大商人的利益来“平均”到普通人身上去了。有皇帝一锤定音说这这个办法是个好办法,他顾恒虽然贵为相爷,却也不好再直接反对,只好闭口不语,保持沉默。
林宥不可察觉地笑了笑,面色看来却仍然很平常,又道:“秋爱卿其他几项新法,大体上也是遵循这一原则拟定。但是这几条新法,朕以为都只是开源……但是光开源是不够的,更重要,并且更紧迫的,是节流。”
他扫了几位相爷阁老一眼,侃侃而谈:“开源节流,开源使朝廷收入增加,节流使朝廷支出减少。这两条朕觉得都不能少,朝廷既然国用窘迫,那就只能大胆变法,这个法怎么变,无非开源节流罢了。然而节流比开源更难,节流从何而节,朕想诸位爱卿也都清楚我大魏朝廷国库的银子都花在哪去了,‘军饷’、‘官俸’,两只大老虎啊。”
秋临江有些激动,他哪里是不知道节流的重要,实在是觉得难度太大,哪怕他在上万言书的时候就已经是打算“豁出去了”,可仍然觉得节流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所以才没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