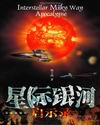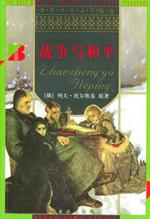战争启示录(柳溪)-第7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共分四大部分,他从本年初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代号为“鸟”的“鸟工作”。
这项工作的具体内容是游说和起用民国初年的三个风云人物: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为所谓“中央政府”领导人拥立的对象。九月末,他曾在上海新公园北侧他的上海办事处,秘密地访问了唐绍仪,并进行了初步会谈。由唐绍仪亲自起草了一份《和平救国宣言》。事隔几日,正在他暗自庆幸工作有所进展的时候,唐绍仪却突然被暗杀。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经受了这一挫折的土肥原,当即离开上海北上,着手进行吴佩孚和靳云鹏东山再起的谋略工作。吴佩孚当时隐居在北京①什锦花园的自宅,平素许多旧部都围绕左右。土肥原密访过他几次,急于拉队伍重整旗鼓的吴佩孚,从一开始便进入了实质条件的谈判。但吴佩孚自视过高,狂妄自大,所以在出山条件上和土肥原代表的日方颇有距离。无风不起浪,“吴佩孚出山”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消息惹恼了眼下担任“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的王克敏,王与吴的关系有如冰炭,水火不容,因此暗中干扰和作梗。这使土肥原非常苦恼。他是前两天才从北京回到天津的,因为他工作的最后一个对象靳云鹏就隐居在天津。
①此时日本已将北平改名北京。市民也习惯称北京。
曹刚带着艾洪水走进客厅时,土肥原便从通向书房的门走出来,转过一道镶着翡疵琅钠练纾呓吞础?
艾洪水清楚地记得八年前的那次土肥原也是在这里接见他的情景。那时他还是名少将,今天这位“东方劳伦斯”已晋升为中将,而且较那时有些发胖了,两鬓有点飞霜,因为头疼,宽阔的前额上戴着铝制的健脑器。艾洪水记得那次他也是这样微笑着,向他伸出手,不过那次谈的话题是让他到张家口抗日同盟军里去抓他的表哥李大波。
“啊哈,艾丧,老朋友,欢迎你!”土肥原伸出手,抓住了艾洪水的一只手,他用另一只手,拉住了曹刚:“曹丧!我正要找你哩,你来的正好。”
勤务兵端上来牛奶咖啡、糖果,便退了下去。
“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土肥原从金边眼镜里透出微笑,“快告诉我有什么事?”
曹刚用日语把他请求协助抓捕李大波的消息叙述了一遍。土肥原听后惊讶得眼镜都掉到鼻子尖上。
“啊?!你们还没抓着那个共党分子?”
“不但没抓着他,他倒抓住了我!”曹刚气呼呼地把在通州的遭遇说了一遍,“哎,那次我差点去见阎王爷!”
土肥原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儿,激动地把手关节弄得嘎吧嘎吧直响。他叹息着说:“说实话,共党问题才是我帝国的心腹大患。只要我们占领一个地方,他们随后也就到了。所以,我已经向大本营建议,应该停止进攻性的战斗,停下来进行扫荡,扑灭共匪,保障治安。不然的话,我军推进得越快,他们占领的地方越多,蒋介石也应该看到共军日益坐大,对他更是不利,他应该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剿共才是正办。克柔,这一点我请你无论如何要把我这个口信儿捎到,这才是我最为关心的。”
曹刚点着头,然后关心地问道:“‘鸟工作’有进展吗?”土肥原摇摇头说:“这个老塞嘎嘞①!简直就是个塞嘎嘞!他的工作很不好深入,他狂妄自大,每次见面总向我发表一些无知的怪理论,他甚至说:‘共产党的党纲宗旨就是共产共妻’!还自我吹嘘:‘我很早以前就公开表示过坚决反对共产党。’又滔滔不绝地说:‘本人以均产主义去顶住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以振兴礼教去扑灭共妻主义’,真有点可笑,我真感到是否我选错了对象。唉,你是我的心腹,这苦衷我只能跟你叨唠叨唠。”他结束了日本话,改用中国话,看了看艾洪水说:“算了,不提我这一段儿啦,还是商议商议如何捉捕这个共党分子吧!啊呀,逮了他这么些年,居然还没逮着他,他也真成精啦!”
①日语中“鸡巴”(男性生殖器)的发音。
土肥原叫进一个守在客厅门外走廊里的勤务兵,吩咐他拿一点酒来。不一会儿,就用托盘托进来几瓶上等的白马牌法国香槟。
“来,曹丧,艾丧!让我们来庆祝一下吧,”土肥原很想轻松一下疲劳的神经和沉重的心情,举起高脚杯笑着说:“首先庆祝曹丧化险为夷,我想不到你经历了这么大的危险,现在危险终于过去了,干杯!”他一仰脖儿,一饮而尽。
又倒上了第二杯酒:“来,艾丧!这一杯好酒是庆祝我们再度合作,干杯!”
两杯酒下肚,他轻松多了,像斧凿似的头痛已缓解了许多。他边用尖厉的牙齿撕扯着日本的干鱿鱼片,不由得打开了话匣子。
“曹刚君,你还记得吧,那是1935年的9月底,我从关东军司令部汇报回到天津,那时你就随在我的左右。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我最迟到11月底,要对宋哲元的工作——也就是‘狐工作’①,必须搞出个头绪。我的天,只有一个月的工夫,而宋哲元又探头探脑,想吃怕烫!我向多田将军汇报关东军这项命令,他甚为不满,处处掣肘,我只好背着他到北京去执行这项命令,11月中旬很快就要过去了,而宋哲元的工作很不顺手,我多么着急呀!……你还记得吗?”
①“狐工作”,即“竹机关”对宋哲元的工作代号。
“那怎么会忘?我记得你急得头痛牙肿,我也跟着着急呀,大冬天的,我都急出帘⒒鹧郏?
“是的是的!这时我便开始中止了‘狐工作’,把注意力转向了殷汝耕,……”
“是呀,你不是派我到蓟密区去跟他秘密接头的吗?我记得当时我表面装的是为那个美国传教士去遵化县寻找他的养女方红薇。”曹刚兴奋地打断了土肥原的回忆。
艾洪水在一旁听着。因为土肥原用一口流利的京腔讲的是中国话,他听得很仔细。“啊!原来他们从那么早就注意上山沟沟的这个小黄毛丫头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们的关系是这么渊远流长……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的!”一涉及到既往,他心里总是这么矛盾地想着。
“是的,你的这次联络工作很有成绩,这也救了我的驾。殷汝耕还真积极,他的决心之大,使我都为之震惊。他毅然揭起反蒋叛旗,他那彻底的反蒋态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没过几天,就在11月25日,殷汝耕就以惊人之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发表了堂堂的反蒋亲日的政策宣言。我派飞机在那天帮他在平津上空散发了那份宣言。啊,你还记得在举事的前一天我们在天津的聚会吧?”
曹刚兴奋地眨着那对小耗子眼儿,快乐使他翘起上唇,嘴角儿出现了两个绿豆粒儿似的酒坑儿,赶紧接上话茬儿说:“我的时候,那怎么会忘?!记得,记得!我倒要提醒您,将军,咱们不是故意挑选了驻屯军出资、由川岛芳子当掌柜的‘东兴楼饭庄’聚会的吗?那天,这个女妖精居然女扮男装,穿了一身缎子长袍坎肩,出来给咱们敬酒,咱当时的用意,不就是让这个小娘儿们在多田将军的床上吹吹枕头风吗?”
“是的。我没有忘。当时殷汝耕带着他手下的全班主要人马,参加了宴会。我说:‘怎么样,能不能起事?’意气高昂的殷汝耕立即就响应说:‘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布新政府成立,今晚我立即返回通州!’我当时真是大为高兴哪!总算完成了关东军的命令。我马上说:‘喂,快拿香槟酒来!好,那么,我们就以香槟举杯预祝成功吧!’可是不巧得很,饭店里的香槟酒已全部卖光,如果到英租界或法租界是很容易找到的,可那时已是深夜,来不及了。我真有点扫兴,便跟殷汝耕商量:‘太不巧了,只有日本酒,怎么样?’殷汝耕却意味深长地说:‘用日本酒庆贺比香槟还好。’殷汝耕一下喝了三杯甜酒,然后就驱车返回通州了。第二天他真的宣告了独立自治。当天晚上我向多田将军做了事后汇报,对我擅自行动,他大为不满,他不同意建立只有殷汝耕的新政权。他总是跟我作对!”说到这里,他的兴奋消退了,突然很痛苦地说:“啊,艾君,想不到这件好事,又让你这位参加过抗日同盟军的表哥给完全断送了!”他拍着沙发桌,突然横眉立目地站起身,咬牙切齿地说:“艾丧!你表哥干的这件事,不仅断送了殷长官的锦绣前程,天津军部还下令逮捕了他,而且多田将军对我就像拿住了什么把柄,使我的成绩全都埋没了!幸好我现在的谋略工作是直属于东京大本营。否则,我还不是处处受钳制吗?啊,我真恨你这位表哥,这个无孔不入的共产党!可怕啊!这才是我担心中国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务必把他抓来归案!艾君,你可要再卖把子力气哟!”
艾洪水蓦地脸红了,他觉得从来笑容满面的土肥原,这时却露出了一脸凶相,使他心里敲鼓般地害怕。他赶紧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
“是,我知道这担子很重,不过,我可是一直在努力,这次就是我发现他们行踪的……”
土肥原举起酒杯,又转为喜悦地说:
“那就继续努力,让我们撒开这面大网吧!干杯!”
曹刚和艾洪水也一块儿跟着说:“干杯!”
三只杯碰到一起,淡黄色的香槟,溢出了酒杯。
二
红薇自从发现了艾洪水的跟踪之后,当天晚上她就开始了迅速转移的工作。当她确知那天夜间敌人还没来得及布置蹲坑监视的暗哨时,她把要紧的文件,包了一个包袱,有一些来往信件还没来得及销毁的都填到炉子里焚烧了,还有一些实在带不了的东西,她只好暂时寄存在跟王妈妈最好的一户邻居家,那是专给胡同里拉水挑水的一个山东人,家里像小猪一样有一窝小孩儿,山东婆娘每天都拉着孩子、背着竹筐,到处去打杂草来喂拉水车的那头小毛驴儿。自从搬到这儿来,王妈妈跟她最投缘、最要好。夜里,那天没有月亮,山东婆娘甩着大脚片儿,一连帮着运了好几趟。有些粮食、菜蔬、杂物,索性送给了挑水的这家。他们一连咕捣了大半夜,红薇这才在房门上贴好了招租条子,跟着王妈妈,拉着鱼儿,回到了河滩的转盘村。
“万祥哥,我应该受批评,我太麻痹大意了,竟然让艾洪水这个小子盯梢都没发觉,隐蔽的地方暴露了,这给组织、给工作,带来多大的损失呀!”她边说边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别难过,谁能保证一点差错不出呢?”王万祥披着棉袄,吸着竹子毛笔杆的小烟袋,慢条斯理地安慰着红薇。
鱼儿又累又乏,很快就睡着了。许多日子不睡热炕头,现在乍一睡,热得他伸胳膊登腿儿踹被子,直打把式,不一会儿撒起呓症,嘴里还说着梦话:“我不走!干嘛咱搬家呀!……
我要上学,我不回河滩拾毛篮……”
红薇听了鱼儿的梦话,心里更是一阵酸楚。眼泪像断线的珍珠那样落到地上,她哭得更伤心了。
“偏赶上大波不在家,我捅了这么大的漏子,大波回来,还止不定要怎样埋怨我哩……”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刮着呼啸的北风。从河滩那儿不时传来因寒冷而坚冰的坼裂声。纸糊的木格子窗户上,为了防寒和怕灯光外泄,挂了厚厚的稻草苫子,用绳子坠着半块砖。
“你没有出意外,这就是万幸,”王妈妈倚在炕头上,也安慰着红薇,“万顺不会申斥你,你放心吧!”
“这都是小事,要紧的是必须向党汇报,以免出别的差错。”王万祥慢声细语地说,又紧着吸两口烟,“明天把对面的小东屋收拾好,你和我妈就住在那屋,你暂时哪儿也别去,就在屋里猫着,我先去汇报。还有另一层缘故,如果组织上不知道,又正赶上大波回来,冒冒失失地先回你们那个家,还不让蹲坑的特务等上吗?”
红薇吃惊地张着嘴,吓得顾不上哭泣了。她急得拍着大腿说:“哎呀,真是的,遇事我倒胡涂啦,也不知他现在在哪儿,没法儿通知他,这可怎么办哪?”
“所以得汇报呀,组织上自然会想办法知会他的。……天不早了,逃出来就不易,睡觉吧,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那天夜里,红薇和王妈妈跟万祥的一家都挤在那条土炕上入睡了。凤娟知道他们回来了,睁了睁眼,瞧了瞧他们又翻身睡着了。她每天要从河滩步行到小刘庄的棉纺厂去络线,一天往返要走几十里地的路程,实在是太乏累了。红薇在锅台上搭了一块木板,铺了草苫,她就睡在那里。但是她满腹的心事,从小又有择席的习惯,所以她一直躺在那里没睡。见景生情,她想到她十二岁那年的复活节——也就是被理查德拐骗来的第二年春天,因为淘气,带着景山公馆附近的邻居家小孩儿——小牛子、黑妞儿、小臭臭、小乐子,到教堂的后院去逮鸽子、掏鸟蛋,一下子窜出了一条花蛇把她的太阳穴咬伤了,她从木梯子上摔下来,送进了协和医院,后来她的病又转了伤寒,最后她被王妈妈带回河滩的家,她就是在这间茅屋草舍里养好的病,从死神手里夺回了那条小命,才没落到雷曼医生手里做细菌试验品的。她又记起她和鱼儿用一块破木板,钉上两根铁棍儿,自制了小木排,多么快乐地在结了冰的河面上飞也似地滑着,有一次差点儿掉到冰窟窿里。她还记起夏天,她和鱼儿站在河边上看着鸬鹚扎猛子逮鱼,他们在岸上脱下小布衫儿飞跑着捕捉蜻蜓,站在浅滩的湿泥里捞螺蛳……但这一切都使她想起了李大波,就是在这间茅草小屋里,给了她人生最甜蜜的爱情,奠定了她的幸福婚姻。没有比今夜她更想念他、更惦记着他的了,一个最揪心的问题,魂牵梦绕地纠缠着她:
“唉,大波!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呢?你是否平安?我理解你不能跟我取得联系,……可是我多么记挂着你呀!只有你回到我的身边,我这颗悬揣不安的心,才会放下来。……”
凛冽的寒风仍旧在肆虐地呼号,从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