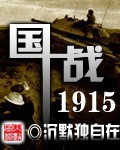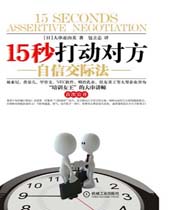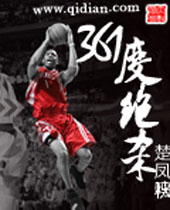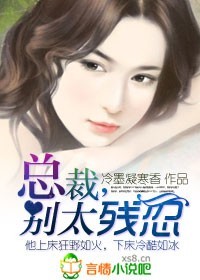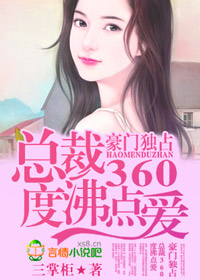3615-新发现的鲁迅-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二十年代与两家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回忆说: “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 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至于为什么她诬陷鲁迅,他认为“主要是经济问题。她(按: 指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章廷谦的话比郁达夫更贴近一层,因为郁达夫是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而章廷谦却是在张凤举他们之列的。九十年代千家驹对周作人信中所谓“过去的事”有如下解释: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周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千家驹自称这是“间接听到与鲁迅兄弟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讲”的,而且最终又说,“我不知道羽太与信子是否同为一人”。又把自己的判断否定了。千家驹所说为孤证,不足为信。但他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信子赶走鲁迅是为了霸占鲁迅买下的八道湾大房子,此可备一说。……
……近年舒芜又提供了一种说法,说得较为具体。他说: “鲁迅替周作人卖了一部翻译的稿子,卖到商务印书馆。正在着急要用钱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送汇票来了。鲁迅很高兴,敲中门进去告诉羽太信子,要告诉她有钱来了。当时可能羽太信子正在洗澡,衣冠不整的时候,因此羽太信子就说鲁迅调戏她。台静农先生告诉我有这么回事情。”
笔者猜测可能早在日本时期,信子对鲁迅就有欲望,她更喜欢鲁迅,周作人只是鲁迅的“替身”。因为鲁迅已经有了包办婚姻,又知道周作人喜欢信子,就成人之美,希望他们好。鲁迅离开他们回国,似乎也不仅仅是为了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可能也有躲避信子而成全周作人婚姻的意思。信子给鲁迅的信无法看到,不得而知。周作人与信子一家住进八道弯以后,信子见到鲁迅的包办婚姻不幸福,她对鲁迅的欲望又强烈起来,她对鲁迅的诬陷,未必是精心策划的计谋,与其说是编造谣言,倒不如说是病中的幻觉。如听窗一事,太可笑。奇怪的病常常产生奇怪的幻觉,总是生活在幻觉之中的人,日久天长,就真假不分了,以幻觉代替现实是人之常情,也不一定非病人不可,何况信子是真有奇怪的病。周作人相信的是信子的幻觉而非谣言。实在说,周作人是被老婆的病欺骗了,而不是老婆的谣言。鲁迅说得很清楚: 为钱的事,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 ‘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所谓“装死”就是犯了奇怪的病。如果信子是出于经济原因诬陷鲁迅,周作人也是可以看出来的,他们霸占房子是否出租?没有下文,可见从经济角度分析也不太合理。从信子病的角度切入问题似乎更容易深入人心,这是笔者多读外国书如弗洛伊德、弗洛姆、容格等人的心理分析著作得出的感想。笔者曾遵照鲁迅的多读外国书的建议,苦读过心理分析的外国书,收益不小。总之,笔者是极信服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的主义的。信子的病洋西医治不好,仍是死认西医,这也是一种病态。尤为不堪重负的是“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 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这样抱怨说。(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5)
信子并非一定要在犯病的时候才有幻觉,既然是精神病,幻觉就是其属性之一。不过是程度有时重有时轻而已。表现为冰山的一角的是信子出于经济原因诬陷鲁迅对她有欲望,正说明是她自己出于对鲁迅长期的欲望而不断地制造幻觉,又把这种幻觉传染给周作人,这是隐藏在冰山下面的潜意识。
第二个谜团,就是人们以为鲁迅没有针对周作人写过谴责文章,对于鲁迅来说,这不太可能。只不过,鲁迅一向善于使用曲笔,很难懂而已。加拿大人李天明说:
鲁迅是嫉恶如仇、睚眦必报的,敌手的攻击他都“三倍四倍地给予反攻”(郁达夫语)。惟独这一次是例外,自始至终他处于被动,避免与周作人正面冲突。他可能担心周作人之昏会导致更严重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忍辱负重,宁可退让。他宁可搬出八道湾,将自己的房子全然让给周作人。他在事情发生后的一两年里竟不参加所有的社交活动。这是何等的自赎,何等悲怆悱恻的事!周作人至死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处,谈及此事的时候总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写了两本关于鲁迅和其小说的书,也不忘表白: “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了。”不过晚年的周作人也引许寿裳说鲁迅生前对兄弟反目的事不置一辞,是他的伟大之处的话,不得不承认“这话说得对了”。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也可能要成为一个永久的谜。可是一旦把握住人在事件中和事件后的所作所为和思想境界,原因的知否也变得不甚重要。人的伟大与品格的高尚不仅仅在于永远正确无过,更在于面对挫折和失意所表露的勇气与真诚。此事件对于鲁迅的打击是沉重的,他痛苦与忏悔的情怀在小说《弟兄》和散文诗《风筝》中有着清晰的表白。
实在说,对于周作人,鲁迅并没有什么可忏悔的,周作人则太没有良心了。人的良心表现为能忏悔,而鲁迅在《风筝》中的忏悔是对朱安的,绝非对周作人。在《野草》第一篇《秋夜》中就有对周作人夫妇的谴责。《野草》中最难懂的一篇莫过于《失掉的好地狱》,笔者以为这篇文章中也含有鲁迅对于周作人的谴责。有人认为,《野草》中《衰败线的颤动》中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表现了鲁迅对兄弟失和的“揪心的苦难和难忍的愤怒,折磨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钱理群《周作人传》)。这也讲得通。有一种观点认为: “清官难断家务事”,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很难说清其中的是非。而于对信子的谴责,是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子女子的中国传统观念的表现,这正是为鲁迅、周作人所反对的。
中国古人的观念是: 修身齐家与政治绝不可分。《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大受世俗文化精英们的诟病,有人读不懂文言文,不知道“平天下”就是使天下太平、百姓平安喜乐的意思,而以为是“平定天下”、“扫平天下”、“铲平天下”。如果是这样,“修身、齐家”当然都不需要。兄弟反目自然就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而无所谓是与非了。
再说女人的问题,不是鲁迅自己把此事的“罪责”“归于女子”的吗?鲁迅对于“家中的日本女人”一直耿耿于怀,不是事实吗?鲁迅的思想中有悖论,是很正常的。在鲁迅研究中,悖论处处都存在。笔者在此书中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 非悖论的思想,就不算思想。在事实与预设理论发生矛盾或遇到悖论的时候,如果不懂中庸之道,就只好采取鸵鸟政策——你说便是你错。
第二部分由“陪着牺牲”到“我可以爱”(1)
鲁迅的身体向来较弱,“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逐出”八道湾之后,即大病在床,多亏身边有朱安悉心照料,一个多月以后就康复了。这是朱安最能感动鲁迅回心转意的时候。萧文邦的《鲁迅新传》说:
这一时期是鲁迅和朱安结婚以来唯一接触较多的时期,也是朱安抱最大希望想以自己的温存去暖和和感化鲁迅已经冰得透凉的心的时期。鲁迅在准备搬出八道湾,去砖塔胡同前,曾与朱安有一段较长的对话,这可能是鲁迅与朱安结婚以来唯一的一次时间较长,内容较重要的单独的对话。鲁迅曾与朱安说: “我决定暂时搬到砖塔胡同去,你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娘家去?如果回绍兴,就按月给你寄去生活费用。”朱安略加考虑,颇有深情地回答: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按: 绍兴称婆婆为娘娘)迟早一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娘家我也不想去,你搬砖塔胡同,横竖总要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去……”鲁迅就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鲁迅和朱安初到砖塔胡同,因受周作人夫妇的欺侮生气,于十月间肺结核复发,天天发烧,胃口不开,朱安是尽心尽力服侍的,病初发时,鲁迅菜饭不进,朱安就在厨房里,把大米泡了,亲自一下一下把米捣碎,天天煮成米汁,还把鱼熬成鱼汤,送给鲁迅喝。后来鲁迅的病稍有好转,就天天给鲁迅做米粥吃,这都见于鲁迅日记的记载,十月四日“晚始食米汁、鱼汤。”十一月八日记有: “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
鲁迅的病能较快康复,与朱安的尽心服侍是分不开的。鲁迅能在砖塔胡同带病创作……天若有知,当也有朱安的默默无闻的一份辛劳在内。她怀着无望的爱,去服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使鲁迅一往无前的冲锋陷阵,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有她的一份贡献的。
朱安另有一种贡献,就是使鲁迅的文章总有一股战斗性和虚无感。鲁迅对许广平说过: “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灭亡。”(《两地书》)
鲁迅和朱安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从砖塔胡同搬到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定居,已经是他们“没有爱”的婚姻生活的第十八个年头了。到了西三条,鲁迅和朱安仍是分居两室。……
平时,鲁讯对于家务琐事.一般是很少过问的.都由朱安操持,朱安女士对于婆婆和丈夫在饮食方的喜好,观察得很细心,她还有一手煎炒绍兴风味菜肴的手艺,很受鲁老太太的称赞。鲁迅虽然没有当面赞誉过,但也从来没有批评过。她每天的时间,几乎都在安排菜饭上度过,她唯一的生活乐趣,是在忙了一天的家务之后,坐在娘娘身边咕噜噜地抽上几枪水烟。她虽然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学问很深,很受人尊敬的人,但他和鲁迅无论思想、志趣、性格上,可以说是全然迥异。哪里来的共同语言。如果说爱情的别名是理解,朱安又怎么能理解鲁迅呢?似乎有时朱安女士也竭力想缩短与鲁迅的距离,也做过种种的努力,但往往适得其反,原以为是想讨鲁迅的欢心,却反而增加了鲁迅的烦恼。
是理解之后才有爱情,还是先有爱情后理解?两种情况都存在,不必一定要先理解而后才谈得上爱情,或者是不需要理解的爱情反而更好?从鲁迅母亲的角度看,朱安的贤惠比较信子的奇怪的病(或换一种表达方式: 大先生的包办婚姻与二先生的自由恋爱),哪一种更好一点呢?爱情问题此处不能深论,但也不可以浅论,它往往是悖论。
据俞芳细心观察,她在西三条二十一号发现了这样一个秘密:
在砖塔胡同、西三条我所看到的,大先生和大师母(按: 即鲁迅和朱安)之间除必要事外,谈话很少。有一件事,我猜测这是大先生想的办法,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放在两处,箱底放在大先生的床下,里面放着大先生换下来的要洗涤的衣裤;箱盖放在大师母的房门右手边,即桌式柜的左边,盖子翻过来,口朝上,里面放着大先生替换的干净衣裤,箱底箱盖上各盖一块白布,外面是不易知道其中的奥妙的。这样,他们间说话的内容就更加少了。(《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俞芳的这段回忆,很形象地道出了鲁迅和朱安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的日常生活之一斑。鲁迅和朱安虽然一直过的是挂名夫妻的生活,但朱安似乎一直是抱有感化鲁迅的幻想,她也企图作出努力,来缩短和鲁迅的距离,得到鲁迅对她的爱,虽然这些努力是徒劳的,但她还怀着希望对俞芳说过: “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这种幻想在朱安的脑海中一直时沉时浮了二十多年,直到她从羽太信子的口中,知道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已经同居的消息后,她的一切幻想都落一了空。这时她非常痛苦,精神十分疲惫沮丧地和俞芳说: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第二部分由“陪着牺牲”到“我可以爱”(2)
这是朱安对爱情的绝望的惨吟,这是朱安对爱情的绝望的悲泣。何等凄厉,何等悲凉,何等伤痛。但她又对鲁迅的人格,有充分的信心,她说: “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个估计,是朱安二十年追随鲁迅的生活中体验得到的,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朱安日后的生活,一直由鲁迅从上海寄钱供养的,鲁迅逝世后,一直由许广平寄钱供养着。
局外人尚且可以认识到这一切,难道鲁迅就不知道朱安的心情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