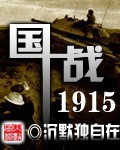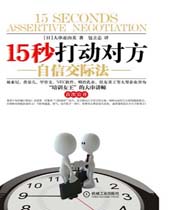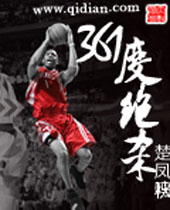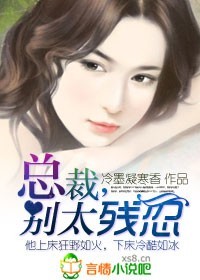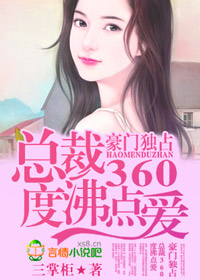3615-新发现的鲁迅-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之苦,归根结底都与性压抑有关,这是鲁迅生命中极重要的“一件小事”。详细的分析,留待后面再说。
后来鲁迅在厦门大学做教授时,受邀作了一次讲演,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的胡里胡涂。”(《两地书》)看来,要真正理解鲁迅,非理解并实践鲁迅的“不读中国书主义”不可,否则对于鲁迅的认识也只能是“胡里胡涂”。说实在话,鲁迅许多真实的思想人们并没读懂,鲁迅某些文章似乎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鲁迅某些文章很像李商隐的《无题》诗,意思恐怕只有鲁迅自己才懂,读者往往不知道鲁迅在说什么,正如那位尊孔的校长一样。某些人本来正是鲁迅所批评的那类糊涂人,只因为也反孔,就自称“我也姓鲁”了,其他也反孔的“旁听人”对他们自然就“肃然的有些起敬了。”绝没有人“跳过去,给他一个嘴巴”,说: “你怎么会姓鲁!——你那里配姓鲁!”
鲁迅此处所谓的“外国书”应该是“日本和欧美书”才确切。因为当时只有日本和欧美国家的物质力量是强大的,文化是先进的。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性文化比较开放,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正受到质疑和破坏。自由恋爱逐渐风行,虽然也无非是为了金钱——请看巴尔扎克的小说——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某些外国书,如劳伦斯的小说则反映了更多的爱情,虽然不怎么体面,但是人性的光辉是耀眼的。此时,东方国家的性文化仍然是陈旧的,包办婚姻和“从一而终”的现像就使很多人都痛不欲生。不仅中国人如此,印度人也是如此。所以印度书就不在鲁迅所说的“外国书”之列。至于说到“国民性”,如果你真的多读外国书的话,就会发现,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人;狄更斯笔下的英国人;果戈里笔下的俄国人;卜伽丘笔下的意大利人或马克吐温笔下的美国人;甚至处死苏格拉底的古希腊人和大叫钉死耶稣的犹太人,等等,都与中国人没有根本的区别,彼此彼此。鲁迅在论述“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时所举的例子就是外国人。鲁迅说: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例: 小事件则如Cogol的剧本《按查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这就是两个例子了,不知为何鲁迅却说是“一例”,这是鲁迅的思想比较难懂之一例。既然古今中外暴君臣民的人性皆一致,而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国民性”有问题,要改造,就伟大得狠了。
理解“不读中国书主义”并不难,这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实实在在地去读原著必有收获。重要的是读原著,而不要读那些“学贯中西”的学者阐述西方预设理论的文章,否则还是读中国书,而非读外国书。也不必多读,踏踏实实地读几本就有用。读了几本外国书,笔者有一个发现: 与中国古人的“知人论世”略有不同的是,外国人还特别不忘“知人论性”。外国人研究品评人物,探寻思想根源,绝不会忽视研究对象的性生活,懂得这一点,也就抓住了人性的根本。不过,西方人看到的问题,中国古人也早就看到了。春秋时期的中国书里就有“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说法。古人认为,人性主要就表现在这两个方面,由此入手观察社会人心,就洞若观火。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一文中把古人“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道理用自己的白话说出,然后就说: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与上面把两例说成是“一例”一样,这也是鲁迅的思想非常难懂之又一例。不读中国书,古代“中国的旧见解”是否与外国书的见解相同就无从知道。中国古人或说东,或说西,并不一律,所谓一阴一阳,决不可能所有的古人都说东,或都说西。除非只有白天(阳)没有黑天(阴),或相反。中国书所谓“东西”,略相当于外国书所谓“存在”。而存在就是矛盾统一,能设想有“东”而无“西”的“存在”吗?如果大家意见本来就一致,皇帝何必要压迫舆论?中国书浩如烟海,绝不是一个人写的,见解当然就不一律。几千年来,写书的人太多,各人的见解不可能统一,一个人的见解,也可能前后不相同,而不问青红皂白将自由表达思想的中国书都付之一炬的秦始皇就只有那么一位。这样,中国文化就既保留了“东”也保留了“西”,也有一些中国书与外国书见解一致。当然,不读就不知道,不就等于没有吗?中国书有关性爱的内容其实并不少,如《诗经》: “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牡丹亭》中杜丽娘说: “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还有《西厢记》、《聊斋志异》、《红楼梦》……,不胜枚举。可是这些书就是不如《红与黑》、《红与白》描写性爱写得直白,敢于直面人生的主题——性欲,所以要多读,中国的书不直面人生主题,而且压制性欲,还是少读为妙。然而,中国古代,主要是明清时期,艳情小说泛滥成灾,是直接描写性欲的,鲁迅作为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专家,对此必然是了解的。当然,这些书都不是好书,更不要读。
第一部分多读外国书(3)
近现代西方人不讳言性,论人必谈性;近现代中国人比较忌讳,但也不是特别忌讳;建国以后的中国人却特别忌讳谈性,尤其是评论中国伟人的中国书,无不讳莫如深,以免获“大不敬”之罪。鲁迅研究尤其是如此。老一代的鲁迅研究者绝不在此事上纠缠,光想一想这件事就会被认为是在亵渎鲁迅,令人手心出汗。以至于普通读者,都不知道鲁迅曾有过一场包办婚姻。即使是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往往也只是在借鉴西方的新词妙语或创造新概念汉语方面下功夫,仍然不太敢往人性方面探讨。但是,外国书告诉我们,非从人性入手,就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一个人。否则读了外国书,连分析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不行,还如何“行”?又如何“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呢?
老一代的鲁迅研究者中,冯雪峰算是比较理解鲁迅的,他在《论〈野草〉》一文中说,《野草》是反映鲁迅内心矛盾的。这只是轻轻点到为止,后来冯雪峰大倒其霉,但也没立即死掉,如果他把鲁迅的“内心矛盾”说明白了,必惨死无疑。在新一代的外国鲁迅研究者中,加拿大人李天明的《难于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是从“人之子”的人性入手,把鲁迅作为真实的人,而非超现实的神来研究的。李天明毕竟是可以用中文写书的外国人,能够理解并可以把鲁迅的内心矛盾揭示出来。这本外国书只是一个开头,还有“接着说”的必要,笔者不过是“接着说”而已。日本人竹内好对于鲁迅传记的疑问、以及鲁迅思想的形成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是没有解答。伊藤虎丸也提出了鲁迅自省的问题,顺着他们的思路研究下去,就可以发现一个新的鲁迅。萧文邦的《鲁迅新传》为人们提供了许多真实的资料,非常可贵。在此基础上认识鲁迅的潜意识,就比较有把握了。因为文章触及了鲁迅研究的一些盲点,故名之曰《新发现的鲁迅》。除了《野草》之外,鲁迅在多处都暗示了自己的“苦衷”。文章写出来了,当然希望有人能读懂,可是人们偏偏不敢读懂,不敢理解,这对于鲁迅也是不公平的。当然肯定会有人以为,这种研究是犯了“大不敬”罪(在以前是该杀头或者该流放的)。这说明人们的思想还没有真正的改革开放(如今人们的思想只有在搞原始积累这一点上是真开放)。鲁迅研究领域一旦改革开放,就可以发现许多阳光照不到的盲点。
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书中最时髦的是心理分析书。弗洛伊德最时髦,议论性压抑对人性的扭曲的文章最能振聋发聩。从这些外国书里,我们知道,性压抑的问题必然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当西方新的性文化传入中国时,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但是却被人们故意掩盖和淡化了。然而谁没有性压抑问题?文艺作品怎么能不说?有些是明说自己,有些则迁怒于祖宗。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革命实践中来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革命青年从反抗自身的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革命实践中得出了非全面彻底地扫除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就不能进步的结论。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谁又不是呢?有着强烈的性压抑感,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彻底的否定,不可避免的要借助于性压抑的反弹力量。
人们在学习鲁迅,全面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却顽固的保留了许多最应该彻底否定的传统,“为尊者讳”只是其中之一。今日,有些人把“为尊者讳”发挥至不可思议的地步,比起阿Q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阿Q“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也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发起怒来……”新的“为尊者讳”就利害多啦,且日益无微不至,无孔不入,旁事不谈,只说鲁迅研究,时至今日,鲁迅研究仍然有大量的盲点。“为尊者讳”这盏鲁迅殿堂中的“长明灯”是什么时候点亮的不好说,但它使鲁迅研究无法再提高和深入则是无疑的。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很多研究鲁迅思想的文章与鲁迅的意思丝毫都不沾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某些分析《野草》的文章。诚然,在鲁迅的文章中,《野草》是最难理解的,鲁迅自称“措词很含糊。”这些含糊之处至今尚未解开,解不开的原因主要是“为尊者讳”的鸵鸟策略导致的“所知障”把我们的智慧给障住了,当然会误解鲁迅。无论如何也要保护那盏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就点起的“为尊者讳长明灯”。
为鲁迅纪念堂重辉庙宇再塑金身的首要前提,就是要熄掉雄踞于在殿堂中央的那盏明亮耀眼的“为尊者讳长明灯”,所以“吉光屯”需要那样的“疯子”。历史发展到今日,“疯子”也能被容忍了吧。
人们的耳朵里,仿佛还留着一种微细沉实的声息——
“熄掉他罢!”(《彷徨?长明灯》)
再说更困难的一个问题: 因为是曲笔,横竖看不懂,就歪曲去理解,对于双方都不公平。实在说,要真正理解他人的思想是不容易的,生吞活剥和简单化是人们常常犯的毛病。关于如何理解他人的思想,遵照“少读中国书主义”,参考“外国书”,英国当代哲学家伯林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具有指导性:
第一部分多读外国书(4)
各种观念的历史是互不相同的。我们也确实力图追寻这些观念的发展轨迹。思想史是我们所认为的人们曾思考什么和感觉什么的历史,这些人都是现实的感性的人,他们不是塑像,也不是各种品质的集合体。设身处地进入思想家们的内心和世界观是必要的,移情也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样做面临证据不足和不确定性,乃至困难重重。在研究马克思的时候,我力图使自己像马克思本人在柏林、在巴黎、在布鲁塞尔和在伦敦那样,思考他的各种概念、范畴及其德语词汇。我研究维柯、赫尔德、赫尔岑、托尔斯泰、索雷尔及其他任何人,都是这样。他们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在什么特定的时间、地点、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他们的思想可能很多人都有同感,但毕竟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你必须不断反问自己,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烦恼?什么东西使他们对这些问题苦苦思索?他们的理论或著作是怎样在他们头脑中成熟的?人们不能完全抽象地超历史地谈论各种思想;但是,人们也不能孤立地仅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描述各种思想,好像这些思想在它们的框架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似的。正如你看到的,这是一种复杂的、含糊不清的、需要借助心理学视野以及丰富想象力的研究工作,它不可能获得什么必然性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只能达到高度的持之有故和言之成理,达到理智能力的首尾一贯和清楚明白,还有独创性和有效性。《伯林谈话录》: 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显然,伯林也是提倡“知人论世”的,他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 是什么东西让鲁迅烦恼?什么东西使鲁迅苦苦思索从而得出了全面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少读中国书主义”?鲁迅的著作是怎样在他头脑中成熟的?伯林所使用的方法,也是本书所使用的方法: 要避免“抽象地超历史地谈论”鲁迅的思想,就要把鲁迅作为一个“现实的感性的人”,而非“塑像”看待,找出一个在我们的研究中充当引导的第一原因和客观的进路。外国书常用的“知人论性”的研究方法,确实是研究鲁迅最实际的一条进路。从鲁迅的家庭关系入手,直面人生——鲁迅的潜意识,沿着鲁迅的包办婚姻这一条路经逐渐进到鲁迅的内心世界;从鲁迅的婚姻状况深入到鲁迅的文化观——“少读中国书主义”。为此就必须充分地理解包办婚姻在鲁迅生活中的意义,否则要想理解鲁迅的思想就很难。“但是,人们也不能孤立地仅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描述各种思想,好像这些思想在它们的框架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似的。”鲁迅的包办婚姻和性压抑并非鲁迅个人的痛苦,鲁迅由此而产生的思想,在他的思想框架之外具有巨大的意义,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乃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搞清楚鲁迅思想的来龙去脉就不是一件与实际人生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