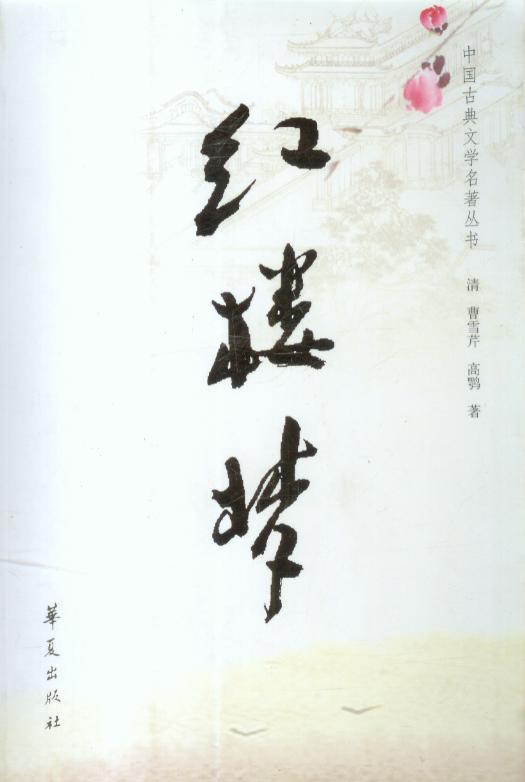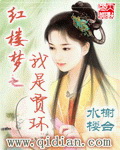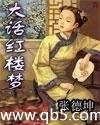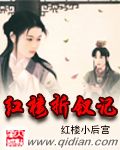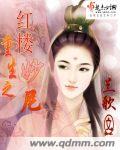定是红楼梦里人-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就要从秦可卿说起——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二百年来,人们就被“淫”(“爬灰”……)瞒蔽住了,以为“不肖”,是指声色享乐、不务正业一类意义,不知那指当时的“政治罪名”:指的是“行为不端”,“结交匪类”,“奸党”等等用语。
这事本是说来话长。幸而近年作家刘心武先生已然把内幕焦点抉示出来了,他说:秦可卿出身不凡,是皇族之女;从养生堂抱来云云是托词假话:她出丧大殡礼仪之重,决非一个宁府长孙媳所能承当享受,看看那诸王路祭的场面,六宫都太监吊唁的特异,皆可表明另有内幕真情。(此为大意,刘先生著述具在,兹目坏恕难详引)。
刘先生此说出后,纷纷诘难,我却觉得应当给以重视,深入研究,不要轻心率意,即泼冷水。
最近,这个问题的局面获得了巨大进展,步步走向接触了历史真相的核心。
原来,曹家的第二次抄家由弘皙“逆案”株连,正是远从康熙太子胤礽之被废、雍正夺嫡引起。雪芹小说中的“世袭”,实指曹家是玄烨康熙与其太子胤礽的两代保育嬷嬷的内务府世家。书中“荣禧堂”金字是康熙御笔,而匾下对联银字,正是东宫太子的赐书!
秦氏亡故,贾珍一定要用“义忠亲王老千岁”留下的“樯木”棺木,贾政说是此非“常人”所用,已妙笔点醒真相了!
再看,可卿“托梦”对凤姐所说的一夕秘谈,岂是“常人”所能预见而有此身份口气?——“天香楼”分明透露了可卿本是“天香云外飘”的皇家之女,应即胤礽之长子弘皙的幼女,遭事后隐名寄身于曹家老保母之家。
这么一讲,即可恍然:所谓的“淫”,是“泛滥”之本义,是掩盖政治原由的特殊用词——倘不如此,当时读者尤其皇族内廷,一眼就看懂,而灭门之祸就不可或免了。
贾珍的“不肖”,祖宗的“异兆悲音”,全系于此,却用了当时一般宦家王族的享乐生活的“过失”来迷惑了读者心眼与追究的兴致。
所以,张爱玲的卓见是非凡的。
再看主管这件大丧礼的是谁?是特请的王熙凤。是因为她的才干胜于尤氏吗?表面似是,实则是要西府的主家内眷。这都是文心匠意,内有藏掖,不可用一般小说的眼光来衡量评议。
一部《红楼》的家亡人散,由这儿伏下大脉络,也就是全部的关键所在。
诗曰:
此情不是一般情,几代渊源死与生。
看到家亡人散后,始知东府事非轻。
第四部分第四十一篇 张爱玲与胡风
张爱玲,间世之奇才,尚不知文坛评界认为谁可与之比肩?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有吗?
看她文萃风格,其为人绝不轻狂,也非“神经质”,出言落笔,各有分寸。因此,她对高鹗下的评语,益发令我“如雷震耳”,她说了两句惊倒世人的话,一次说:高续《红楼》是
狗尾续貂
再次说,高鹗相附在雪芹书上,已成
附骨之疽
三次说:
高鹗死有馀辜!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轻轻松松的话。她无法“克制”了,如鲠在喉,不吐是忍受不住了。
这已不再是“风波”“情面”的事,要动“真格的”,势不两立了。
这让我感叹,让我喝彩,让我下拜。从清乾隆辛亥、壬子以来,不曾有哪位英雄伟士说过类似的话?
这不由我一提胡风先生。胡风是第一个敢说高鹗之伪续是“居心叵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骗局”。
我当然也想起我自己:对高书说过几句失敬的话,就有人批评,这是“偏激”;也因此使某些专家教授怀恨在心,百计为之“报复”。不知这些尊高贬曹的“红学家”看了张女士和胡风先生的话,又作何感想?
谁也不与原作者伪续者沾亲带故,谁也更不与他们是“前世冤家”。使张爱玲以及胡风说出那样话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思之思之,悟乎悟乎?
糟蹋中华民族珍宝,是最不可恕的亵渎和犯罪。附骨之疽可以而必须切除、消毒,并防止复发。最大骗局,岂可不暴光?受了蒙蔽的读者无过,他们有朝一日也会觉察,不会把假丑恶当成真善美。
至于熙凤之女,巧姐儿与大姐儿是一是二,专家也成了争议之题;她引了《金瓶梅》的例证,数语可决:巧姐是专定乳名,大姐是称女儿的泛词,何来矛盾?(写得忽“大”忽“小”,与此无干,是行文的问题)。故我亦不再赘说。
张爱玲对任何问题都不放过,如马道婆话激赵姨娘,早本说的是她受“折磨”,后本改了“委屈”。哪个对?其实,“折磨”并不定指“酷刑拷打”,完全可用来形容处境的难处。“委屈”倒没什么了不起了,大家庭人多势杂,谁无委屈?
校勘之事最难,要有“咬文嚼字”的耐心明眼,更要有语文文化多方面的知识见解。通情达理,方能做到字斟句酌。不能宏通博达,也会造成比较取舍上的失误,好的丢了,以为所有“修改”就定胜于初——这构不成一条定律。
以上的话,是我触事抒感,并非批评张女士。她没有一概重视后改之意。读者幸垂明鉴。
诗曰:
出语惊人总为何?岂同私撼肆仇訶?
中华自有连城壁,泥陷污途恨几多。
第四部分第四十二篇 怡红院里众丫鬟
袭人这个大丫鬟,是历来最为人唾骂的角色。人们认为她最奸坏,最无品,伪善杀人瞒哄宝玉……,几乎集众恶于一身,罪不容赦。张爱玲却没受这种成见的影响,倒有点儿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的气概。
她举了程本如何一再改动文字,有意损坏袭人的形象。她又解读《芙蓉女儿诔》中痛骂的“詖奴”“悍妇”与袭人无涉,是指王善保家的这个奸谗之人。
可知她的心田仁善,不肯从俗冤屈一个无辜者。功德无量。
她自言小时侯爱看戏,台上出来一个人,必先问是好人还是坏人?——自笑这种幼稚的观念,不懂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不能机械地划分阴阳界限。这大约也是从一个小说作者的立足点而如此自白的。这也可能是她并不诟骂讥贬袭人的缘故。
另有一个现象,却值得讨论——
《红楼》十二钗,数止十二,称为正钗,而96名副钗者,全是丫鬟,到书之后半部都有相应的乃至重要的情节故事,非同虚文陪衬,而张爱玲对这么多的女儿着语无多,就连鸳鸯、平儿、紫娟等也未蒙多及。细一统计,原来她着意的都集中在怡红院中之诸鬟。计有袭人、晴雯、麝月、檀云,以至遭撵逐的茜雪,被排挤的小红,她都表示了兴趣,给予了笔墨。
这应如何解释?殊耐人思。
如果不是我过求“甚解”,那么是否这现象所反映的,正是张爱玲表面不多言的男主人公贾公子宝玉。
围绕宝玉的这些女儿的种种,受到关注,也就是宝玉受到的关注。
这一点,似乎正是张爱玲的心理深层的折射。
与此不无关联的一题则是脂砚。张爱玲已然确认这个批书人是一位女性,并书中人的一个“原型”,十分重要;可是她对这位“同道”却也未曾表露出足够的兴趣。她运用脂批,限于可以为其“大拆迁”“大搬家”论点,帮忙支离的那几条(而且加上误读和错觉)。至于脂砚的大量重要见解,尤其艺术审美的流露,文心匠意的指点,似乎都不在张爱玲的兴趣之内。
这很奇怪。因为她自幼酷爱各种艺术,而且精通熟悉。她对脂砚的“画论”——以画法比喻雪芹的笔法名目甚多,又如“伏线千里”的极大特点与重要作用,她也未曾充分研讨——似乎感觉上并不那么敏锐。
这都与她的天赋才能不太符合。
复次,我对张爱玲的“古文”(即中国古代语文、文学,包括诸般文赋、诗、词、曲等不同文体)造诣毕竟如何?未曾得见,无从评判。她虽说过,自己“受古文的毒太深”,行文之时省一个字也是好的。若从这句话看,其领会感受甚深,恐怕胜过一力主张“白话化”的那些先生。
“词寡而理长,语近而意远”,这是中华传统语文的一大特色与优长,而一味只懂“白话”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没法“对话”与“共识”。读《红楼梦》而不精通所谓的“古文”,以西方的语文标准来绳量曹雪芹的文笔手法,词语铸造,就会南辕北辙。可惜,张爱玲在版本研究上,只注意“老、嫽、姥”和“旷、(彳狂,一个字)、逛”等用字异写的稿本早晚先后,却不讲哪个本子的文字风格是接近雪芹真笔,或哪些片段是后人添加的。
在这些方面,她表现得不充分,不完足,甚至显得轻率与盲从(别人)。
然而,“新红学”已历百年了。百年之间“红学家”如过江之鲫,却极少女性真学者。在我心目中,只能仍推张爱玲为个中佼佼,超迈等伦。这就倍觉此人之可贵,多作苛求,即不公允了。
诗曰:
百年多少自称家,学识如何有等差。
若论女流真拔萃,爱玲才器冠中华。
第四部分第四十三篇 崭新的创见
遍观张爱玲的红学见解,其中最新鲜、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她认为湘云是原来“早稿”的主角,但后来将二十回以前的故事“全删”了(直到第二十一回突然上场)。
这一点已然奇了。谁知更奇的是她又认为林黛玉这个人物原先没有,是后来由湘云“分化”出来的!
也就是说:湘云是写实的,黛玉却是虚构的。
这个现象,怕是别人所绝未道过的新意趣、新“方法”吧?
假使如她所解,那就是作者雪芹由于历史实际上的种种复杂原由(非今日的我们通过简单表面的“考证”所能知),而不便直写他与湘云的自幼真情,故此“化”出另一位“表妹”,借她来写二人的感情。
又假使是如此,那么等到作者一旦“借”写的目的达到了,就只得安排一个黛玉早亡的构局而将她“交代”了,以便将真实笔墨“移交”给湘云本人。
那么,书中到了第七十八回中秋联句,黛、湘独在,宝钗退避,她二人一虚一实,幻为奇文——这方是艺术,这方是“创作”——然而,依然真实目标还是“自传”:情节素材的主体还是雪芹与脂砚的——所谓“一芹一脂”,所谓“余二人”的脂批的亲昵语气,一一得到了诠释解读,恍然如“梦”之觉醒。
岂不快哉!岂不幸哉!
张爱玲的文笔风格、讲话方式,与我甚异;我今为之加注、加讲,申明她含而不往下说的话言,使今日读者豁然开朗,出了迷洞,世界光明,这不算我饶舌多事吧?
再重说一次:
所谓“自传说”的本意,是“写自身的创作”,相对于“写别人的创作”而言;从未有与“创作”艺术成分互不两立的任何念头。麻烦并不出在“自传说”者这一方面,是出在误解、不明的那一方面。纷纷扰扰,纠缠了这么多年。
这番意思,我在上世纪40年代创《红楼梦新证》时,已然说得够清楚了。我说:雪芹的书是“写实”,但穿插拆借,渲染点缀,乃小说家之故常,本不在话下。何必絮絮赘云……。
张爱玲之内心本衷,不能不承认“一芹一脂”的史实真理,意义深刻。
这可使一些“弄左性”硬不承认的评论者寻味一下,要不断重新反思,以求真实。
诗曰:
黛玉原来属子虚,雪芹何以有为无?
湘云方是真脂砚,失乐园曾绘画图。
'副篇'字体与正文区别一下
张爱玲的“大拆迁”“大搬家”论,受了吴世昌的影响,而且十分严重。其实吴的论点是需要推敲的。如前文已举,他说第五十八回老太妃之薨本是元春的事——元春在八十回前那么早就亡故了……不知老太妃之薨是史实,是乾隆二年正月的事,太妃是康熙老皇帝的庶妃(后封熙)嫔者也,与元春之死于乾隆四五年间,纯属风马牛不相及。
又如吴氏非说秦可卿之死原在“最后”,现存文本是“移前”了,云云。其理由何在?不过只是十二钗册子排次秦氏居末罢了。殊秦氏之居末,只是因为她乃“家亡”“人散”两大线路的兼“并行关系”人,即:她一方面是托梦于凤姐的家亡人散警示者,同时又是与宝玉关系非常的重要人物——如把她排在钗、黛、元、探、湘、妙之后,则只与“人散”相连;如排在凤、纨、元、迎、惜、巧之后,则又与宝玉人散一方关系不切。故此只得排于末后。然而这与死亡的迟早又有何交涉乎?
这种臆说猜想,却使得张爱玲上了当,营造出大量的“搬家”论来。
话要公道,她对吴亦非句句采纳。例如,吴见《甲戌本》有一批云: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余(今)赌新怀旧,故仍因之。
吴氏据此,遂断言脂砚“保留”了《风月宝鉴》中的每回的“小序”——即变为“回前批”者是也,云云。张爱玲就不大赞同这个“小序”论。
其实,经典中如《毛诗》,有大序与小序,小序即每篇诗的注解形式;至于小说,从来也没听说还有什么“大”序与“小”序,这不过是他一己的论点,但他却作诗说:“棠村小序分明在,红学专家苦未知!”(有人和韵云:“棠村小序何尝在?红学专家一笑知。”亦红坛掌故。)
在此不妨顺便说说拙见。
《风月宝鉴》之名,为“东鲁孔梅溪”所题——即是“其弟棠村序也”,此为一事两见,词字稍变而已。盖作序的,即是题名的:棠村者,即是梅溪之又一别署而已。
是故,脂砚所云“故仍因之”,就是仍存其书名,以表“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