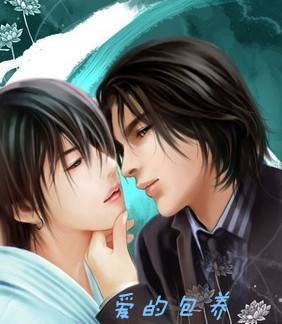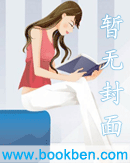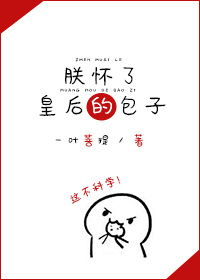复旦的包法利夫人-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撞击发出的声响、钞票的沙沙声、学生们热烈的讨论声,犹如“雄军百万,铁骑纵横,呼号震天,如雷如霆也。”
偶尔有“黑猫”冲来,那种鸡飞狗跳,更是惊心动魄,给人以眼前有千军万马激烈厮杀之感,高潮就在此刻出现。好在小贩们都是身经百战,老于沙场的,也不惧怕,等人一走,照样围拢过来。据说年年红的老板当年就在这里卖盒饭起家,如今也是盘了好几个店堂,小饭馆在复旦有了点小名气,据说有一阵子王沪宁也常常去吃呢。
第一部分 古典民乐系列《十面埋伏》之图书馆(2)
其实喧闹的不仅是图书馆的外围,更激烈的战争在馆内。当你一大清早,冒着严寒爬出温暖的被窝,在瑟瑟冷风中赶到,这里已是围了水泄不通的人。阅览室的门一打开,立即听到怦怦的声响,那是书被扔到桌上所发出,好不壮观的景象。
他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
等到大门轰然关闭/却发现这里是地狱
到处都是路/我只是拒绝选择
有一段时间,文图迫不得已禁止带书入内,阅览室内喧嚣顿平,BBS上则余波不息。复旦人的雄辩传统在这里开始展现。某个id发贴曰“两发炮弹炮轰图书馆”,要求允许带书包和水进入。辩论的焦点很快从阅览室的功用延伸出去,部分人认为既然阅览室事实上已成自习室,就应该给同学提供更大的方便。因为“同学们方便啦,自在啦,感觉心情舒畅啦,这可能并不很大的快乐一旦象阳光一样洒到每个人的身上,起了‘蝴蝶效应’,整个上海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不能说不因此而有所改变。”
反对的声音很快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有人举例反问,法律禁止杀人,但每天还是那么多人被杀,根本禁止不了,是不是应该取消法律,让大家都来杀人,爱怎么杀就怎么杀呢?也有人从正面攻击,制定规则,应有“公心”,每个人的利益都要包含进去,还要考虑长远影响和连锁反应,如果承认图书馆等同自修教室,一系列想不到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
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居然有同学就此做起论文,建立了一个以收益(效用)为自变量的供需模型,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论证图书馆制度的利弊,即如何才能使得成本最低而效用最大。这一点我觉得是复旦真正的精神所在,我们总是从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里提到的钱,不是利滚利,而是实际熨帖的,让人活得舒适而体面的那种。
不知道是从生命的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逐渐远离了自己的梦想,走上一条被生活慢慢淹没的道路。起先,看书是为了摆脱孤独,让自己不至于堕落的太快,但后来,阅读就不仅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图书馆是如此地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没有好好呆过图书馆的学生就不是优秀的大学生。
文科馆前面的那条马路到了晚上,会一改白天的喧哗,变得很安静。夜里的图书馆亮着灯,脚步声轻微,震动那些铁书架,那些陈旧的书本,泛黄了,和灰尘肩并着肩,坐在一起,像一群长者。带着他们无人阅读的青春,听着窗外杨树的叶子,被风翻动。人一个一个,在夜的笼罩下,剔落出来。在这样的时刻,人心里有一种冲动,象是英雄末路的悲凉,仿佛曾经激昂一时的音乐逐渐丧失了旋律性,零零落落的节奏,如同马蹄声,渐渐远去。
第一部分 古典民乐系列《梅花三弄》在人间(1)
黄鹤楼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李白
复旦最美的是相辉堂前的草坪,不开心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去草地上走走,感受那份柔软、那份踏实和轻松。慢慢地躺到草地上,嘴里咬着草叶,闻到青草蓬勃的香味,睁开眼睛,定定地看天上的云彩。保持这个姿势开始遐想,天空中有大鸟或飞机掠过,它们的鸣叫把我从彼岸拽回来。思路打开,空灵而透彻。
在毕业的前夕,我独自一人来到相辉堂,最后一次以同样的姿势仰卧,看天色慢慢由湛蓝到橙红再到淡黑,草坪由碧绿转向灰暗,人由纷繁变为寂寥。在我散焦的视野中,各种影象交替更换。我一个人,在一处熟悉的地方,认真举行一场恋恋不舍的告别仪式。
在朦胧中,我仿佛已经看到我无忧无虑的青春正在转过身子离我而去,如天真孩子般决绝。脸上不知什么时候有些润湿,我下意识地竖起双腿遮挡前方,尽管这个时候,相辉堂已没有什么人了,只有偶尔往返的自行车发出俏皮的口哨声。
让我们一代一代人津津乐道的相辉堂其实是普通的一幢两层楼建筑,青瓦白砖、红色窗格,房子很有些旧,加上从来不在外面装修,以至于曾经被人调侃说象是一个厕所。楼梯在外面,左右一边一个,看上去正好男女分开。楼梯下是一个商店,买各种各样的文具和生活用品,非典的时候还卖过点口罩。
相辉堂正面是校园里最大的一块草坪,一些大型的仪式都选在这里进行。相辉堂前草青青,它串起了每个复旦学子的光华四年。大一时,在这里召开入学典礼;大四时,在这里举行毕业典礼。同样悠扬的校歌,几乎没有改变的青春面庞,孩子的心却从期待变为了沉重。
每一个新生都会有在相辉堂前徜徉的足迹,在其中坐下来喝彩的日子。日日月月的交替,上演不同的戏,在这个复旦人永远无法忘怀的地方。每当华灯初上,它就成为校园里最浪漫的所在。几乎每个谈过恋爱的人都有一段关于相辉堂的歌声、月色的回忆。
相辉堂曾因风靡一时的先锋话剧和小柯的现代舞成为充满文化气息的圣堂。我个人总是感到,相辉堂在本质上,是一个让人思考的地方,而与娱乐无关。那些戏剧或者舞蹈,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
第一部分 古典民乐系列《梅花三弄》在人间(2)
有时候,最好的戏剧甚至不在这里上演,而是在它外面的草坪上。我曾经在那里听过世上最美的曲子,洞箫演奏的 《梅花三弄》。洞箫是一个奇怪的乐器,它只适合于独奏,声音暗哑凄凉,术语称为咽,听了却让人莫名的放松。
那是一个炎热的五月,草坪上照例坐满了闲散的人群。在这种时候,听洞箫让人感觉有些滑稽。他们大声的笑,盖住了微弱的声息,我在断续中吸收那些光和影,放进自己的记忆。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停了下来,乐声也嘎然而止,一切都归于沉寂。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在日积月累着孤单,时时像有受伤的鸟飞过,黑色的翅膀在挣扎叹息。表面上的荣耀根本无法挽救我们的堕落,我们必须退回去,到古老的世界去寻找生命的真谛,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古典的原因。
前卫先锋的戏剧说穿了也不过如此,它在另一个形式下回归经典。比如我们现在,在草地上,喝着啤酒,抽着烟,大声的说笑。可我们的心里,却曾经那么渴望,看见雪地上的梅花,孤独地开放。霜晨雪夜,草木凋零,只有梅花傲然挺立,静静开放,将它清幽的芳香散溢于人间。
梅花每个人都喜爱,而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于是我们就改变了它,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它的钟爱。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爱得深沉。生命象鲜花一样美好,爱象阳光一样动人,真实象岩石一样坚固,良知象野草一样劲生,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在大学里第一次,等流星雨来临的那个夜晚,自己是在相辉堂前的草地上度过的,那是个喧闹的夜晚。而如今,草坪上,弧形的,摆得整齐的,照集体相的椅子和木板阶,没有人,显得那么空旷和孤单。我知道,一定有人刚刚离去,带着兴奋与感伤。一定还会有人再来,相辉堂前,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枯坐在相辉堂前的月亮里,月亮撒了一地的哭。我看到那些边流泪边徘徊在阴影边缘的孩子,看到他们背后拖着的情节相似的长长故事,看到那些孩子把故事慢慢的用自己的方式表述出来。年轻脆弱的青春,如拉环一样轻轻折断,而喷涌开的是,泡沫般的激情。“从东到西 94 步,从西到东 93 步”。临走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丈量草地的孩子说。
第一部分 古典民乐系列《春江花月夜》之游园惊梦(燕园、曦园)
昨夜闲潭梦落花
可怜春半不还家。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在复旦待了若干年,也分不清燕园和曦园的人不少,比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以为有桥的地方应该是曦园。这两个园子看上去也没有多大差别,燕园的出名,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它有出典,据说该园业主原姓谢,之前又为王氏富商所有,故此园历王、谢二姓,唐人刘禹锡有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燕园以此命名,隐喻历史变迁之意;二是它与北大燕园同名;三则是名噪一时的燕园剧社,给它长了人气。
就我个人而言,更喜欢曦园,曾经在那里的一块墙壁上,发现过苏老的题诗:“超然此地一亭台,缦缦卿云复旦来……”。暮春时节,校园里到处是白花红叶的树,这树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红叶李。曦园里的红叶李是长得最美的,开花时节,那纷纷扬扬、满天花雨的落地无声总让我想起黛玉葬花的情景。
那里的水不好,绿得耀眼,仿佛沉淀了太多的秘密。某一天,我看到曦园那一潭死水中冒出一朵洁白的莲。田田的莲叶当中,盛开着一朵直径约十二三厘米的睡莲,她那细长细长的花瓣在末梢,以优美的弧线收拢成尖尖的细巧的角,纯白的花瓣,让人感到绝世的清纯,忍不住想用生命去呵护她。
燕园则适合在傍晚的时候去,轮廓渐渐隐没,光线一点点弱下去,不是消失,是一丝丝抽去。风轻微地掠过我们身边,拂过树叶,拂过恋人的相偎,静静地锁住一棵树。恩恩怨怨、纠缠不清的紫藤长在水边,爬过长岸,褐色的茎干象是长了褐色的眼睛,在夜幕中闪烁。凸凸凹凹的石头路上,一声一声的听见伊人远去。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园
——《游园惊梦》
其实,复旦园没有什么特色,这是事实,但不是真理,就象人人对于生活有不同的注解一样。费尔南多·佩索拉曾经说过:“跋涉就是一切,生活是没有的。”跋涉就是改变,是一种过程,而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缺乏本质,我们永远在路上。
这些年,复旦每年都是改造,曦园和燕园一年比一年沉默,当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精彩。能够一身清闲、了无牵挂,有闲情和时间到这里来走走的人越来越少了。新建的叶耀珍楼惊醒了沉寂中的曦园,超市里花花绿绿的商品遮盖了小园的清翠,而燕园由于偏安一隅,甚至已经被某些人渐渐遗忘,门楣后“弦歌”二字黯然无色,几乎要让人辨认不出。
围墙打破,一点一滴的绿在市政工程建设中逐渐逸出,和着校园里每年涌出的那些孩子。都说遗忘过去等于背叛,可怕的是,也许我们根本没有过去。曾经拥有的那些,连做一个梦都不够资格。大声朗读的学子、轻轻起舞的老师、夜尖上带着小露珠的小草、还有那些欢乐的鸟儿不时发出的声声脆鸣,原来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在梦中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并不快乐,可是梦醒了,却越添凄凉。
孤独一个人徘徊于园中时,是很可以制造一些可怖的肃杀气氛的。一块不大的草坪加上它的边界,假山很平常。有几个有点模样的石头立在那儿,孤嶙嶙的,没一点儿气势。也许就是这些,真正感动了我。在这个到处是车嘶灯闪、物欲横流的都市中,在那些日夜颠倒、变幻莫测的宿舍外,还能有这么一个地方存在,让人感到寂寥。
巴赫金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在城市里,人的声音盖过了一切,欲望太多而理想太少,人的精神太忙碌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当人人都在为了现实的目标在努力的时候,唯有停下来的人是一个定点,作为坐标来衡量这个世界。也许我们是应该好好歇一歇,比如睡下来,在梦中听音乐。
每一次/小小的失误
都有可能让你跌入无底深渊/万劫不复
你听/筝的历音技法正在制造一个又一个旋涡
睡吧/像白痴一样的睡去
把失眠的耳朵交给箫、琵琶和筝
第一部分 古典民乐系列《广陵散》之绝唱(主席像)(1)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骆宾王《易水送别》
我跟网友在复旦见面有一个固定的地点,校园中最有气魄的地方——主席像下,它目标大,容易辨别。现在很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可能是拜卫慧的《上海宝贝》所赐。倪可就是在像背后,被那个身高不足5英尺半,长相平平的男人所诱惑,开始她的性爱旅程。
在我入学的时候,主席像还没有被这样亵渎过,对我们那一代而言,它是一个神圣之地。主席像的背后是旗杆,虽然我从不看升旗,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升旗,可光那一种凛然的正气,就让人走过时不得不打个寒战,肃穆起来。
在以小资著称的复旦说这种话,可能要被人骂矫情,但我无所谓。像我这样冷淡的女子,早就听惯了别人说我是冷血动物、阅人无数,逐渐丧失了感动,更谈不上敬畏。忘了是哪个哲人说过,一个人若是没有了敬畏之心,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了。
在得知我要远赴西藏的时候,中文系以说话幽默著称的傅杰老师对我有一个评价,说我是亡命之徒,但我非常惭愧的感到,我离他的恭维还很有距离。这表现在,我对某些东西,还不敢完全否定,比如主席像这样的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