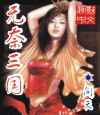爱也无奈 作者:叶辛-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揣起,看完跳地戏,回到雨山屯屋头,关起门细细看。留神,就你一个人看。看的时候,打好满满一盆水,放进去再试试。”吴远贤说的话,就像在打谜语,让我边听边猜,也不知所以然,他呢,一点也不管我听没听懂,摆一下手,轻描淡写地说,“你敢于在大庭广众面前救护小女,足见你心地善良,好人,好人哪。这年头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见了。就这样吧,其他的一切,都等明天小女出嫁之后,到石碉来,我再告诉你。”
说着,他看着我把纸包揣进衣兜里,走到门前,把门打开,让我出去。
重新来到叶子烟雾缭绕的院坝里,耳里闻着嘁嘁喳喳的谈笑声,眼里望着一张张黝黑的皱纹满布的农人们的脸,有熟悉的,也有不那么熟悉的,我忽然觉得,这雾岚山下,缠溪两岸的乡间,有了一点儿神秘感。插队几年,和老少乡亲们朝夕相处,自以为对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已经都晓得了。谁知,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啊。
夜半时分,地戏跳起来了。
那真没冤枉我等了几个小时,活到二十多岁,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表演,而且我觉得,这跳神,和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封建迷信大不一样。
在吴远贤吹响牛角,挥动法器的指挥之下,一个个脸戴面具、身着战袍的汉子,就在院
坝里跳了起来。
吴远贤口中念念有词,起先听不明他说些啥子,挨得他近一些时,他的声音就听清楚了:
年年风雨顺,
田坝谷米香。
主人勤耕种,
抬米入新仓。
远贤今嫁女,
饭甑四乡开。
鱼肥酒肉美,
寨邻好情意……
随着他嘴里越念越快,节奏感也越来越强。稀奇的是,站在台阶上、屋檐下围观的寨邻乡亲们,也都随着他的节奏,有板有眼、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唱得兴奋处,他们也跟着拍掌跺脚,喜笑颜开。
锣敲着,鼓击着,还有人拨动着月琴,刹那间,吴远贤家小小的院坝,成了欢腾雀跃的娱乐场。
最为吸引我的,还是跳地戏的汉子们戴的面具,这些造型奇特、和头盔相连的一只只面具,有的油刷得五颜六色,有的就取丁香木和白杨木的本色,雕法粗犷,线条有力、夸张,着了色彩的无不对比强烈。有的还在额头中央镶嵌了小小的镜子。
“华老师,好看吗?”一片喧嚣声中,吴仁萍不知什么时候挤到了我的身边问。
“好看好看。”我一边使劲鼓掌一边说,“我从来也没看见过。他们戴的面具,为啥有的涂颜色,有的不涂色?”
“听老人们说的,不涂色的是明朝时期的雕法,涂了颜色的是清朝以后的做法。”趁着和我说话的当儿,吴仁萍紧紧地贴在我身上。
天哪,这么说,几百年,历史是相当悠久了。
“奇怪,我到老乡家去,咋个就没见他们家中放的面具呢?”我不由好奇地问道。
“让你看到还行啊,”吴仁萍凑近我耳边说,“闹起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烧了多少面具啊,真正造孽!老人们说,怪不得我们一年比一年过得穷,那都是不跳地戏造的孽呀!华老师,我亲眼见的,在大院坝里,整整烧了一天一夜,还在冒烟。胆子大些不烧的,也都藏起来了呀。”
“跳地戏时,不戴面具多好。”我想当然地道,“演员脸上的表情,不是比面具更丰富生动嘛!”
“这你就不懂了,”吴仁萍脸挨得我很近地说,“我们这地方有一句话,叫做戴上脸子是神,脱下脸子是人。面具就是神灵,是我们的心灵里头想象出来的。”
我不由转过脸去,望着这个大年龄的、作业经常做错、时常留级的姑娘。她这当儿讲出的话,哪像是没多少文化的学生讲出来的呀。
多少年以后,我插队山乡的地戏传遍了全国,唱到了外国,中外学者都把它当作一种稀有的文化现象——“戏剧的活化石”来研究,我也对地戏逐渐有了深入的了解,这才晓得,西南山乡,高原和山地面积占了将近百分之九十,自古以来,群山连绵、沟壑纵横,老百姓的村村寨寨,都分布在崇山峻岭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坝旁,山川阻隔,遥远荒蛮,偏僻而又闭塞,使得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能和外界有广泛的接触,甚至于基本上不和外界接触。但是对于众多的自然现象,对于人一辈子都要遭逢到的种种困苦灾难及不可理解的事物,这里的乡民们也需要得到解释。还有一点更为重要,那就是作为人,他们也像生活在全世界各地的所有民族一样,期待美好的生活,巴望着有朝一日真正能过上好日子。可是他们真不晓得怎么做才能迎接到这样美好的未来,朝朝代代,生生息息,他们都是求助于跳神戏来驱除邪恶、驱逐疫鬼、纳吉许愿,这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形式。
纯朴的乡民把村寨的兴旺和衰落,吉凶祸福,都和跳地戏联系起来。地戏在乡民们的心理上成了能过上好日子的支柱。
不过这些道理我都是在好些年之后才明白的,在当时,我只是随着手舞足蹈、又吹又打、又唱又叫的老乡们沉浸在一片祥和欢乐的气氛中,并且有吴仁萍这么个相好的姑娘站在我的身边而高兴。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吴仁萍一无所求地把她自己给了我,也是间接地对命运排定她的角色的一种抗争,她要自主地替自己做一回主、发泄一回。尽管她自己,不一定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命运注定了这一天让我终生难忘。
看完地戏回到知青点茅草屋里,夜深人静,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吴远贤交给我的纸包。想看明白,他说的国宝,究竟是个啥玩意。
到了下半夜,雨山屯上的电反而足一些,十五支光的电灯泡,把呈现在我面前的两只青蛙照得晶莹透亮。要不是在我的衣兜里已经揣了那么长时间,我真的会认为这是两只田里头刚刚抓来的活青蛙。
那么晶亮,那么剔透,青蛙的皮肤上像沾了水滴,青蛙的两只鼓鼓的眼睛就像瞪视着我会转动,还有那微张的嘴和嘴巴里的舌头,就像随时准备探出来吸食蚊虫一般。
姿势是那么生动,线条是那么流畅。细观之下,石色明净,石质细腻,温润如玉的肌理就仿佛是青蛙的皮肤。
最难得的是这两只栩栩如生的青蛙,明明是玉雕的,却一点也看不出雕琢的痕迹。青蛙背上的斑点是如此逼真,一雄一雌,互相呼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只青蛙神形兼备,手轻摸上去就有种惟恐它们会受惊跳起来的感觉。真正触摸着它了,却又会感到光洁细嫩,有一股凉凉的温润细腻之感。
真是人见人爱的宝贝,真是稀世难见的神物。
再不识货的人,都会知道它们是国宝。
我忽然想起了吴远贤的叮嘱,把两只青蛙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转身用一只大盆打了一盆水来。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把两只青蛙放进水中的时候,两只玉青蛙竟然像真青蛙一样游动起来。而当我津津有味地欣赏着青蛙舒展着四肢游泳的姿势时,两只青蛙分别发出了清晰的鸣叫声“呱、呱呱”。啊呀,这哪像是玉蛙鸣叫的声气啊,完完全全就和山野田坝的青蛙叫声一模一样。
骇然把我吓了一跳。
我脑壳里闪现出了一个词眼:价值连城。
这一夜,我失眠了。虽说入睡已是下半夜,虽说喝喜酒、看跳地戏折腾了整整一天,虽说还和吴仁萍之间发生了平生头一次的性事,应该是很累很疲倦了。可我就是睡不着,浑身上下好似有一团火在燃烧,脑壳里亢奋得直发热,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盖着被子嫌热,掀去被子又觉得冷,总感到枕头没放好,一会儿猜测着这一对青蛙的来历,一会儿生怕这对青蛙没放好,一会儿想象着这对青蛙究竟该值多少钱,一会儿费神地思索着,为什么人们传得纷纷扬扬的国宝皇帝的宝剑,却变成了一对青蛙。
可以说我什么都想了,惟独没想到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个训诫,如此精美绝伦的宝物,谁个持有了它,就会给那个人带来灾祸和凶兆。
雨山屯头遍鸡啼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梦中仿佛还听到送亲的队伍把唢呐吹得连天震响,仿佛还夹杂着歌声和哭声。我脑壳里头还闪过一个念头,吴玲娣出嫁了。
一觉睡醒起来,雨山屯浸染在秋冬之交混沌的雾岚之中。山脚下的田坝、山岭上的坡土、一片片的树林、偌大的草坡,还有曲曲弯弯的缠溪两岸,全都笼罩在浓浓的蒙纱雾里。是昨夜闹得太晚了,是雨山屯团转的几个寨子都贪看了跳地戏,村村寨寨一片梦一般的沉寂。
这难得的清静正合我意,我匆匆刷牙洗脸过后,随便刨了几口泡饭,就往寨子外雾岚山上的石碉赶去。
雨山屯外的石碉石堡,是雾岚山上的一处古迹。据说有好几百年历史了,爬上山去,得攀登一百几十级石阶,没多大的事情,寨邻乡亲们都懒得去费这力气。可在雨山屯团转,哪个都晓得,吴远贤是石碉、石堡的看山人。有事没事,他总在山坡上转悠。有时候人们费了老大的劲儿,攀上山去,走进神秘幽暗的石碉、石堡,遍找都不见他的身影。可当你一旦离开石阶,在山林里东钻西钻乱转着的时候,他又会悄没声息地出现在你的跟前。
今早晨是他约了我,我不怕见不着他,我怕的只是他还在岚山屯寨子上睡觉,没来得及赶上山来。昨晚上毕竟是他嫁女儿的日子,况且他还自始至终主持着跳地戏,一会儿吹响牛角号,一会儿挥动法器,闹腾了好几个时辰,累是不用说的。
可我显然是多虑了,当我沿着朝露和雾岚打湿了的石级山道攀完一百多级石梯,在石阶上拐过弯来,一眼就看到吴远贤老人站在圆拱形的山门前,他已换回平时看管石碉石堡的服装,面带几分赞许,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令我惊奇的是,睡得那么少,他的脸上还没啥倦意。一定是嫁女以后,了却了一桩心愿,兴奋的缘故吧。
关上山门,迎我进屋,在石碉楼上小小的矮方桌旁坐下,一面给我斟茶,一面听我迫不及待地提出问题,他坐定下来,呷了一口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轻声慢语地侃侃而谈起来。
莫看这连绵无尽的山峦,尽是些荒坡野岭,草深林子密,可它们在世间的年月,要比人世间的芸芸众生,多存在千百年了。
你要晓得价值连城的宝玉青蛙的来历,那就要给你讲一段久远的往事,那是大明开国时期的故事。
六百多年前,朱皇帝朱元璋在刘伯温、徐达等文武大臣的辅佐之下,打走了元顺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却不料元朝还有一个梁王盘踞在云南,一个段氏控制着大理,他们认为自家的兵力雄厚,又有关山重重的屏障和阻隔,自恃天高皇城远,你朱元璋奈何我不得,不服他的管,把朱皇帝派去招安的官员要么驱逐出境,要么—个个都杀了。气得朱皇帝龙颜大怒,亲自部署征南。
促使朱皇帝下决心调集军队征南的,除了云南不服他的梁王之外,西南各地的土司部落,也是锣齐鼓不齐,明降暗不降,各行其是,时有骚扰,割地为王的有之,自成体系的也有之。
于是乎朱皇帝派出以大将军傅友德、蓝玉、沐英为首的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一路沿着江西、湖南、贵州杀将过来,直至攻破大理。
“走上山来,山门上有四个大字,你看清了啵?”我正听得津津有味,吴远贤忽然向我提起了问题。
我只得如实相告:“没在意。”
“那是‘威震此山’四个字。”吴远贤一字一顿地说,“这四个字,就是征南大军打下贵州的这一片山野土地,看到这里风光无限,适宜于安营扎寨,而令人刻下的。”
其实这一段历史,留给后人的,岂止是这四个字啊。在云南、贵州的很多地名上,留下的痕迹就更为明显了。诸如“永顺”“镇远”“贵定”“清镇”“普定”“普安”“平坝”“长顺”“广顺”“安顺”“镇宁”“威宁”“宣威”“顺州”……
玉蛙(下)
这些地名充分显示了三十万大军过处,威风八面,经过清剿、招降、一路镇压敢于反抗者,“诸蛮”纷纷望风而降、普遍平定归顺的史实。今天也还存在的丽江古城,之所以古风犹存,就是因为当时年逾八旬、任丽江府宣抚司一职的阿烈阿甲,审时度势,及时地将宣抚司一职传与儿子阿甲阿得。这阿得灵机应变,“率众归顺”,还出力协助明王朝统一了周边的民族地区,朱元璋龙颜大喜,赐“木”姓予阿甲阿得。从那以后,丽江木府的名称也便传开了。
云南被傅友德他们平定,梁王被杀,大理重又纳入大明的版图,那些个土司、宣抚,顺的顺、降的降,局势暂时是安定下来了。可云贵高原毕竟是山也遥远、水也遥远,路途更是十分的遥远啊。胜利了的军队一旦凯旋而归,班师回朝,不知哪个山沟沟里又冒出了一个什么王,或者就是当地的土司,不服明朝管了,怎么办呢?苦思瞑想,朱皇帝命令傅友德的三十万远征军沿着交通要道,以五百六十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所,组成军屯形式,就地驻守下来,封官许爵,稳定云贵。卫所之下,交通要道沿途又设置驿道和铺,铺下面又是哨,铺、哨之间,则常拨弓兵守望。这一来,南京城里的朱皇帝就睡得着觉了。顺便说一声,西南几省,老百姓的村庄,都以寨子相称,为什么偏在交通沿线这一带,村寨会像北方一样叫做屯呢,原因就在于大军过处,很多地名都是随军而来的军师起的。这军师,拿今天的话说,不就是知识分子嘛。记得你这个教书先生教书匠,几次问及为啥子这一带的地名都起得文拖拖的,原因也在于此。
我喝着茶,恍然大悟地连声噢噢地应答,直觉得茅塞顿开,大长见识。
吴远贤拿出摆龙门阵的架势,慢条斯理地接着说。
军队不打仗了,仍然要吃饭。于是就让驻守下来的军队设立军屯,垦荒种粮,解决吃饭问题。
光是吃饭还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