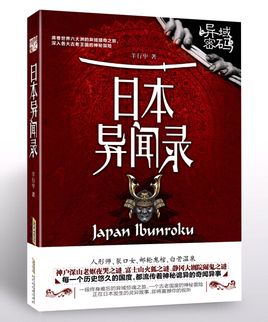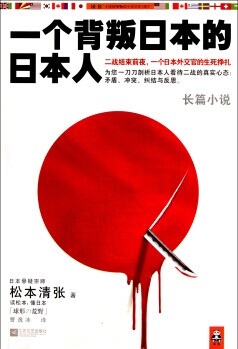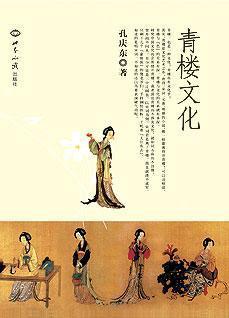�ձ��Ի��Ļ�����-��1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ġ�����ʷ������֧��ʷ�����о��⣬����һЩר��ʷ���о�Ҳ���ֳ���Ϊ���Է�������ʡ��磬���ձ�ֳ��˼��ʷ���о�����ʵ��ͼ��ʮ�ֵ����ԡ�����ǫһ�ġ��ձ�ֳ��˼��ʷ�����������������鷿1937�꣩���ӵ´�ʱ���ġ�ֳ��˼�롱д������ʱ����ֳ��˼�룬ϵͳ�����������ٶ�����ձ���ʷ��������������ֳ��˼�롣���߰ѵ´�ʱ����ֳ��˼���Ϊ�����õĿ�ҵ�ۡ����������Ŀ�ҵ�ۡ��������õġ������Ŀ�ҵ�ۡ��������ͣ�������ʱ�ڵ�ֳ��˼���Ϊ�����������ֳ��˼�롱�����������塤���������ֳ��˼�롱�ȡ����߶��ձ���ʷ�ϵ����Ŷ������ź�ֳ�����ʿ������߶����ۣ���������ʷ�ϵ�ɧ���й��ġ����ܡ�Ϊ��������������������������������ǵġ��۷ɡ����й����������غ���ʾ���͡�������Ȼ��ͼͨ������ʷ��ֳ��˼������飬��һ������Ϊ�ִ��ձ���ֳ�����Գ���˼��ԨԴ���ṩ����֧�֡���������
��������
�������֣��ձ��Ի���˼������ս������ս��ս�����й��˵�������ƫ����1��
�����������ձ��ֻ����й����յĴ��£��ձ�ѧ����ʮ������̸�ۺ��о���ν��֧�ǹ����ԡ��������в��١��о�����¶�ǵر��ֳ��������ֻ����ն����ġ����ǽ�������һ�и���ͳ��Ķ����������й��������ԡ��У�˵�й��˱��ء���̡�������Ұ�������ࡢ̰������ɫ���ݳޡ����衢��α�����̡���̬�����Žᡢ���������⡢�������ԡ�Ъ˹����������äĿ�ֹۡ��Ա����������ҹ���ȵȣ������軭�Լ���Ŀ�г�ª���й��������й����й��������DZ��³��˶������̶������Ԩ�����Ƕ����й����Ѿ�����һ�����Ϸϵ����塱��������������Щ�����ۡ��������й���������պͿ��գ�Ϊ�ձ��ij���ռ���ū��Ѱ�Ҹ��ݺͶԲߡ���������
�����������ڡ������ԡ��������ԡ����о���������ά���Ժ��ձ�ѧ����������ѧ����Ӱ���£������һ��ѧ���о��������ȱ������о��ձ��Ĺ����ԣ�����լѩ��ġ��������ձ��ˡ��͡��ٶ���ձ��ˡ���1891��������ʸһ�ġ�������ʮ�ۡ���1909����Ұ�����ġ��ձ������Ե��о�����1914���ȣ�Ҳ�������о�����Ĺ����Ի������ԡ����ڵ�ʱ�ձ������ֻ��ı����£��о���ν��֧�ǹ����ԡ�����֧�������ԡ�������Ϊһ��ʱ�кͳ�����������һ��������������������֮�����Լ�������������
�������������������ֻ����������������
���������ձ����й����Ļ����Ե�һ������ǣ����й������Ե��о������Ǵ�ѧ���ĺͿ۵��о���������Ȼ��Щƫ���Ͳ�����Ҳ����һЩ�м�ֵ�ļ��⣬�������й���ʷ�о�ר�Ұ���⼪��1908�귢���ġ������庫�˵Ĺ����ԡ������Ҳ���꡶����⼪ȫ������10����һ���У�ͨ����ʷ�ϵĸ����������ܽ����й���������������������Ϊ�й����ǡ������ġ������ǡ�����ĺͽ��ġ����DZ��صĶ����ǽ����ģ��Ǻ�ƽ�Ķ��������Եģ���ʵ�ʵĶ����ǿ���ģ�������ġ�Ω�Ҷ�������ġ���Ȼ����⼪�����ġ�֧�ǹŴ�ʷ���С��ж��й��Ļ������������У�������������Ҳ�Ĵ��ֻ�������ƪ�����й������Ե����»���������ѧ���Եġ����紨���꼪��1901��1981���ڡ�֧�ǵ�����������ᡷ��1937��һ���У����й�����������ʷ���˽�����Ŀ��죬����ʶ���ˡ�֧�������Եĸ����ԡ�������ͼѰ�����ڵĴ𰸣�����һ����ѧ����ֵ���ɱ��㷽�ġ�֧�ǹ������ۡ�Ҳ��Ϊ�Ͻ�����Ȼ���Կ������߶��й����й���û��ʲô�øУ������й��������е����渺�桢�ŵ�ȱ�����ʶ�����ϻ��ǿ۵ġ���������
���������ڶ��������������Щ�о�������ѧ���о��м�������һЩѧ���ԣ����������ձ����������Ӱ�죬������Ծ���Ϊ�ձ��ֻ��������ʶ�����о��о��뷽�跨�ر���й���ʷ�Ļ������о�����������طŴ��й��������еĸ��档�簲�����ġ���С˵����֧�ǹ����ԡ����������۷���1926�������й��ŵ�С˵�硶��ƿ÷������ˮ䰴���������ի־�졷����Ʒ��������д�У������ֺ����й������ԣ��Ȼδ�����ɣ�Ҳ������ѧ����һ��;����������ȴר���й�С˵�з�����Щ�ܹ�˵���й��˸��桢ȱ��������ªһ������ӡ�����ֻҪ��һ�������Ŀ¼������ˡ����鹲��ʮƪ������һƪ�ǡ���˵���⣬���¸�ƪ��������Ϊ����������
���������ڶ�ƪ�����������������ݣ���������
������������ƪ���������ˣ���������ɥ�������������
������������ƪ�������ԣ��������ͣ���������
������������ƪ��ȱ��ͬ���ģ����ڲ����ԣ���������
������������ƪ���������塢�´����壻��������
������������ƪ�����ȵĽڼ�Ͳ������Ľ�Ǯ������������
���������ڰ�ƪ�������������������ģ���������
���������ھ�ƪ�����ź��أ���������
����������ʮƪ���������֣������ʢ����������
���������⿴���⣬����ȫ���Կ�������������еġ�֧�ǹ����ԡ�ʵ���ǹ�Ǻ��������ֻ�е�������ǿ������ȱ�㣬��������Ұ��������������α��ɫ���й��������ı�����Ȼ�dz�ª�ġ�
�������֣��ձ��Ի���˼������ս������ս��ս�����й��˵�������ƫ����2��
�����������е����������о��й����е�Ұ��ϰ�ף��������й�������й���ʷ�о�ר��ɣԭ���д�ˡ�֧���˷������ʷ����1913������֧���˵ij������ϰ����1919������֧���˵������뱣�ء���1917������֧���˵���Э�ԺͲ¼��ġ���1921������֧�ǵĻ¹١���1924���������Ҳ���꡶ɣԭ���ȫ������1������һϵ�����¡������ڡ�֧���˵ij������ϰ��һ���У��о����������е��й����ϣ�˵���й��ˡ����Ϲ�ʱ�����г�����ķ�ϰ�������һ���������ϡ��żȻ���¼�������������ʷ�У��洦���м��ء����������ձ���Ϊ�˺ܺõ����֧���ˣ�һ��Ҫ�ӱ���������й۲족�����ܹ⿴�����ǵ�ʫ���б��ֳ����ŵ㣬��Ҫ�����෴��һ�棬���ơ���������
��������������ª���й��˵��軭��������
�������������֣����dz������Ϊ�ձ��ֻ���Ŀ��Ѱ�����۸��ݵġ�֧�ǹ����ԡ�����֧�������ԡ��ġ��о�����20����30��40������ձ������˲��������Ķ����������ص�����ĸ��˵��ı��飬��ԭ�������ġ�֧�������ԵĽ��ʡ������ٻ�֮���ġ�֧�ǵ������ԡ���ɽ����εġ������֧�ǡ���֧�������ԵĿ�ѧ�Ľ����������Т̫�ɵġ�֧�ǹ������뾭�þ�����������
��������ԭ�������ġ�֧�������ԵĽ��ʡ�������1932�꣬����α�����ոճ���ʱ����ġ������������гƣ�����������������ǧ�����ڵ�һ�֣����Ǿ�����Щʲô���������˽�Ҫ��ͷ��������һ�������˵���������ž�����һ������������顣��˵��д�����Ŀ�ģ����ǡ��ܹ�Ϊ���Ķ�֧��������ṩһ��ο�����ʵ���ϴ�������������ѧ���о����ã�����Ϊ�ֻ������Ӧʱ֮������֧�������ԵĽ��ʡ�ȫ������˶��й��˵����֮�飬������ָ���ձ�����ν��֧�����ձ���ͬ��ͬ�֡��ۣ��ǡ�����Ķ�֧����������������ձ�����֧���˼Ȳ�ͬ�ģ�Ҳ��ͬ�֣����Ҳ��û�С����ơ��Ļ����������о�֧���˵������Զ���֮��ʲô���ƣ�����������������������һ���������ֿ�ԡ������ţ�������ȫ���������������ġ�֧�������ԡ���ֻҪ�������½ڵı��⣬��֪����Ҫ˵ʲô�ˡ��硰�����ۡ�����û���ӡ����������ԡ������������塱��������������������ƽ���塱�����ǿ�ѧ�ԡ�����������ʶ��ȱ����������Ű�ԡ����������ԡ�������̬�������������ҹ����ȱ����������ʽ���塱���������ԡ��������ӡ����������ԡ��ȵȡ����磬˵���й��˵������Ը��ǡ��������塱����Ϊ�й���һ�������⣬��ϲ��˵��û���ӡ���������������д������������
����������ǿ���ѹ��֮�£��;��á�û���ӡ�������˳�������������������Ͳ����������塣����ֱ�����죬��վ�������˶���ǰ�ߵļ��ϡ����ޡ��Ϻ����ڳ�Ϊ�ձ����ӵ�ռ���������ǼҼһ����������ձ��죬����ӭ�ձ������ˡ��������ڹ����빲����������ʱ���������α�����ռ�죬����������ÿ�ζ��������������ͺ��졣��Щ��ʵ������¶�����ǵķ������塣��������
���������������������ڶ����������������˶�����Ҫ�����ձ����ϡ������������ȻΣ���ش����ǵ������˶�����ȻԴ�����ǹ��е�����������Խ�У�����Ϊʲôһֱ��ôִ�ֵض��ձ��������ж���ֹ֪ͣ�أ�����ĸ���ԭ��ֻ�����ǵķ����Բ��ܽ��͡�������ΪӢ��������������Լ�ǿ���ձ�����Լ���С����������
�������������ԭ�����������й��˵ġ����ա��������ձ��ֻ��ı�Ȼ�����ȴ˵�й������������ڡ������������¡��˴���Ȼ�������������������ձ������й������й��ˡ����ա���ԭ��ԭ�������й��������ձ��������������취ֻ���ձ����й��Եø�ǿ�������й����ܡ�������������Ȼֹͣ���Ҽһ����������ձ�������ӭ�ձ����ˡ���������
��������ԭ������̸���й��˵ġ���ƽ���塱����Ϊ��֧�������ڱ������ǰ��ú�ƽ�ģ����ǵ���Ȼ������ֻҪ�б��ϣ��Ͳ������˭��ͳ�Ρ������ֿ�������Ϊ�й���û�С����ҹ����һ�µġ�Ȼ������ȴ����һ���д�̸�й��˵ġ���Ű�ԡ������ٳ��������У��й��˴�СԸ�⿴��ɱ������ɱ�˵ij��棬�̳�������Χ���˹��ڣ����ơ�����һ�����ӣ�����Ҫ˵���ձ��ֻ�ʿ�����й���ɱ�������й��˵����֡���Ű�ԡ�������������
���������������ձ����˱�֧�Ǿ���ɱ���ˡ������Щʬ�壬�����౻�����۾������˱��ӣ����˶���ġ�Ҳ��Щ�˵Ķ��ӱ��ʿ�����Щ������ȥ��Ҳ��Щ�˱������˽ţ����������ϡ���������
������������
�������֣��ձ��Ի���˼������ս������ս��ս�����й��˵�������ƫ����3��
���������������˶��У��С���ʳ��ū�⣬������ūѪ���ı���ⲻ�ܽ�����Ϊ��һ��ɿ�����������������ԭ����ȷ�����Ų�Ű�ԡ���������
�����������߲���Ҫ�ʣ��й��˼ȡ����ú�ƽ����Ϊʲô��Ҫɱ�ˣ�Ϊʲô���ձ�����ʵʩ��ν����Ű����ԭ�����������ձ��ֻ���һ���ʽǶȿ����⣬ȴ������Ŀ�е���ν��֧�������ԡ�ǿ�����͡���˵�й��ˡ����ú�ƽ������Ϊ��Ҫ˵�й���ų������ϲ�����̣�û�й��ҹ��˭��ͳ�ζ�����ν���ձ�����ͳ�ε�ȻҲ����ν����˵�й��ˡ���Ű������Ϊ��˵���ձ��������й���ɱ���dz����й��ˡ��Բ�Ű��������һ�ֿ�еġ��ġ������ԡ���ȴ�����ձ�����������й���ɱ���ӣ�����������й��˵ı�Ȼ�����������ġ�֧�������ԡ��ġ����ʡ���ʵ�����Ѿ��롰֧�������ԡ��ġ����ʡ�û�ж���ϵ�ˣ����ó��������ʡ��ģ����������Ǿ����ձ���ǿ���������ˡ���������
�����������ٻ�֮�������ġ�֧�ǵ������ԡ����������������Ļ��о���1937������������ȷ˵����֮�����о���֧�������ԡ���Ŀ�ľ����ڷ����ձ��ֻ�����ʵ����д���������ʾ������ҵػ�Ծ��½�����У��������֧�Ǹ����߳ͣ��˴��±��ԭ�������Ͼ�����Ϊ��Ӫһ��֮˽����������ֶ�Ͷ��֧�ǵ������ԣ�ʹʮ�����������������ա����ա����ս�������֧�ǵĹ����Ծ����������ģ���������֪��֪����ս�����DZ����ؾ�һ��������֮�以���˽⣬�ǻ��ྴ������Ҫ�С���������������������˼��֧�ǵĹ����ԣ�������ͽ����������顣�����������ƣ����š��Լ��Խ���Ȩ�IJ����ǵ�����Ϊ�����еĵ����ģ������ڱ���֮�¡����ֿ��³�����߶�����֧�������ԡ����ڱ�⣬��Ŭ��ƽ�ľ����������ģ���Ǩŭ��������֧����������ȷ�ش���������������ͳ��ȫ�飬���ѿ������ٻ�֮����������IJ����ǡ��˵��������İ�Ϸ����Ϊ�Լ��ġ�֧�������ԡ������Ͽ۵����°��ˡ�ȫ���������ġ�֧�������ԡ�������������������������������������ȱ�����ҹ���������ı��䡱�����˷��ԡ��ȣ������˶��й��˵�ƫ������������
�����������磬���ڡ�ȱ�����ҹ���������ձ��о��й������������ͨ�п��������ٻ�֮����Ϊ��֧�����������ġ�����˵���й���ͳ�ν����²����ڵĹ�ϵ�ܵ�������Ϊ������֯�ij�͢��ʵ���Ǿ�����Ⱥ���ٹٽ�Ϊһ�壬�����빲�������ǵġ����ҡ�ȴ���²������û�й�ϵ�����ͺñȺ�ˮ�����볼�DZ���IJ�������Ȼ������������ײ�ȴ��ʲô����Ҳû�С�����ǡ��������֧�ǵ���ʷ��Ҳ������֧���˵�˼�롣�˵���ʹ�ʵ��������֮�������Ҫ�����ע�⡣���������й����ձ����˽�һ���Աȣ�˵�����ʹ��ij�����û�в��һ���������dz�Ҳ�������ڳ�͢�����dz�����Ұ�����������IJ�����û�С�������������dz�����������ǵĹ��塣��֧��ȴ��ͬ�����������Ž�Ȼ�������ҹ���һ�����������Ƕ���һ����������ǹ̶�����ģ����������ǵľ���˭����û�й�ϵ������ֻ��Ҫ���ȵ���������ٵ���Щ���ۣ���Ȼ��Ƥ��֮���������ձ���ʡ�����һϵ������һ�����Ĺ̶����俴���ǡ����ҹ�������֣�����֪�й�������Ϊ�˸ij����������������������һ�֡����ҹ����ʵ���ϣ��ձ������ձ��˵ġ����ҹ�����й������й��˵ġ����ҹ�����ڸ���ġ�����������һ���У�������˵���������ڻƺ�����������ʱ�����ܵ����������Ļ���ԶԶ�����������Ǻ���������˷dz�����Խ�У��Գ��л����й������ģ����ķ��������Ϊ���ġ����֡����������ң���Ϊ�ĵ����ޡ���ν���С�����ָ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