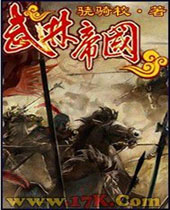温莎的树林-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另一个肩膀
那一年,和陈朗哥哥一起去参加一次比赛,我们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之前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还是把演出服穿在身上,免得放在箱子里压皱了。
我穿着一件陈朗的爸爸帮忙借来的雪纺纱裙子,白色的裙子,水钻扣子,样式简单,裙边上一边一个飞着淡紫色丝线刺绣的蝴蝶,裙子上有一股淡淡的茉莉花的清香。
那是条很漂亮的裙子,可是试装的时候,我表现得格外别扭,一会儿嫌尺寸大了,一会儿说图案不好看。陈朗的爸爸脾气很好,笑眯眯地一个劲地说“穿惯了就好”,“穿惯了就好”,每次去参赛之前,他对我们都百依百顺。
爸爸责怪我太挑剔,然而,我自己心里知道,那么不合情理地挑三拣四,也许只是为了说服自己,那条裙子不属于我,永远也不会属于我,比赛结束,我把它脱下来还掉,也许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到它。
其实,我只是为了说服自己不要去爱上它。
于是我穿着漂亮的雪纺纱裙子,陈朗哥哥穿着挺括的礼服,领口上亮亮地镶着一层边,金色枫叶形状的袖扣,看上去人仿佛陡然大了几岁。坐的是慢车,陈朗的爸爸一上车就捧着茶杯睡着了,剩下我们两个人并肩坐着看窗外飞逝而过的风景,为了保持衣服的平整,齐齐整整地僵坐着。
旁边站着的一队民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的装束,被看久了,我的脸不由热起来,他们的表情让我想笑,可是陈朗哥哥一直很严肃。
那天,他告诉我,打算将来去考奥地利的那所音乐学院。他有个远方姑母就是那个学校毕业,愿意帮忙资助他。
陈朗哥哥的手轻轻地覆盖在我的手上,他的手冷得像一块冰。他说,“雨霏,将来哪天如果我走了,答应我你会好好照顾你自己。”他的表情十分郑重。
我记得那天我既没有答应他,也没有拒绝他,只是默默地低着头。
终于我们两个人都困了,他问我要不要靠在他身上睡一会。于是我靠在他的礼服上,隔着厚厚的垫肩,隐约感受到他肩膀的起伏和头发上洗发水的清香。火车就那么自顾自地往前,一站又一站地停留和启发,站台上素不相识的脸没来由地对着我们微笑挥手。我闭上眼睛,不再去想任何事情,那是一个非常别扭的姿势,我勉勉强强睡着,醒过来的时候,脖子扭得酸疼,而他依然一动不动地端坐着。
那一次他得了一等奖,我得了三等奖。一下台,我就脱下了白裙子。我们当天赶回家,我在火车上靠着窗台睡了一路。
我靠在林国栋的肩膀上,跟他讲起那条久远的,白色雪纺纱裙子。其实我已经几乎忘记那条裙子了,但是这一刻,它却无限真切地浮现在眼前,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抓到,茉莉清香扑面而来。
他的右手扶着我的胳膊,等我讲完的时候,轻轻地伸过来,扣住了我的右手。
他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冷。”
他的手是宽大的,温暖的,手心稍稍有些潮湿,我能感到上面的纹路。他的肩膀形成一个很舒服的弧度,我的脸颊靠在上面,依然是半梦半醒的感觉。
二十年后的他
“你是不是很容易累?” 林国栋问我。
我点点头,把头偏开一点,看着远处的天空。虽然早上彻底地刷过牙,我依然很害怕他会闻到我嘴里偶尔会传漏出来属于病人的味道。
他的手依然紧紧扣着我的手贴在自己胸前,隔着温热的手掌心,是他的脉搏。我的眼睛慢慢地开始有些发酸,我想,那大概是望着太阳太久的缘故。
林国栋转过头来看着我,他的脸上有一种很难过的表情。过了很久,他轻轻地说,“你放心,一定会好的。”他的声音含着自我欺骗式的倔强。
“对不起,太阳出来的时候,我睡着了。”
他说,“我们可以再来。”
我对他微微一笑,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我的手心依然带着他的体温。
回去的路上,我悄悄地把头贴向他的后背,没有碰着,却依然能听见他呼吸的间歇胸腔深处传来的声音。
我说,“你常常来找我,你家的人会说你的。”
“不会。”他说。
我在心里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
他把我送回大楼门洞前,人坐在自行车上,一条腿垂下来踩在地上,伸出手去抓抓头发,嘴角上翘着,他穿着米色衬衫,蓝色牛仔裤,神态和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大街上和人打招呼的时候一样。
我看着他那个单纯得几乎没有烟火气的神情,心里突然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铲了一下,痛了起来。那种痛楚一丝丝地弥漫开来,透过经络从心里缓缓蔓延到全身。那个神情,会让我忘记痛苦,对生活产生非分之想。过二十年,也许他会变成现在林医生的样子,温和,沉稳,有宽厚的肩膀和淡定的态度,善待旁人,爱护妻儿,是一个公认的好男人,可是,过二十年,我又会在哪里呢?我不敢再想下去。
最后,我几乎是用很不友好的态度对他说,“以后,你还是不要来找我了吧。”
他的神情僵住了,嘴唇微微张开,过了一会,问,“为什么?”
我低下头看着地上,林国栋踩在踏板上的那条腿垂了下来。
“我不喜欢别人多来打扰。”我对着水泥地说。
沉默了一会,他开口了,声音很低,“你觉得我打扰你了吗?”
我点点头,抬起眼睛来,正对着他的额头,他的眉心处蹙着一道细细的纹。
他移开眼光,抿紧嘴唇,我咽下一口口水。
“那……陈朗,他不是常常给你写信?”过了很久,他问。他的声音里有些干涩。
“我们从小就认识。”我说,声音里有种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强硬。我转过头,对着涂得乌七八糟的楼道墙壁,不再看他。
林国栋没有再说什么,他的自行车默默地消失在墙角那一头。
缘分就这么浅
进门的时候,小阿姨正在和人讲电话,看见我,手里的无绳电话机居然“啪”一声掉到了地板上。
她弯腰捡起电话机,脸上满布着惊讶。
“我先挂了,以后再说吧,”她低声对着话筒说,转过身来,“你到哪儿去了?我还以为你在睡觉。”
“我睡不着。”我对她说,走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茶几上散放着昨天的报纸,空气里荡漾着一股淡淡的烟味,烟灰缸里躺着一个烟头。
同很多有艺术气质的人一样,小阿姨有时喜欢抽烟,可是,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清早就抽烟。
她的眼圈微微有些发青,头上包裹着厚厚一块毛巾,她走过来,坐在我身边,用修长的手指捻着毛巾里蹿出来湿漉漉的头发,长长的发丝卷在她白皙的手指间,像一条条细细的小蛇。
捻了一会头发,她拿起指甲钳开始剪脚趾甲,圆润的脚趾上冰蓝的指甲油落掉了一块,她仔细地研究一番,轻轻地嘀咕了一句,神态有种不经意的美艳。
“蔡雨霏。”她剪完脚趾甲,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我也默默地看着她。
“蔡雨霏,”她低下头去,“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和你的肾脏匹配不够好,不适合做移植手术。”
又是长长的静默。大楼下面的城市就在我们的静默里活动起来,像一只蛰伏的动物缓缓苏醒过来,爬出洞穴,开始左顾右盼。楼下对面糕饼店一个女人绵延不绝地抱怨一个不识趣的顾客,骂上对方八代祖宗,而很远的地方不知哪里传来悠悠的几声鸡鸣,给人种“大漠孤烟直”样的错觉,仿佛千里之内只是碧水黄沙。
我错过了日出的太阳在窗帘里透进光来,暖暖地落在脚上,果冻依然伏在墙角里它的小角落中趴着睡觉,一个小爪子向前探出来。
小阿姨抬起头时,她的眼睛里闪亮地盈着眼泪。
“有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你们什么……”她的嘴唇艰难地左右移动,最后,紧紧地抿成一条鲜红的线,和高高的鼻梁形成一个倒立的T字,神情里有种决绝的态度。
“活着的时候不要我,人死了,女儿却要我照顾……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她俯下身,揭开毛巾,把手指用力□乌黑的头发里,一股清香带着潮气飘逸出来。她的肩膀微微起伏,传来断续的呼吸声,声音里带着点恨意,“连我的肾都不能用,缘分就是这么浅……有什么办法……”
我把手轻轻地搭在她的手背,她的手指冰凉地覆盖在湿漉漉的头发上。那一刻,我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我一直想着不要小阿姨捐肾给我,但是直到此刻才明白,内心深处依然是悄悄有着希冀的,自私的渴望,无声破灭的时候,剩下的,是满满的绝望。
我躺回床上去,屋子里静悄悄的,小阿姨上班去了。现在她在林国栋姐姐的那家广告公司工作,每天忙个不停。
天花板上有一只小蜘蛛,兢兢业业地在角落里结网,一个上午,我看着它慢慢地从这头到那头,再从那头到这头,丝丝缕缕,居然结成了一层薄薄的网,心里有些高兴,又有些难过。
我的眼前浮起林国栋转身离开时的背影,然后,我把眼睛闭上。
她拉着他的手
夏天已经来了,梅雨季节湿热而甜润的气息悄悄地从土地里升起来,像石头缝里的青草。几乎天天都下雨,天地间一切都是潮的,粘的,空气里千丝万缕说不出的牵绊和纠葛,仿佛特别有人间味。
不下雨的那天,小阿姨带我去宜家买了几件家具,让人运回来,小敏姐姐站在她家门口看着经过走道的那堆硬纸盒,脸上稍微生动一点,淡淡地说,“宜家的东西好看,就是用不了几年,不过无所谓,反正你们也不是长住,下次搬走的话,索性就扔掉好了。”
小阿姨笑笑,“下次我们搬家,就送给你。”
没想到她说,“算了吧,我们家的家具都是整片水曲柳,结婚时打的,五十年用不坏,哪像这种三夹板做的,用用就烂了。”她的声音里有点轻蔑。
流掉孩子之后,她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说话口无遮拦,让人听着不是味道。平时经常呆呆地搬个板凳坐在门前看着走道,脚边放一个脸盆,旁边一堆蚕豆,她一边剥豆一边自言自语,有一次我看见脸盘里堆着豆荚,而豆子扔得满地都是。
小敏姐姐的评论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心情。我和小阿姨一同把半人高的书柜拼起来,靠墙放着,她把一套新买来的张爱玲放在书架上,我随便拿来翻翻,里面十几页被她撕掉了,看目录,是“花凋”。我从前看过“花凋”,不由觉得小阿姨这么做有些可笑;我还没有脆弱到那个程度。
常去的病友网站上有个女孩子和男朋友分手了,她说“现在才知道,其实我们没有资格谈什么爱情。”
我默默给她发去一大束玫瑰花的图案。
几天里,我没有看见过林国栋。确切地说,我没有往窗外看,每回拉开窗帘之后,都立刻移开眼光,然后逃一般地回到房间里阴暗的那一半。
有一天黄昏,我听见有人叫“果冻”,“果冻”,有个男声回复了一句,听不清他在说什么,那低沉的嗓音却钻过玻璃直钻进我的耳朵,是他的声音。他们继续说话,像是在谈论什么。
我终于忍不住,靠在窗帘旁边,朝对面二楼看过去。
对面二楼,隔着窗户上的铁条,房间中央,站着一个女孩,一头长发波浪般微卷着披在肩上,她穿着一件白色露肩的裙子,下摆宽松地撑开,裙子上缀着大朵向日葵,她的侧脸对着我,挺秀的鼻梁和红润的嘴唇,光艳照人。而林国栋正拿着一块布,低着头为她擦裙子上的什么东西,隐隐约约听见她正在催他“你快点嘛,就要开始了”,声音里充溢着青春。他抬起头,对她说了一句什么,就在他的眼光转向这边来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猛然一拉窗帘,把自己严严实实地盖住。房间里很静,我的心裹在窗帘中间咚咚地跳。
过了很久,拉开窗帘,那边已经空无一人,连窗子都关上了,垂下米白色的窗帘。
我默默地坐回沙发上,想起来,那个女孩,几个月前曾经在楼下见过。那天,她穿着精致的米黄色套装,修长的双腿,站在出租车边拉着一个背对着我男孩子的手。
原来,那天背对着我的,是林国栋。她拉着他的手。
命里有贵人
窗台上依然站着林国栋送给我的那个卡通小人,胖嘟嘟长着个啤酒肚,一张老少咸宜的笑脸,戴顶礼帽,开足发条,他就扭着腰跳起舞来,跳完后突然脱下裤子露出屁股。每一次它都让我发笑,即使现在也不例外。
我仿佛依然能听见那个女孩子银铃一样的声音和那声音里隐隐的笑意。她的发卷披散在肩膀上,随着身体微微摇摆前后动荡。
我拿出电子琴,把手指放在上面,慢慢地,它们像是自己拿定了主意,在键盘上游动起来。苍白的指尖飘出一段音符,仔细听,那是一支李斯特。
我的指尖触着冰凉的键盘,轻轻地闭上眼睛。
对于李斯特的曲子,陈朗哥哥有一套莫名其妙的讲究,心情激动的时候不能弹,太高兴的时候不能弹,(奇)悲伤的时候不能弹,(书)压抑的时候不能弹,(网)痛苦的时候不能弹,紧张的时候不能弹,照那套规定,几乎没有什么时候能弹。而事实上,他有非凡的定力,无论心情如何,都能在短时间内调整到无风无晴,他坐在钢琴前,在惨白的锥光里闭上眼睛一会儿,再睁开的时候,整个世界里,只剩下五线谱,没有别的,指尖流淌出的乐调干净得不沾人间烟火。
他如果听见我这么泄愤式地弹李斯特,一定会生气得叫起来。可是,又有什么要紧。
带果冻下楼去散步,它在一棵树边办完事后,咕噜噜摇摇脑袋,无忧无虑浑身轻松的样子。
小敏姐姐坐在楼门前的一张小板凳上摇着把扇子,一面神情专注地看着她自己的手。她看见我们,对着果冻笑起来,努起嘴做出“呜呜”的声音来招呼它,果冻也很配合,用力舔她的手。现在,只有看见果冻的时候,她才像是真心真意快乐的,仿佛这个满身绒毛的小东西使她暂时忘记了人世的严刻。
逗完果冻后,她突然说,“把你的手给我。”
小敏姐姐拿过我的手,摊开掌心,看了看,点点头。
我问她什么意思,她淡淡地笑笑,“你的生命线不短。”
我看着她。
“当中一段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