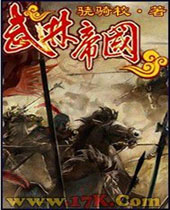温莎的树林-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信封,上面写着英文,还贴着几张图样鲜艳的国外邮票,但是看不清到底写的是什么。
“干什么呢,小林?”小赵叔叔的大巴掌突然掉到了我的肩膀上。
“没,没,没……什么,”我猛地一惊,结巴起来,看着小赵叔叔,情急间憋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我,我在网上订了一本参考书,老也不到,我怀疑是不是寄到后面的楼来了……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事……”说着说着,我的脸不听使唤地热了起来。
“哦?”小赵叔叔居然相信了,一本正经地帮我找,还是我先说“不要紧,我该上学去了。”
我骑上车,在清晨的风里融入人流,这才放松一点,突然感到自己刚才的行径有些不可思议。
化学系大楼位置极佳,从顶楼实验室放眼望去,上有蓝天白云,中可观校园全景,往下看,正对着女生浴室,而我们的实验课,刚好挑在女生浴室开放的日子。
最后一堂实验课,几乎所有女生都早早做完实验去洗澡,剩下男生围在窗前,在刺鼻的硫酸味里盯着楼下,想象着一群女孩子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一件件脱光衣服…………隔着层屋顶,口水都快掉下来,偶尔会有人小声提醒“那个,那个刚出来的,是不是很像徐怀钰”,于是大家齐刷刷凑上去,嘴上说“像什么呀”,眼睛里却恨不得伸出手来。
忽然,楼下脂粉堆里,一个女孩扬起红扑扑的脸,晴天霹雳般对着我们高声叫了起来,“庄慕瑜,看什么看,你这个伪君子!”她湿漉漉的头发披在肩上,脸上慷慨激昂。
那一叫,楼下的女生眼光齐刷刷看过来,加上男生的目光,一同聚焦在木鱼的身上。
桃花劫
那一声嘹亮的“庄慕瑜,你这个伪君子!”让木鱼的脸像酚酞试纸遇见水分子,红了个彻彻底底。在十几张艳丽脸蛋的逼视下,男生们迟疑片刻,野狼般“嗷”地一声叫了起来,一个同学唯恐天下不乱,嬉皮笑脸地推了木鱼一把,“哥们,你对人家干什么了,人家骂你伪君子,啊?”
“我没,没,没,没……”木鱼红着脸,像是被什么卡住了喉咙,那个同学更来劲了,“别狡辩了,就承认吧!”
木鱼的脸色由红变青,猛然转过身,用力一把推开那个同学,对方“哎唷”一声跌跌撞撞倒在旁边的椅子上,木鱼却只管蹬蹬蹬几大步,拎着书包就出了实验室门。
男生们又是一阵起哄。
我朝校门外的护城河边骑车过去,木鱼果然在那里。他坐在树下,嘴里叼着一根青草,靠着斑驳的树皮,凝视着污浊的河水和对岸被火烧云蚕食的天空。
“我对她真的没有过什么特别的表示。”木鱼有些无奈地说。那个女孩是化三班的,由于性格活跃而家里有钱,在系里有点小名气,据说她每次回家坐的都是父亲公司里的奔驰车。她和木鱼是在一堂“思想道德修养”课上认识的,当时木鱼上课迟到,慌慌张张坐在她旁边,还刚好被老师提问,结结巴巴当众大出洋相。
“她整整一堂课都在看,看蔡骏,等到下,下课,突然问我借笔记抄。”把笔记本还给木鱼的时候,她审问一般地打量着他,“你有女朋友吗?”
“我说,没,没有,”木鱼脸上的表情无辜得可以,“然后她就……”然后那个女孩就开始追他。女追男,隔层纱,木鱼在纱的这一面很为难,躲藏唯恐不及,几次下来,那个女孩很生气,觉得木鱼欺骗了她的感情。
我笑起来,“你告诉她已经有女朋友不就好了吗?”
“那时候怎么想,想,想得到。”木鱼吐出嘴里的草杆子。
那个女孩子相当骄矜,她告诉木鱼,“找我做女朋友,至少不必担心我看中你家的钱。”看来,她是觉得自己和木鱼门当户对。
“可是……我想,如果真,真,真的喜欢一个人,为什么要在意她看中我家的钱呢?她可以既看中我家的钱,也看中我,不矛,矛,矛盾的啊,就算她先喜欢我的钱,然后喜,喜欢我……”木鱼的表情显得有些困惑。“怎么办呢?”他问我。
“这个……顺其自然吧。”我暗暗庆幸我家没多少钱,起码没有这种桃花劫。
露露表姐的婚礼如期举行,场面热闹,气势华贵,衣香鬓影,都跟预想的一样。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接近尾声时,角落里突然冒出一个醉醺醺的男人,一拳头挥舞过来,没有打中新郎,砸在了我的脸上,几周前被木鱼临门一脚才好不久的鼻子再度受创,黏糊糊的血顺着下巴往下流。
“今天我一看见他的表情就觉得不大对,”出租车停在我家楼下,露露一面付车钱一面说,“不过,和新郎一比,实在是帅多了。”
“你表姐为什么要请他来?”我又扯了一块纸巾塞进鼻子,含糊不清地问。
“她希望得到所有人的祝福。”露露打开车门。
“如果人家不想祝福她呢?”
“那就太小器了,”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表姐不嫁给他,是对的。”她化着妆,头发挽起高高地拢在脑后,身上洋溢着芬芳的脂粉气,艳光四射地站在车边把手递给我,“快出来啊。”
女人的逻辑碰到现实,就是祸殃池鱼,倒霉的伴郎被一拳头揍得鼻子血流不止。露露以前没告诉过我,那男人非但长得像甄子丹,还是业余拳击选手。
这一天晚上,我发现,对门二楼的窗帘拉开了,我甚至可以看见里面靠墙的一架木头沙发,上面是天蓝色的沙发套。
我的鼻子突然不痛了。
陈朗哥哥的信
小敏姐姐一打开门,果冻就“呜呜”地叫着扑上来,两只爪子竖起奋力抓着我的裤脚,声音里像是受了很多委屈,神情却充满热情,圆溜溜的鼻子使劲地蹭啊蹭。最近它长胖了一些,毛也光滑了,变成一只很登样的小狗。
“它睡觉的样子最可爱了。”小敏姐姐微笑着说,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两只手有些费力地撑在腰间。这些天她帮忙照顾它,居然还真的去买了一包喜之郎来,“咱们果冻啊,可喜欢吃果冻了。”她轻轻地抚摸着它的毛。小敏姐姐是广东人,却说一口标准的北方普通话,因为她嫁了一个北方男人,恋爱七年,她完全被他同化了。
小敏姐姐听说我们要出门,立刻答应替我照顾果冻,还说,“不要紧,只要让它待在另一个房间里,不要让它随便爬到床上就可以。”她很喜欢狗,以前养过一只博美犬,从很小一直养到它死,整整十五年。“十五年的狗,相当于百岁老人了,”她垂着眼帘,“它死的时候,我好难过好难过。养狗就是这样,你知道总有一天它会在你眼前死掉,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句话让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突然想,世上的狗也许都习惯在人的眼前死掉,那么,假如有一天,人在狗的眼前死去,它会不会感到很意外。如果是我的果冻,知道从此没有人照顾它了,它会不会很难受。那时候,它会是多大呢?
小敏姐姐问我,“怎么样?”
我说,“医生开了很多药。”她点点头,脸上很慈悲的表情。
前几天才知道小敏姐姐的丈夫去年出了车祸。她告诉我的时候,脸上很平静,“从前我总是担心家里的狗跑出去被车撞死,没想到……”然后看看我,“不过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我有孩子了,还说一定是个儿子,”她脸上带着点淡淡的微笑,“他猜对了。”
“对了,对面楼里的小林,小名也叫果冻。”小敏姐姐说。
“是吗?”我抱起果冻,说,“跟姐姐再见。”它居然真的举起一个小爪子,欢天喜地像在说bye…bye,我说“我们回家”,它“呜”地一声,像在说“好”。
陈朗哥哥从维也纳写信来了,开首第一句话“希望这封信不要被退回”,我不由微笑起来,仿佛看见他眉心皱起,中间形成三道细痕。我们经常搬家,有时换了地址才通知他,信就被退回去。
陈朗哥哥是现在少见的,喜欢写信的人,他在信里说维也纳的天气,说那里古老的欧洲建筑,说他们住的宿舍原来是二战时的美军俱乐部,里面华丽考究,还有人天天换床单。这封信特别厚,夹了几张照片,他在照片上很神气地微笑。
在信的结尾,他问,“你的病怎么样了?”每次给他回信,我总是说,我好多了。
我去楼下对街的书报亭给小阿姨买最新一期的“瑞丽家居”,那是她每月必修的,过马路时想起小敏姐姐的老公,不由格外放慢了脚步。等买到杂志,转过身,对面楼口的路上停着一辆出租车,车边站着一对引人注目的男女,男孩子穿着笔挺的西装,宽宽的肩膀,背对着我,旁边的女孩子穿米黄色的套装,三月初就光着腿只穿丝袜,看上去充满了活力,正拉着男孩的手说什么,神采飞扬,两道精心描画的眉毛长长地延展开去,我听见她高声说“我表姐不嫁给他,是对的”,像是在和谁赌气,然后他们消失在大楼背后。
清澈的眼睛
屋子里弥漫着蒸氲的中药气,小阿姨伸伸鼻子,“很香啊。”
“那你喝一口。”我愁眉苦脸地看着她。果冻跳到桌子上,伸出小鼻子凑到药碗边上好奇地闻闻,像是被药味呛了,“呜”地一声,也立刻近而远之了。我摸摸它,“是不是很难闻?”
它长长地“呜”一声,别开头去,仿佛说“难闻死了”。有时候,我真的怀疑果冻能听懂我的话,它那个小脑袋比我们想象的先进得多。
“中药就是要越苦效果越好,”她告诫我,“快点喝,否则就冷了。”
我坐在桌前,捏住鼻子,端起碗往嘴里灌了一口药,胃里仿佛生出一只手,立刻把流进去的液体用力地往外推。我捂着嘴朝洗手间冲过去,浓浓的药冲口而出涌进马桶,一股刺鼻的气味。我站在旁边,眼泪汪汪地干吐。
“真的好难喝。”我喘过气来,对小阿姨说。她轻轻地拍我的背。
“要不,以后煎药的时候,加糖……不,你不能吃糖……”她转过身,走出卫生间,对着门边墙上一张纸看了一会,“你可以吃蜂蜜,那就加蜂蜜。”
我无奈地对她笑了笑,“这么苦的药,要加多少蜂蜜啊,”然后我问她,“小阿姨,你也去医院检查一下肾脏吧。”
“为什么?”
“听说这种病有家族遗传,”我低下头,“我妈不就是得尿毒症死的。”
“胡说八道,”小阿姨满不在意地拢了拢头发,“就算有,我和你妈一点都不像,基因肯定不一样,”她对我挤挤眼睛,“小时候你外公外婆骂我,就说我是垃圾桶里拣来的,不是他们的女儿。”
“那我妈呢?”
“你妈……你妈很乖。父母要她穿什么,她就穿什么,要她不和谁玩,她就不和谁玩,”小阿姨轻轻地叹了口气,“你妈真的很乖。”
我折腾了几乎一个多小时才把药勉强喝完,小阿姨把装着药渣的罐子递给我,“雨霏,你把它从阳台上扔下去,扔到路当中。”
“干什么?”
“给人家踩啊,药渣摆在路当中,踩的人越多,就能把你的病踩掉。”她认真地说。小阿姨这个人挺奇怪,有时候百无禁忌,有时候十分迷信,而她的迷信里,也多少带着一点游戏人生的色彩………我担保她不是真的相信别人的脚能帮我把病踩掉,只是懒得把药渣倒进垃圾袋而已。但我喜欢她那种口气。
“就这么倒下去,人家不会说吗?”
“半夜三更,谁看得见啊。”
于是,我拿着药罐头站在阳台上,趁没有人的时候,把里面干巴巴的药渣倒了一半下去,然后趴在阳台上,久久地盯着楼下的路。已经快十一点,路上空空荡荡,等了半天只有一个老太太走过,却心明眼亮地绕开了那堆药渣。
“怎么不踩呢。”我抬起头,嘀咕了一句,正要把另外一半也倒下去,看见对面窗前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个人,在橙色的台灯光里,他正看着我。
两栋楼隔得不远,我甚至能看见他鼻子里塞着棉花团,脸上有点诧异的表情。下一秒钟,我意识到,他就是前些日子在菜场看见的那个骑自行车的男孩,没想到他就住在对面。
在不同的城市里搬来搬去,我已经习惯对别人的眼光视而不见。但他有一双清澈的眼睛,看人的眼光很善意,像果冻一样。
那样的眼光让我慢慢脸红起来,我看看手里的中药罐,心想,他大概看见我把药渣往楼下的路上倒了,所以才会觉得惊讶。
透明的玻璃墙
我们就那么愣愣地看了对方几秒钟,然后他冷不丁地抬起头,一动不动望向天空。他鼻子里那团棉花球,像个黑暗中的樟脑丸。
我不由自主地跟着抬起头,大楼中间窄小的一片苍蓝夜幕,像城市脏污丑陋的水泥外衣上一块美丽的补丁,上面缀着星星月亮的图案,一个弯钩,几点碎钻般的亮光,没有什么特别离奇。
我把目光移回来,他却依然望着天空,而且伸出手去,放在鼻子上那个大白棉花球上。
我这才明白,搞了半天,他看着天,是在防止自己流鼻血呢。
我想起那个故事,一个人在街心流鼻血了,于是望着天空,结果满街的人都不知就里地跟着他往上看,不由觉得好笑。
就在这个时候,三楼的胖女人在楼下叫起来,“喂,谁把东西倒在路当中了?啊?”她抬起头,站在这边门楼下,对着上方大声喊着,“哎唷,好像是剩菜嘛……谁这么不讲公德心?唉,小林啊,是不是你倒的?”
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躲进阳台的阴影里。对面阳台上的那个男孩捂着鼻子看了我一眼,然后很快低下头望着楼下,“苏阿姨,不是我倒的。”大概是鼻子的关系,他的声音沉沉的,有点闷。
“那你有没有看见是谁倒的?”胖女人还是不依不饶。
“没看见。”他继续回答。
“唉,大家都自觉一点啊!”那个女人依旧不依不饶地叫着。
这会工夫,我已经拿着中药罐子回到屋里。小阿姨在客厅嘀咕着“真是三八”,一边用力地把一堆颜料笔泡进脸盆,桌上一幅广告画已经呼之欲出。
我把药罐子里剩下的一半药渣倒进垃圾袋里,小阿姨问我干什么,我说“刚刚只倒了一半”,她有些不高兴,“你怎么搞的,这样不吉利的。”
我关上阳台的门,拉起窗帘,又看了对面一眼。二楼那家的窗户已经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