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80-衰与荣-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法。你从哪儿学来这些聪明?赞叹不已。隔几天不这样向他讲一堆啰啰嗦嗦的生活流水账,她就憋闷得慌,她在一切人面前装样子,唯有对他可以畅谈。翁伯云呢,隔几天不听她嗡嗡上一耳朵,也觉得少了趣味。
和你讲话痛快,你是最好的听众。
是吗?很高的评价。
知道我还为什么愿意对你讲话吗?
不知道。
我愿意听到你的惊叹和夸奖。
那我就多多的惊叹和夸奖。哟,是吗?太聪明了。
她大笑不已。
不过,他并不总是夸奖和附和,时而也提出忠告:“你这件事情就稍有些聪明过份了,太过份也不好。”
“接受你的意见;别再打断我了,听我往下讲。”她其实喜欢听这样的忠告。
翁伯云是从美国归国的博士,身价高,虽是单身,却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黄平平有时也领着人到这儿活动。嗳,我今天要举办一个小型舞会,借你的地方用用。她在电话中说。好。他自然答应,预先便把房间收拾了。
她领着人们来了,跳啊,舞啊,地方不够搬桌挪柜啊,教练啊,张罗啊,指挥调动啊,和中年男人跳,和漂亮小伙儿跳,说笑啊,拍手啊……他饶有兴味地坐在一边。邀他跳,他摇头。不会,也不想学。她骂他老夫子,便撂下他,到人群中热闹去了。半夜了,人们尽兴而归,剩下满屋烟气,杯盘狼藉。她一下清静了,才想起他。他刚刚送走客人回到屋里,含笑看着她,像看一颗掌上明珠。她心中不禁动了一下。一晚上冷落了他。我跳得好吗?她问。好。他点头,把毛巾递给她。她擦着汗:真好假好?他依然含笑看着她:当然是真好。她心中又感到了什么。只有在他面前,她才扮演另一种角色。我帮你打扫吧,她看看乱糟糟的房间。不用,等你走了,我自己慢慢打扫,你累了。她看着他,又看了看表:太晚了,不想回家了,我在你这儿住一晚上吧,有地方吗?他一下忙起来:有。你睡房间里。床单换一条干净的。我睡在这沙发上。
睡下了,她听见他穿着拖鞋在门厅里慢慢走来走去。已是后半夜了。他轻轻敲了敲房门。她从床上撑起头:有事吗?
他站在门外没有说话。好几秒钟静默,夜很沉寂。
我累了,而且,主要……我没有心理准备。她说,唯恐伤害对方。
……对不起,你睡吧。门厅里的灯也熄灭了,听见沙发弹簧吱吱响着。他也躺下了。她拉开窗帘,头枕手臂,目光矇眬地看着窗外。
她不能想象和他发生关系是什么情景,她从未这样想过,她对他没有过这种欲望。她睡着了,梦见自己变成六七岁的小孩儿,在外面玩耍,累了,一身热汗变凉汗了,回家了。父亲来了,母亲来了,又都不见了,面前站着的是翁伯云。翁伯云隐去了,一个暖烘烘的草窝,停着一只小鸟。
政协礼堂的舞会是个老派的舞会,一多半老知识分子,绅士气,知识气,有点沉闷。没有迪斯科的疯狂节奏,都是古典舞,人们规规矩矩地一对对舞着,舞曲停歇时,又都规规矩矩散到舞厅四周。也有不少年轻人,但大多是高知子弟。又一曲舞开始了,翁伯云把黄平平介绍给一位朋友:你们跳吧,我不会,我喜欢看。黄平平随着旋律舞入场中。舞伴是个六七十岁的老教授,戴着金丝眼镜,瘦得两颊下凹,喉结凸起,可一和她搭挽上,立刻精神抖擞,竭力使舞步显得潇洒年轻。那兴奋,言语,目光,无不要博得她的好感。真是人老性在。可笑。她扫视着舞厅,发现有三种结构模式:年轻人与年轻人跳,含情带笑;老年人与老年人跳,多是夫妇,缓缓旋转,无言语,很拘谨,转出了几十年共患难的节奏;老头子与年轻姑娘跳,有几对一看就是父女,更多的就说不清了,一些很可爱的姑娘。老家伙们怎么把她们“拐”来的?
曲终停歇,老教授摘下金丝眼镜,用手绢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同时不中断谈话,好像这样就能使她不离去。她含笑应付着,目光却四下张望,想发现自己认识的人,这个圈子她比较陌生。她不愿意陪老头子跳舞,或者说不愿意陪她无所求的老头子跳舞。她的每一点支出:时间、精力、感情都不能是白费的,或者为了享受,或是为了进取,或是为了光荣和满足。
上卷:第五部分我喜欢像你这样的美男子
又一曲开始了,老教授精神抖擞,准备向她伸出双手。她四顾着,同时不得不准备再白陪一次。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出现在面前,容光焕发地伸出手:平平,我请你跳好吗?好。她高兴地和他搭挽上,转过头礼貌地冲老教授点点头。老教授眼睁睁地看着小伙子,露出一丝悻悻然。
这才是舞蹈的旋律,这才是青春的旋风,这才快乐。阳光灿烂,青松挺拔,谁愿意在一棵老朽的树旁佯装快乐呢?一条小路从山上如狂舞的飘带盘旋而下,两辆自行车鸟一样飞下来,满山笑声。
“你怎么到北京了,齐胜利?”她问,同时眼前浮现出去年和他在一起亲昵厮混的情景。
“我专门找你来了,新华社有人说你来这儿了,我就又追到这儿,好不容易才进来。”齐胜利答道,他有一张英俊稚气的孩子脸。
“找我干什么?”
“我……要和你结婚。”
“别说傻话了,我可不能要你当丈夫。”
“我下决心了,一直在北京跟着你,直到你答应我。”齐胜利的样子非常认真,以至有些口吃。
“还是当小弟弟吧,你比我还小一岁呢。”她有些在意了,但并不急,仍然半开玩笑地说着。
“不。”
“我早已有男朋友了。”
“不可能。这两天我在北京调查了,知道你和那个叫翁伯云的博士不错,可你不会嫁给他。他比你大十多岁,我刚才观察你和他讲话了,你根本不爱这老夫子。”
“别这么说他,”黄平平有些不快,“他可不比你差。”
“他敢和我一块儿游泳吗?敢跟我比健美吗?看看谁强。”齐胜利用力曲了一下小臂,鼓起凸凸的肌肉。
黄平平笑了,她喜欢他,“人不光靠肌肉。再说,我又没说他就是我男朋友。”
“别人也不是,我能看出来。翁伯云纠缠你,我等会儿就去找他谈谈。”
“你疯了。”黄平平嗔道。她喜欢他这样单纯热烈,但又感到事情小有麻烦——她从没有被麻烦过。
一曲舞罢,正好来到翁伯云坐处。齐胜利走到他面前,直直立住:“您是翁伯云教授吗?……我叫齐胜利。”
“啊,您好。”翁伯云礼貌地站起来。
黄平平忙在一旁介绍道:“胜利是我去年在武汉采访时结识的朋友。”
“我和她不是一般的朋友。”齐胜利正视着翁伯云,声音不高却郑重地说。
“那更好。”
“我是她男朋友。”齐胜利用意义明确的声音说道。
这场面足以使任何一个姑娘难堪无措,但黄平平只是一笑,往翁伯云身边靠了靠(她知道这个举动的含义,它将在翁伯云那儿引起她所需要的心理反应),看着齐胜利说:“你和我的关系,我和伯云讲过。”
“是。”翁伯云说道。他不知原由,也从未听过齐胜利的名字,但他知道此刻应该如何保护黄平平。
齐胜利的气势顿时没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这时,一个人走过来:“平平,找你真不容易啊。”
黄平平一看他,高兴地笑了:“伯云,胜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肯定都听说过他,这就是李向南。”
武汉东湖,风平浪静。黄平平穿着游泳衣躺在小船尾部。齐胜利穿着游泳裤,双脚蹬住船底,身子一次次后仰着稳健有力地划着双桨。他胳膊上的肌肉在阳光下一下下凸起着,抖动着。随着他肌肉的一次次爆发,能感受到船很猛的冲力。这冲力传递到她身上,她便感到身体起着一种兴奋。
武汉东湖比杭州西湖好得多。他一边划一边用孩子般的南方口音介绍道。你怎么老看我?我是幅画?
我觉得你美。
是吗?我给你表演个更美的。他收桨,站到船头,一个鱼跃扎入水中,好一会儿露出头:美吗?
美。她被刺激着,也跳下了水。
他踩着水,双手向她泼水,她睁不开眼,换不了气,呛水了,有点手忙脚乱起来:别别,我水性不行,会淹死的。船在哪儿?她想抓船,但船已漂到几十米外去了。她慌了:快,快拉住我。齐胜利咯咯咯地笑着,用侧泳拉着她一起游到船边。俩人在船上晒太阳,身子晒干了,醉融融的,天空澄清无比,湖水荡荡的,躺在一个透明的与世隔绝的世界里,便生出无限情欲。
你躺得离我近点。她说。他挨着她躺下。她侧过身搂住他,轻声说道:你知道吗,许多女人对男人重才不重貌,可我重视,我喜欢像你这样的美男子……
上卷:第五部分人生就是一次次危机
面对三个男人。一个,健美的体魄激起她燃烧的情欲,她享受女人的快感(她绝不会同一个体貌干瘪的男人睡觉,哪怕他是伟大的天才);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她更多时候愿和他来往;一个,她身后的安乐窝,可以靠靠的暖墙。都到一起了,好办。
胜利,明晚你陪我看电影,有话到时再说,好吗?(扶着他胳膊,含着情意)约好时间地点。向南,你有事吧?咱们出去谈。没关系,我对跳舞无所谓。翁伯云,我们上你那儿谈,借贵方一块宝地,行吗(带点娇嗔)?中午顺便给我们弄点吃的,啊?
翁伯云自然遵命。
她愿意这样驱使他,也稍有不安:遣使多了,欠得也就多了,到一定时候,就把自己“抵押”了。不要再这样了。可为什么总没煞住呢?
向南,你喝点什么?汽水?好,我也喝汽水。翁伯云,你呢?一进门她就拉冰箱,开瓶,拿杯,加冰,叮叮哐哐,如同回到自己家里。翁伯云礼貌地问:平平,你们在哪儿谈?到我书房里谈吧?那儿安静些,我可以在门厅里看书。黄平平一挥手:走,向南,端上杯子,咱们到里面去谈。翁伯云,你有兴趣可以进来。不不。——翁伯云摇了摇头。
书房挺雅致。贴墙一排四个大书柜,玻璃后面各种精装书,外文书,一壁堂堂皇皇,对李向南有着某种隐隐的压力。薄纱窗帘,写字台上的玻璃板绿荫荫地像一面湖。空调嗡嗡响,很凉。黄平平在转椅上转了转,她注意到李向南目光中的某些疑惑。听说过翁伯云吗?她问。李向南摇摇头:他是……黄平平笑了笑:他是从美国回来的建筑学博士。看到李向南还在等她讲下去,就又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关系有点特殊?也没什么,他是我最可信赖的人,我什么都愿意和他讲。就这些。
酸溜溜的一股劲涌上李向南的嗓子眼,这么说,自己远不是她最信赖的人?本来这很正常,可现在颇让他受不了。那个武汉小伙儿呢?黄平平和他有着一种与自己没有的特殊友情。别难受了,世界本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男人也不止是自己。不过,他不能不佩服黄平平: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她最信赖的人呢。大概所有与她交往的男人都有这种错觉吧?
还有刚才的舞会,自己一踏进去就有一种外来户的感觉。这里有着另一种优越感。他穿得太邋遢,舞也不会跳,东张西望的,让人白眼,小心翼翼地溜边走,略觉局促。当然他没有忘记自己的骄傲。演奏的乐队仪表堂堂,穿着镶金边金扣的白制服,像是俄国沙皇的仆役,及至演奏到兴奋时,钢琴师便对着麦克风奔放地歌唱起来。整个大厅的气氛都被他史诗般的男中音感染了。贵族的艺术。
他要谈的事既复杂又简单:想把一份条陈送到成猛手中,托平平帮忙。
平平沉吟了一下:我帮你试试。
李向南信赖她,她能帮助李向南,都使她生出热情。李向南毕竟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但是她对他又略有一丝轻视,非搞政治不行?处心竭虑的有多大意思?
你这是为了坦率表白自己,上边能理解吗?她说。
是有求于她,还是第一次真正了解了她,李向南发现自己与黄平平的关系无形中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削减了他对她的亲昵感,却激增了他对她的征服欲。
我并不是非搞政治不行,但已经搞了就绝不认输。人生就是一次次危机:我喜欢和危机作斗争。他平静地说道。送条陈的事如果有困难,你就不必多费心了。他站起来,一切要简洁。
不吃点东西了?黄平平一下有些急了。向南,你等等,我跟你一块儿走。她拿起挎包;翁伯云,我们先走了,有事我再给你打电话吧。
翁伯云彬彬有礼地送他们下楼。
我这就帮你去想办法。黄平平又开始充满热情。
李向南走着,没说话。
还要我帮什么忙?她又问。
李向南站住了:平平,告诉你我的一个心理。有人驾小帆船横渡太平洋、大西洋,有人孤身到北极探险,我挺佩服他们。可每当他们半途而废,我就替他们扫兴,会骂一句:软蛋。不能坚持到最后,就不要开始;开始了,就不要退下来。
那你还有什么灵活应变啊?黄平平说道。
李向南继续走着:平平,我能理解你的聪明,我赞赏你的聪明。
我有什么聪明?黄平平略有些不自然,她的聪明在于别人识不破她的聪明。
好,再见吧。李向南在车站旁站住,伸出手:我希望今后能得到你更多的理解。
她莞尔一笑,没说什么。
上卷:第五部分似乎很正派,绝不对女人挑逗
七八个五六岁的小孩儿在院子里忙忙碌碌“过家家”,像窝快乐的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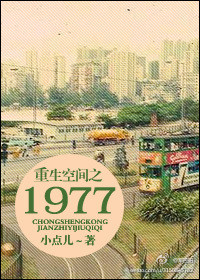

![埃提亚[更新至 第229章大地权杖胡戈第的黑暗阴影(下)]作者:上帝不在天堂.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