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80-衰与荣-第6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晓时继续讲着话。第二个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剖。第三个问题,深刻全面地估计文化的发展规律。第四个问题,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我们对传统文化应持的态度,就是历史采取的态度。
在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起过合理的作用。它存在几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而现在,历史对其提出了否定、批判。我们这么多人的批判发言,这几年来各个领域的批判,都是历史在执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几千年不是偶然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近代、现代遭到批判,同样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历史首先提出的,我们的声音是历史赋予的。自觉到这一点,就可以更有力地实行这一批判。实际上,西方文明的进入,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方面的批判,早就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了。
历史的发展本质是批判的,就如生命,每时都在批判这一瞬间,在批判中同时发展着新一瞬间。这新一瞬间正是通过批判,吸收并综合了旧的一瞬间。
我们必须对“批判的继承”这个口号的通常意义提出质疑。在这个口号下,辩证法被简单化为机械的一分为二:对传统文化否定一部分,肯定一部分。似乎全部工作只在划一条分界线。好比吃饭,剔除骨头,吃下肉,就是批判的继承。其实,深刻彻底的辩证法表现在:全部吃下去的肉,都要被我们的肠胃进行批判。一切都被分解了,改变了,重建了,更新了,原来意义上的肉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停留在区别传统文化什么该批判,什么该继承,是非常懦弱的,甚至是空洞伪善的方针。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对整个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如果其中有什么因素今后留下了它的影响,那也完全是被重建了、更新了的。
现在唯一要强调的是批判的无情与彻底。……
下卷:第一部分黑色的大江在神秘地旋转
夜晚,他和邹芮琴又在复兴路上散步。“你小时候什么样,可聪明了吧?”她突然问。他笑了:还没人问过我小时候的事呢。“我想知道。”
可以。我喜欢研究人的童年,那是研究人的好办法。我小时候的事可多了,讲哪方面呢?我很小时住过南京,二层楼上,红色的地板地,家里买了一套新家具。爸爸妈妈一出去就把我锁在家里,有时还把我绑在沙发上。(“为什么绑起来啊?”)怕我调皮呗。我每次被锁在家里,都要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我从来没有安分过。我喜欢把家变来变去,箱子里的东西全翻到地上,床上的东西放沙发上,沙发上东西装箱子里。我喜欢爬上爬下,攀登一切可以攀登的高度。我不喜欢秩序,不喜欢被管制,不喜欢被囚禁。我至今不喜欢被“囚禁”在任何地方。不管是用锁、用房间、用户口、用工作、用事情、用伦理、用义务、用感情,用一切东西来囚禁我,限制我,我都在心理上反抗。从小养成的。
幼年时,我跟着父母跑了很多城市,经常搬家。
颠簸的火车,发蓝发冷的天空在车窗外掠过着。路边的树掠过着,长堤掠过着,长堤上长满了草。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在车窗外掠过着,大地旋转着,山在天边慢慢旋转着,河流湖泊在大地上移动着。天已经黑了。车厢内的灯光昏黄。在座位之间用箱子搭成了小床,他便睡在那儿。父亲靠着座位瞌睡,母亲在照料他。人们乱哄哄地挤来挤去,一个农村妇女抱着婴儿倚在车窗睡着了。她的嘴半张着,很痴憨的样子。下了火车,又换马车。这是在南京城里了。马在前面拉,车在后面像个小轿,和妈妈坐在里面。马车夫扬鞭赶着。住了没多久,又离开南京了。那一天是夜晚。家里来了许多客人,记得有楼下那个医生。吃饭,忙碌,马车、汽车来了,搬东西,从楼上到楼下,乱糟糟。汽车在街上飞驰,颠簸,路灯在街上掠过,大概是到了长江边的码头。黑暗的大江,灯光闪烁,如梦境一般,觉得它特别大。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夜晚,多少年后,始终如梦般在眼前出现。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人都是影影绰绰的。困倦中好像到了船舱。只觉得江面很高,就在舷窗下,黑色的大江在神秘地旋转着。时间很长,又很短,似乎是过了江,大江在他印象中是那两岸稀稀疏疏的灯火划出来的。后来到了北京,又到沈阳。沈阳在他印象中是一幢陈旧的、没有生气的五层楼房。噢,我给你讲一件有意思的事吧……
他突然停住步,看见杜正光迎面走来。后面远远的,灰影一般跟着石英。“你们怎么了,拉开距离了?”陈晓时问,他大概猜到了缘由。
“我走我的,她走她的。”杜正光火气挺大地说道。
石英在街边远远站住了,杜正光回头看了一眼,转身走了。
陈晓时走到石英面前:“又吵架了?”
石英低着头用脚轻轻蹭着小草,眼泪慢慢流了下来。
陈晓时看着她,想到了两年前的秋天。
下卷:第一部分那是送殡的队伍
天高云淡,群山起伏。离小城不远的山地里,一个黄土峁上坐着五个人,杜正光,他妻子薛惠敏,他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他四岁的女儿。第五位是他的同学,远方来客陈晓时。他们是星期天来郊外游玩的。这会儿铺着一块蓝塑料布,围坐在已经收割了的庄稼地里,在他们中间散乱摊放着吃剩的面包香肠、水果汽水。
已是下午,太阳偏西,可能是玩兴已尽,他们有些疲倦,天地显出一片辽阔无边的寂静来。黄土高原沟沟峁峁地展开着。像凝冻住的黄色海洋。在西面平缓化为烟霭浮罩的小城市,在东面扩展到天边,拱起绵绵的青色山脉。
真静,能听到耳鸣。
北面一两里处,壁立着一段雄奇的石崖,是一千多年前凿就的一孔孔巨大石窟,能依稀看见石窟中那一座座大石佛大慈大悲的微笑。
广阔的寂静中隐隐地传来一种声音,极远的,似乎是唢呐吹奏的乐声。眺望的目光终于看到:在远处山脊上一行穿着白衣服的人,像一线小白点在缓缓移动,那是送殡的队伍。似乎还听到了嚎哭,若有若无。白色的队伍沿着山脊缓缓移动着,越来越远,越来越高,又沿着山脊慢慢落下去,一点点消失在山脊后面。唢呐声越来越细微,终于一点都听不见了。
老太太人老眼不花,这会儿收回目光,盘腿坐在那儿叹了口气,唠叨道:“人活着就是一辈子,活过去就活过去了。”
杜正光正撑着头很舒服地躺着,这时抬起头很爽朗地一笑:“妈,您说的可真是句大实话,谁能活两辈子?”他惯于用笑来活跃气氛。这是他的魅力。他笑够了,话才接上:“不过,现在人长寿了,一般都能活八九十岁,像妈妈这样的,肯定能活一百岁。要和过去的人比起来,这就差不多顶两辈子了。”
“过去得痨病,没办法治。”老太太没有笑,感叹地添了一句话。
不知为什么,谁也没再说话,辽阔的秋天露出一丝初现的肃杀。
陈晓时侧身很惬意地斜躺着,隔着塑料布能感到土地的温意。山,云,风,阳光,土地,树木,庄稼,田埂,鸟雀……他神思恍惚地沉浸在黄土高原的秋意中。
眼前的一家三代四口人像一幅画。老太太头发花白,但精神健朗,她拿着一个旅行水壶让小孙女喝桔子水;四岁的茸茸长着红苹果一样的圆脸,正聚精会神地玩耍着小石子儿;薛惠敏静静地坐着,一下午就没听她有什么言语,一边慢慢地织着毛衣,一边含着善良的微笑,显得端庄朴实又有些憔悴;杜正光则依然侧躺着,笑看着自己这一家人。
这是一幅天伦之乐图。可为什么自己稍一眯眼,那一丝冬天一样的黑色就在后面隐隐微现呢?这是什么幻觉?杜正光凝视妻子的目光中似乎露出了瞬间的冷静观察?
不,只有一片幸福,再没有比这寂静天地间融融洽洽的一家人更显得和谐的了。
突然,远处传来快节奏的叮铃铃声,一辆自行车沿着田间小路飞快地左右回旋着骑来,一个姑娘的红色风衣像旗帜一样飘动着,一条狗跟着她快活地跑着。
“杜老师,你的信。”车到,跳下一个生气勃勃的姑娘,大黄狗在她身边摇着尾巴转来转去。
“什么信?”杜正光一边起身接过信,一边给陈晓时介绍道,“这是石英。这是陈晓时——你可能听说过他的大名——我和惠敏过去的同学。”
看见陌生人,石英不好意思地笑笑。“大姐,你给谁织毛衣?”她挨着薛惠敏坐下,亲热地问。
“给茸茸织。”薛惠敏慢言慢语地答道。“哪儿来的信?”她看了丈夫一眼,随便问道。
杜正光正注意看信,没回答。
“是《时代》编辑部来的。”石英代为回答,“肯定是杜老师的中篇小说要发表了。”
“你怎么知道?”薛惠敏问。
“我也收到他们一封信,让我去改小说稿。”石英压抑不住兴奋,“我给他们寄过一个短篇,就是上次杜老师给我看过的那篇,我和杜老师一天寄去的。杜老师,他们已经决定用你的稿了吧?”
杜正光看完信随手叠好,又想到什么,把信递给了妻子,“他们也让我去改稿。”他转头冲陈晓时一笑:“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时代》决定用,但是又要我去编辑部作些修改,可能嫌有些地方太尖锐了吧?”
“为发表,总得有所妥协吧。”陈晓时说。因为这个漂亮的姑娘,杜正光的倦淡一下消散了,变得容光焕发,微凸的眼睛幽默地闪着微笑。陈晓时心中也笑了笑。同时他还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也坐了起来:“那你们也要去北京了吧?”
“看来得去。”杜正光说,“要不,他们不给你发啊。”
“杜老师,我和你一块儿去吧,明天就走。”石英兴奋地说。她对他称老师并不奇怪:杜正光比她大十多岁,她在学习写作,时常请教他。
“你们如果明天走,咱们就能同车了。”陈晓时说道。
“咱们就明天走吧,杜老师。”石英显得急不可待。
下卷:第一部分要发表处女作了
“瞧你急的,要发表处女作了,就像小孩过年一样。”杜正光揶揄道,“不过,咱们来不及,总不能一拍屁股就走吧。”
“怎么来不及?我今天就去给咱俩请假。星期天也没关系,我去找领导。”
杜正光笑了:“急也不在乎这一天嘛。还是过一两天走吧。”他转过头,“陈晓时,你不用等我们。我到北京再去找你。”
陈晓时说:“行,北京再见吧。”杜正光并不愿意和自己同行,这里的奥妙是可以想到的。他心中笑了笑,不禁又看了石英一眼。
很可爱的姑娘,她的到来使整个气氛都变得活跃热闹起来。
石英抱起茸茸和大黄狗一起玩耍。
“黄黄,”她吆喝着大黄狗,“卧下,卧下。”狗听从地卧下了。她抱着茸茸往狗背上放,“茸茸,别怕,黄黄不咬人,分开腿骑在它背上。大姐,”她转头冲薛惠敏一笑,“你别怕,摔不着。杜老师,你说什么?怕把狗压坏?不会,真的没关系。”她哄着茸茸,“茸茸,你坐好,我扶着你。黄黄,起来。”狗站了起来,“走,慢一点。”黄狗走起来,然后慢慢跑起来。石英双手扶着茸茸跟在黄狗后面转圈跑着,一边跑一边笑。茸茸也咯咯笑着。石英一步没跟上,在田埂上绊了一下,仰面摔倒了。她双手紧抱的茸茸摔在她怀里,大黄狗停住步,摇着尾巴回头看着。
石英躺在地上开心地大笑,茸茸在她怀里也笑了。
所有的人都笑了。好不容易停住笑,石英抱着茸茸拍着身上的土站了起来。
那边山坡上响起高亢婉转的民歌,远远望去,一个穿红运动衣的农村小伙子在梯田上慢慢赶着白云似的一群羊。人们都静了,是一首情歌,在黄土高原上远远近近地响着,描绘出天高地阔和古莽苍凉。
糖包的油糕蘸上蜜,
咱二人成了好夫妻;
落花生角角剥了皮,
心上的人儿就是你。
…………
歌声使人心醉。
石英眼里噙满泪水,她放开怀抱着的茸茸,掠了一下头发向前走了几步。人们不知道她要干什么。突然,她略提了一下身子,放声向着那远处的山坡唱了起来。
青青杨柳风摆浪,
死去活来相跟上;
河滩石头海里的水,
我心中爱谁就是谁。
…………
她唱完了。歌声凄越婉转,在淡淡云天缭绕。人们都期待地凝视着对面的山坡。白云似的一群羊在缓缓移动。
对面山坡上的歌声很快响了起来:
三颗颗星星一摆六六地升,
年轻人儿爱着年轻人;
柳叶叶落在树根底,
天南地北想着你,
…………
因为有姑娘对唱,歌声中明显增添了刚才没有的激情。
陈晓时极为热切地转回目光看着石英,这种北方农村的对歌,他还是头一次见。石英有些兴奋地挪了挪脚,清了一下嗓子,很快又唱起来:
头茬茬韭菜长不高,
二茬茬韭菜冷水浇,
旁人都说咱俩好,
为什么撂下妹妹光你跑。
对面的歌声接着她的余音就响了起来:
墙头上种谷我回不过牛,
提起出门我泪长流,
不是我狠心撂下你,
因为我家穷走西口。
石英更为兴奋地紧接着唱了过去:
冰盖的房子雪打的墙,
咱二人相好概不长。
对面的歌声又高亢地对了起来:
你在家里我在外,
哥哥定要回家看你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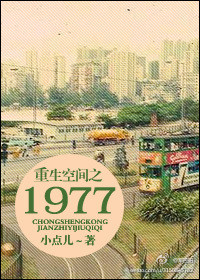

![埃提亚[更新至 第229章大地权杖胡戈第的黑暗阴影(下)]作者:上帝不在天堂.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