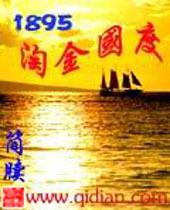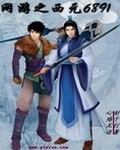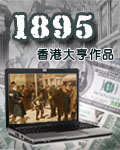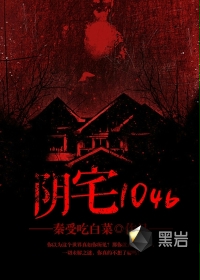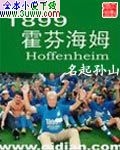4689-托普检讨-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另外从全兴和申花冠名的方式上而言,全兴的“优惠条件”也是申花不能相比的。“全兴”愿意在球队的队名中全身退出。而托普入主申花后,球队的名字保留了“申花”二字。
然而即便如此,最终托普还是远嫁他乡。可以想见四川人是何等的失落。当时流行的一个普遍说法是,托普本有意接受四川全兴足球队的冠名转让,可是被“商务通”捷足先登,才不得已转而投向申花,弄了个天价合同,这是事实的真相吗?根据前文所述,宋如华出川入沪蓄谋已久,这个传言显得托普很无奈,主要是起了放烟幕弹之效。
于是,2001年甲A联赛开赛时,我们看到了喜剧性的一幕:与申花队合作的托普是四川企业,与全兴俱乐部联姻的“商务通”是北京企业。一个东进上海滩,一个挺进大西南。据了解,商务通是以1600万元买下了全兴俱乐部队一年冠名和胸前背后广告。
一转眼,2001年的隆冬就来临了。从10月下旬开始,四川就有板有眼地传出了托普即将2000万收购全兴足球俱乐部的消息,消息说双方已经起草好了转让的相关文件,一旦时机成熟,双方即刻完成签约手续。此时,申花还未与托普正式“分手”。
托普可能收购全兴吗?让我们来看看宋如华后来在内部的解释,“托普有必要冠名四川的足球队吗?在四川几乎人人都知道托普,我冠个名图啥,还有什么意思。而上海就不一样了,以前别人都不知道托普,现在怎么样?一说起托普,谁不知道呢?”
宋如华深谙炒作之道。他知道在联赛结束哨声吹响前后,“冠名”某支球队的新闻是最能吸引人眼球的,之所以选择拿全兴开刀,是因为它最具有被人炒作的“要素”。时间证明了一切,宋如华不但炒作了全兴,还炒作了浙江绿城、河南建业以及辽宁金德等足球队。
就在申花球队改名的前一天,全兴集团正式宣布将退出中国足坛,但接下去的100多天—— “只见雷声不见雨点”的托普始终没有一位核心决策层人士出面商谈冠名事宜,双方唯一的联系就是四川福特宝公司一负责人,价格一压再压,据说后来连2000万的心理底线也击穿了——全兴球员终于忍不住提出罢赛罢踢,联名上书,要求俱乐部给一个说法。
托普的用心和诚意让球员怀疑,也让四川媒体“难以容忍”。
2001年12月24日,《华西都市报》以“历史机遇在眼前 四川足球向何处去?”为题写到:
尽管从目前了解的信息看,跃跃欲试的“下家”众多,但真正下决心接棒者至今仍未确定。因此,除相关职能部门要为全兴足球的平稳交接出谋划策外,我们更要吁请省上领导旗帜鲜明地为交接棒牵线搭桥,同时发挥政府的协调职能,因为全兴足球的退出和交接绝非仅仅是单纯的商业行为,它是社会影响面很大的一件事。省上领导曾公开表示“群众关心的事就是大事。足球就是群众关心的大事,政府不能不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期盼着有魄力、有实力,负责任、有远见的接力者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重振四川职业足球雄风。作为传媒,我们更愿意为此再次大声疾呼:川足兴亡,匹夫有责。
在掌声与唾沫之间,托普痛并坚持着。虽然历史永远只能给人看得见的一面,但闹翻上海、戏弄四川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第一张,足以证明宋如华正一步步走下神坛……
《托普检讨》 上市前夜的一份传真件《托普检讨》 “帝国”生死棋局
●27个软件园:“帝国”生死棋局
如果1997年宋如华没能拿下西部软件园的国字号牌子,以后的托普又会是怎样的呢?有人说,托普可能早就玩完了,“死于内讧,或者死于多元化”。即使活着,也不会那么潇洒,有人下判断,宋如华更不可能成为福布斯中国内地前50名的富豪。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当宋如华拿下“西部软件园”,他的“机会”来了。
当时就有一家广西的上市公司愿意出资5000万收购西部软件园的牌子,要知道,1995年底,托普的销售收入也不过4000多万,而仅仅一个牌子就价值5000万——这让精明的宋如华闻到了资本的诱人气息——借此“东风”,1998年托普重组川长征,“川长征”更名为“托普软件”,宋如华在资本市场上一鸣惊人,被人称为“资本运作高手”。
西部软件园带给宋如华的“机会”还远不止于此。学界出身、商界生存的背景,使宋如华充满了接触政界的渴望,而西部软件园不仅拉近了托普与政府的距离,更关键的是润滑了双方的关系,搭建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公共关系平台——托普从政府手中获得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资源,政府则可以利用托普的软件园寻找打造高科技产业的政绩。
在这场皆大欢喜的合作中,宋如华更重要的收获——是他还发现了一个来钱更快更容易的门道——以“建设软件园、投资换市场”的名义圈地,使土地资源转换为土地资本,然后再把这个土地资本重新评估后拿到银行“套现”,如此鸡生蛋、蛋生鸡,只要托普能源源不断地从政府手中拿到廉价的“高科技”用地,银行就好比是宋手中的一个钱袋。
创业5年来,托普虽然也经历了诸多风雨,但总的来说,运气一直比较好,“一个事业,有心这样做,却无意中走上了另一条路”,1995年12月,托普第一届技术代表大会开幕式,宋如华说,“托普人总能够把一件事推向一个事业”。在宋看来,所有的好运都是上天注定要给托普的。“就像西部软件园封顶那次”,宋如华总爱津津乐道地向别人说起这件事情,“8月的成都雨老是下个没完,软件园里积水不断,根本无法施工,更不要说封顶了,眼看9月的开园要泡汤了,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办呢?我们的开园日程已经安排好了的呀。我就带着大家跑到楼顶,拼命地喊‘不要下了’!结果怎么样?嘿嘿,雨还真停了!”
以后的更多经历,似乎更“证明”了宋这种“吉人自有天相”的逻辑。
在“把一件事推向一个事业”确立为托普战略的背后,宋如华便“一发不可收拾”,弃软件研发于不顾而择圈地为主业。毕竟,这比辛辛苦苦卖PC、显示屏、税务软件轻松多了。对“宋老师”而言,显然,这个生意让他的面子也比过去光彩多了,因为赚钱的含金量似乎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他开始彻底玩资本、开始大搞“复制”。
跑马圈地后,宋如华先投资几百万元搞基建和绿化,高额评估后,以抵押贷款方式从银行圈钱,或者加价转让给上市公司等子公司。如法炮制的过程中,宋如华也一直在寻找资本运作的机会。截至其2004年消失在公众视线内时,托普在全国数十个省市开发区建了27个软件园,占用土地超过12万亩,而且每个园区的投资据称都在1个亿上下。
这27个软件园就像27枚棋子,谁能想到,在托普的这盘生死大棋局上,宋如华最后是自己把自己给下“死”了。不“死”也不容易,因为这27个软件园组成的资金链,就像一个连环的定时炸弹,一环扣一环,只要有一环出了问题,就有全盘崩溃的风险。
●从“东大软件园”看出新门道
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借助托普北京工作部打通的关系渠道,宋如华积极主动地建立起了自己在软件行业尤其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一些人脉资源,此“关系渠道”为托普快速跻身全国软件产业的“前列队伍”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明确中国发展民族软件产业的思路,1996年,国家科委(现科技部)软课题《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战略与对策研究》的总体组织及研究工作全面展开,作为软件企业代表,宋如华、李智参与了该课题的部分内容的起草工作。
1996年9月,带着尚未解脱的“叛乱”阴影和对托普未来发展的困惑,宋如华参加了在沈阳召开的“全国软件产业发展研讨会”,并参观了东大软件园。东大软件园聚集人、物、财的神奇力量让宋如华兴奋不已,此前他坦承并不知道软件园是什么。
1995年是东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年”。当时的背景是,沈阳浑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一块闲置的征用地,一直都没有企业进驻,开发区希望东软能进驻。目的很简单,“买几十亩地,为开发区的建设造一些声势,给其他高科技企业带个好头。”
历史的起承转合总是在不经意间。
第二天下班后,时任东软总裁的刘积仁与公司后勤部长等4人带着地图一同驱车到开发区考察,极目望去,荒无人烟,除了豆秧就是叶茎上挂满刺球的荒草……这时大家都默不作声,因为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刘积仁心中一直都有个梦,那就是建造“一座能凝聚中国年轻IT人的软件园”。可是,就在眼前的这一块地能让他满意吗?
5分钟后,“要买就在这儿买”,刘积仁指了指手中的地图坚定地说,“这里离高速公路出口近,进市内方便,离机场也近”。就这样,东软在开发区一圈就圈了800亩土地。刘积仁的“梦”源自于其看到如下一个现实:国内高校企业开发出来的科研成果转化率非常低,而在国外,同样的科研成果大都衍生出一个又一个的产业机会。
刘积仁的这一“搏”让东软找到了真正的发展助推器。在东北大学和当地省市政府部门的共同主导下,1995年10月,东大软件园被科技部授予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称号,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大学软件园——这为东软在资本市场上增色不少。
1996年6月18日,东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顺利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专业软件企业。自上市起,股价走势就一路飙升,受到投资者的大肆追捧,被誉为“中国软件第一股”。东软通过上市公司在电信、电力、社保、教育、企业等行业的优秀经营业绩,先后从资本市场融资6亿元,从而为东大软件园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血液”。
东大软件园的园区内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湖,按照最初的想法,本打算将人工湖的形状设计成辽宁省地图,但当时的省长闻世震在看到施工沙盘时说,“希望东软未来能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于是,人工湖就被设计成了中国地图的形状。
东软前后这一切的变化及其要做“中国的东软、世界的东软”的野心,让宋如华吃惊又羡慕不已。一回到成都,他就在高管会议上提出托普集团也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软件园,就叫“西部软件园”,他要求相关部门负责人尽快准备材料向国家科委申请。
《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战略与对策研究》课题1997年正式定稿,并报送国务院、相关部委负责人,提供决策参考。课题的研究结果,即通过软件园区形成规模效应和积聚效应,发挥其辐射功能,带动区域软件产业,并在全国范围推广。在此之前,也就是在宋如华参观东大软件园的前一个月,国家科委还出台了《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认定试行办法》。
《托普检讨》 上市前夜的一份传真件《托普检讨》 民营企业还有审计部
●“民营企业还有审计部?”
1996年12月,由国家科委主办、四川省科委和托普集团联合承办的“西部地区软件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本来这是一个各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和地方软件企业共同探求未来软件产业发展可选择路径的会议,结果几乎成了一场“托普秀”——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官员在发言时不但屡次提及托普在四川的排头兵地位,而且还盛情邀请与会专家到托普科学城参观;宋如华也是出足了风头,不管是大会还是小会,有会必发言,他还提出了“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软件技术产业化模式,即“以政府的政策支持为后盾,以产业化(企业)为龙头,发挥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技术开发实力,结合用户需求共同开发软件产品”。
有实力,有激情,有想法——这是托普留给参加研讨会人员的总体印象。
3个月后,宋如华的努力“付出”得到了回报。经过选址,托普集团在郫县红光镇科技工业园先期征地100亩,用于西部软件园的开发建设。不久,在考察成都市高新技术企业时,时主管高科技产业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徐冠华也视察了西部软件园园址。在一片开满黄灿灿油菜花的农田旁,宋如华不时向徐冠华等官员介绍托普做大软件产业的决心和托普人的理想。
为了能一举拿下国字号软件园的牌子,宋如华煞费苦心。他深知一个民营企业如果能拿下一个国字号牌子,就等于是拿到了“尚方宝剑”——至少托普的颓势可马上得到扭转,托普多了一个“护身符”,以后的生死也不会那么随便,因为事关地方经济和产业形象。
1997年4月,在国家科委火炬办的整体安排下,由中科院软件工程中心副主任钟锡昌教授、中国软件登记中心主任李维高级工程师、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刘乃琦教授等人组成的专家组,到托普集团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评审软件产业基地。
很显然,一个月前动土的软件园目前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阶段,专家组要评审的基地还只是在建工程。考察过程中,一个托普集团随行人员的话给专家们留下深刻印象,“你是什么部门的?”该员工回答:“审计部。”专家们一下子来了兴趣,“民营企业还有审计部?!”待该员工介绍了部门职责后,托普已经从专家们那里赢得了不少的印象分,宋如华向专家们提供的《托普典章》等文件材料,更强化了托普“管理规范、前景远大”的形象。
5月23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首批4家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授牌仪式在那里举行——“西部软件园”赫然名列其中。从企业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