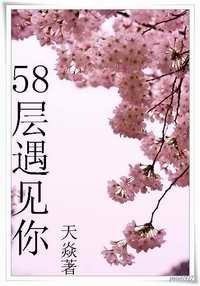580-红墙童话-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受;是在许多年之后,他们才从父母身边的人员嘴里,听说了如下的故事: 那是1960年的春天,一位警卫员领回少奇同志的工资后,就和大家议论起少奇同志的生活问题,“别看他是国家主席,生活也够紧张的,他们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尽管有500多元,可是扣除房租、水电和保育员的工资后,剩余部分既要支出8口人(应该是9口,笔者注)的全部生活费,5个孩子的学杂费,还要支援亲友,少奇同志抽烟喝茶每月要花几十元,即便是精打细算,也难以分配。” 另一位卫士说:“所以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处处要求节俭。” “连孩子们夏天喝点饮料也抠得很紧。有个孩子早就想买辆自行车,但光美说买不起。”保育员最清楚这些。 “最为难的是我这个厨师,逢年过节稍一改善,就说超标准了,这样下去首长的身体会受到影响的,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郝苗的话是很有分量的。 另一位同志有点不平地说:“应该给少奇同志夜餐费,我们不是都有嘛!少奇同志平时出差从来未拿过出差补助,这也是不合理的嘛,按规定该有的也应该给人家嘛!” 卫士长插话说:“你们说的这些过去都提过,可首长和光美同志不同意要。” 这时有人提议:“像这些的生活小事,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看就以夜餐费的名义给他们补助点吧。”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而且不要向他们汇报了。后来经与警卫局主管少奇同志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他们30元,每人每天补助5角。补助就这样开始了。 1962年夏季的一天,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毛主席说,中央几位领导也应该有夜餐费,但他们都不要。现在有的领导同志生活比较困难,准备予以补助。毛主席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嘛。” 后来,毛主席出于对生活困难的同志的关心又在一次小会上提到这件事。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就问光美同志:“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我不知道。”光美同志惊讶地答道。“你去查一查看。”少奇同志又补充了一句。 光美同志立即来到卫士组问大家,卫士们以为别人已经告诉她了,瞒也瞒不住了,便照实说:“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的规定,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个人夜餐费,这样就……”卫士还想讲些理由,但光美同志已经清楚了,“别说了,总而言之是补助了。”她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马上把我和卫士长叫去,严肃地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为什么瞒着我,这些事过去我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吃三顿饭嘛,白天工作、夜间工作,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你们可以要,我不要。比我困难的人还很多,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我感到了他的气愤不平。 停了一会儿,他又追问:“这是谁的主意?”我说这是开会大家一致同意的。 少奇同志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提高嗓门又说:“开会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为什么不报告我?我的生活问题,应该让我知道。我有自己的工资,不能再要国家补助。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要把每次退赔的收据给我。” 光美同志也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赔。以后凡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不要瞒着我们。开始少奇同志以为我在瞒着他,你们是好心,可却帮了个倒忙。” 我们算了一下,共补助了两年10个月,每月30元,共计1020元。从当月开始每月扣30元,还得扣两年10个月。这样一来,每月从补助30元,到倒扣30元,等于每个月的生活费降低了60元。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3节 “成长进度表”
虽然,在生活上,刘少奇给孩子降低了水准;但在其他方面,刘少奇不仅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刘少奇为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0岁学会骑自行车,11岁要会自己洗衣服,13岁能够生活自理,15岁独自出门。 并不是定完就完了,定完是要严格落实的。“我们都依照这个进度表实施,我自己是每项指标都略有提前。游泳是在8岁学会的,也是在八九岁之间,学会了骑自行车。除了拆洗被褥外,我10岁以后就没让别人洗过衣服。”刘源说。 在严格要求自己方面,孩子们从对父亲言行的观察上感受良多。 1956年以前,在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别的房间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物以稀为贵,刘少奇的几个孩子,也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就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三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结果秘书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留下了一台,送给卫士一台,还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有一天,刘少奇到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回答说是楼下的秘书拿来的。 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了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父母亲对孩子们学业、政治进步、人格成长的关心,还反映在对孩子们主课以外的多方面兴趣爱好,如体魄的强健,审美情趣的积淀等,都给予关注和支持。 从那个时候起,乒乓球就是中国的国球了。大人孩子,都喜欢打乒乓球,并以乒乓球打得好为荣。要想打得好,就得苦练。一次,李树槐的女儿李延梅到西楼会议室这边玩。会议室里有个乒乓球案子,刘源见有了对手,两人打得昏天黑地。 直到过了午夜,王光美还不见刘源回家,有些着急了,因为刘源平常一直是个挺守规矩的孩子。于是,惊动了警卫人员,四处去找。最后在西楼会议室里,找到了两个汗流浃背、仍酣战不止的孩子。 作为母亲,孩子午夜不归,让她焦急不安;还影响了那么多人的休息,她心里是挺生气的,但看到孩子并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是在打乒乓球强身健体,就没有太多地指责孩子。 也许是受毛泽东的影响,中南海里的许多首长和干部都对练书法雅兴匪浅,稍有闲暇,就在废旧报纸上练开了。刘源不知从何时起,对中国的水墨画产生了兴趣,家长练大字时,他也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划拉。 王光美首先注意到了儿子的兴趣苗头。一次,中南海门诊部主任郑学文因医疗保健方面的事到甲楼,偶然间发现刘源对画画的兴趣。巧的是郑学文的丈夫,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校长、著名的美术教育家丁井文。当她和王光美攀谈起此事时,遂提议帮助刘源找名师点拨一下。 在丁井文的带领下,刘源一一拜谒了李苦禅、李可染、叶浅予等中国画界的泰山北斗,观摩他们的造化妙笔,聆听大师的开蒙之言。每次登门拜师,丁井文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刘源骑着小轱辘的自行车跟在后面。经丁井文建议,刘源拜声望德行俱佳、又年富力强、和丁井文交谊最厚的黄胄为师。 就这样,刘源投在黄胄门下学习中国画。听说刘源拜到了名师,中南海里另几位有同好的孩子,也和他一起学艺,也跟着丁井文遍访画界大师,到中央美院和美院附中观摩学生绘画。这些孩子中有朱德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等,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还都在丁井文当校长的中央美院附中,受过正经的科班教育。 名师出高徒,几个孩子经黄胄指点,以及到中央美院和美院附中那浓厚的习画氛围熏陶后,画技都有提高。刘源在11岁那年,参加巴黎国际儿童画展,竟拿了个金奖,还在其他比赛中得过两次三等奖。 中共中央在庐山第二次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刘源也跟着父亲上了山。在山上,他画了幅画送给毛泽东,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元元。毛泽东看了署名,半诙谐半认真地说:“这个名字不好,不要圆,要有棱角嘛!”刘源赶忙解释:“不是那个圆滑的圆,是源泉的源。”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源泉的源么,那挺好!”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4节 刘少奇偏爱“真”字
庐山和毛泽东的对话,使刘源开始琢磨起自己的名字,渐渐感到不太满意了。中南海的孩子,都叫他源源。他觉得这是小孩子的名字,将来长大了,人家还“源源”“源源”地叫,多难为情。 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请求。父亲被说动了,真的思考了一番,随后和刘源做了一番交谈。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讲,这番话的内容似乎有点过于严肃和深奥了。 刘少奇说: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遇事不应简单视之,要加以鉴别,求是求真;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要人云亦云,要勇于坚持真理。母亲王光美谈话时也在场,她记录下刘少奇的话,从“求真”、“坚真”、“持真”几个意思中,联想到“鉴真”一词,并准备以此做儿子的名字。 然而没过太久,在首都的文化、宗教界举行了一次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活动提醒了王光美,“鉴真”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和尚同名,她又觉得儿子的名字这样改不太合适。改名之事被搁置了下来,但父亲那谆谆教诲,却烙在刘源的心里。 通过起名字对孩子进行教育,在刘家还发生过一次。 有一段时间,刘少奇发现丁丁做事松懈而漫不经心,学习不刻苦也不认真。他把丁丁叫进自己的办公室,在指出他的弱点和缺点后,告诉丁丁,自己为他想了个学名“允真”。他对丁丁说:“爸爸希望你以后能改正自己的缺点,无论干什么事都要努力认真。” 丁丁在起用学名刘允真后,常常想着父亲的殷切希望,做什么事都比以前更认真和投入了。从给丁丁起名“允真”,源源起名“鉴真”看,刘少奇对“真”字还真有点偏爱。 在刘源等几个孩子的记忆里,爸爸妈妈不单单自己对子女要求严格,还说服其他和子女相关的人,不可对他们搞特殊和过于宽宥。 1959年5月10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家里,接待了平平和源源就读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陶淑范、褚连山等老师。 在认真询问了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刘少奇说:“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们的学生,有句老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希望能严格要求他们,你们不严,我就不高兴。”“那次老师来,爸爸妈妈跟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事情已经过去近50年了,刘源还记得。 刘允真考高中那年,成绩不理想落榜了,因此情绪低落。有的人想用刘少奇的名义,去学校为他讲情。刘少奇知道后,专门为此事召开了有工作人员参加的家庭会议。 “我的孩子们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让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照顾。现在考不上学校,想打我的旗号,好像高干子女上了初中就一定要上高中,上了高中就一定要上大学,而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参加工作就一定要当干部,而不管有没有那个能力!” 讲到这里,刘少奇面露微愠:“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高干子弟就不能当工人、当农民、当解放军战士?我再次声明,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刘允真最终没有靠父亲的关系上北京的名牌高中,继而上什么名牌大学。而是根据考试成绩,进了北京郊区的一所寄宿制的半工半读农技学校。 临去学校前,丁丁向父亲告别。在自家孩子眼里一贯神色严肃的父亲温和地对他说:“我支持你学点技术,但一定要刻苦努力。否则一事无成,到时候就谁也帮不了你喽。”
第八部分 刘少奇住得最久的寓所第55节 中苏交恶,儿子遭殃
1960年,刘少奇的二儿子刘允若,从苏联回国。 在苏联,刘允若最初读的是工学院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后来,他感觉这同他的兴趣不甚一致,而且和几个同学的关系也相处得不太融洽,以致心情不是很舒畅,就想转学转系转专业,改学文学或新闻。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中国驻苏联使馆留学生管理处提出后,留学生管理处不同意,就给他做说服工作。但刘允若想不通,又给父亲写信,想从父亲那里得到支持。 对这种遇到一些挫折就言退却和变换的意念,刘少奇很不赞同。他回信说:你转系的理由不充分,我支持留学生管理处的意见。刘允若思想仍转不过弯,导致在一段时间里情绪低落,学习成绩下降。 刘少奇闻知此讯,感到儿子的行为简直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写信切责说:你过去虽然受过一些苦,但也染上了一些坏习气。眼下的所作所为,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 对此,刘允若并不以为然,不就是想让父亲说两句话帮自己转系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对父亲接二连三且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刘允若产生了逆反心理,觉得像父亲这种搞政治的人,简直有点太铁面无情了。 直到隔了一段时间,他逐渐冷静下来后,才觉得父亲讲的道理是对的。最后,他还是服从了父亲的意见,继续在理工科学习,只是专业转为导弹的总体设计。 就是在苏联留学的期间,刘允若与一位叫丽达的苏联姑娘相识而坠入爱河。而他们的恋情,偏偏是伴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矛盾和敌对与日俱炽。 1960年4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赫鲁晓夫的理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