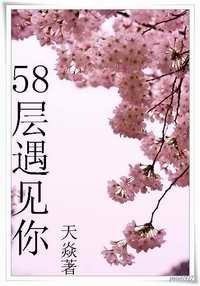580-红墙童话-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也发起捐献一架“红领巾号”的活动。育英小学的红领巾们很想为此出一分力,但他们都出自实行供给制的家庭,自己的衣食也是由国家供给的,拿不出多少钱,因此很着急。 当时育英小学正在拆除危旧房,盖新房,那是日本人盖的,都是木头房子,所以拆下的木料成堆。孩子们见木料上有许多铁钉、扒钉,顿时有了想法:把钉子从木料上起下来,当废铁卖了钱,不就有得可捐了吗。 他们各显其能,寻找各种各样的工具,把深深在木料中的钉子,连拔带抠地弄出来。每弄出一颗,“就像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粒子弹那么高兴。”金戈回忆说:“当年的劲头可大了,一有空就去拔。哎呦,那时可没少拔,一天差不多能拔三四斤废钉子。拔完后交给老师,卖了钱捐献。”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0节 中南海的孩子都会游泳
在中南海的孩子们的记忆中,育英小学是很重视学生体魄的锻炼的。学校里建了一座相当宽敞的运动室,各种健身设施完备。遇到刮风下雨,体育课就可以在室内上,丝毫不受气候变幻的干扰。 冬季,学校的老师带领孩子们,在校园的一隅,靠自己端水,泼出了一块人工滑冰场。学校购买了一批冰鞋,教孩子们滑冰。中南海的孩子有点得天独厚的便利,守着中南海这个冬季天然冰场,回家滑得更痛快。 中海最初没有开辟滑冰场,只是在南海的东八所一带,圈了一个场子。那时滑冰运动还很不普及,所以冰场上见不到几个大人,在冰上欢腾雀跃的,都是孩子们。有一张毛泽东看着李敏等换冰鞋滑冰的照片,就是在这个滑冰场拍的。 张纪宇说他在学校学了滑冰后,勾起了很大的瘾头,缠着母亲买了一双冰鞋。“毛远新回中南海滑冰,起初没有冰鞋,都是跑来跟我借。我们两个挺熟的,最初的相识也不是到育英小学以后。1949年底1950年初,我随妈妈到江西了一段时间,就是在那儿认识了住在江西省副主席方志纯家的毛远新。后来到育英上学,听说他也在,他是我初到育英时惟一认识的人。” 毛远新实际上是育英小学初创时的学生。1949年,他的母亲朱旦华(毛远新父亲毛泽民已牺牲6年)和方志纯结婚后,他随母亲和继父去了江西,所以离开了育英一段时间。 1951年,毛远新又回到北京,先是住在朱德家里。从1952年起住进了菊香书屋,和伯父毛泽东一起生活。在育英小学的履历表上,毛远新家长一栏里填的是江青的名字。在育英读书期间,他的表现应该说是相当优秀的,担任过小队长、中队委和大队主席。这些,都可以从他的履历上查到。 如今的中国,在国际上有“自行车王国”之称。而在50年代初,自行车别说在大众眼里,即便在高级干部家中,也属稀罕物。孩子们回忆时比喻说:“那时买辆自行车,就相当于如今买辆轿车。” 育英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家中没有自行车。把自行车骑到学校的,大家只记得一个人,萧立昂。他的父亲萧三,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老乡、《国际歌》中文歌词翻译之一,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几个参加过列宁葬礼、并为之扶灵的人。 有时,萧立昂骑自行车上学。一次,他在校园里骑车骑得飞快,结果撞到了篮球架子上,把车大梁都撞弯了。尽管如此,大家都觉得他骑车很神气,引起了学骑车的兴致。 第二个有自行车的,是在国外当大使的黄镇的女儿。因为育英小学里把自行车骑进校门的,就这么两三位,所以大家都记得他们。 不知是出自谁的提议,或许是校方体察了学生们的欲望,大约在1952年前后,学校出资购买了20辆自行车,是比大人骑的自行车略小一些的轻便自行车。学校里随即多了一项业余运动,骑自行车。中南海里的许多孩子,就是在育英学校学会了骑自行车。当学生学会骑车后,老师还利用节假日,带留校的孩子们骑车远足,作为一种锻炼。 张纪宇还能记起一次参加学校组织的“远征”:“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没有回家,跟着老师骑车去了紫竹院。那时的紫竹院只是个地名,还没有如今的园子,有水洼,里面尽是蛤蟆骨朵儿。” 中南海中年纪大些的孩子,大多体魄强健,这应该归功于育英小学的重视体育锻炼;当然,这和中南海里有天然的锻炼场所,有锻炼的便利条件,也沾点因果关系。最起码中南海的孩子都会游泳。如果哪个自称是中南海的孩子又说自己不会游泳,那他肯定是在说谎,大可将之排除在中南海的孩子之外。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1节 享受领袖的关怀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2节 毛主席逗弄杨尚昆的儿子
也许,对孩子来说,中南海的环境太好了,偌大一个可以游戏折腾的园子,到处都可以感到关爱的气息,所以孩子们都特依恋这里。平时,盼着星期六的下午早早到来;星期天的黄昏,总是不情愿地登上返回育英小学的班车。 徐肖冰、侯波之子徐建林回忆说:“妈妈动员我们回学校可是费了劲了,好说歹说都不见效,最后只好给我们塞点吃的,哄我们走。那时是供给制,也没有什么高级东西,或者是个苹果,或者两块饼干、一块糖。这些东西自己还不能独自享受,到学校全要交给老师,统一分给所有的孩子共享。自己得到的份额肯定是比原来少了,但消除了那种有人有、有人无的现象。”平等、友爱和互助的精神,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浸润于孩子们稚嫩的心灵。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进入中南海也就半年左右,中南海内的环境已经整治得大有改观。南海海底的淤泥,据说清出了16万立方米。沿海边用石块砌起了护岸,杂草和垃圾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伍绍祖回忆中老延安们在中南海里养的鸭子,绝迹了。金戈初进中南海时那空气污浊,蚊蝇孳生的感觉,也大有改观。中南海的水,变得清澈;中南海的空气,变得透明。 星期六,孩子们一回到中南海,就可以在瀛台、静谷的假山、奇石、古树间捉迷藏;晚饭后,可以在新砌的小码头解缆划船;再晚些,可以到春耦斋等着放电影。 星期天,同班和同年级已经熟悉的朋友,可以互相串串门。张纪宇和杨小二、毛远新是同年级的同学,关系也比较好,有时就应他们之邀,到他们家里去玩。 “我们家和菊香书屋挨得很近。当时我还是小学生,头脑里也没太多的禁忌。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歌唱得很熟,但那时的感觉是大救星是非常亲近的人,而不是要敬畏十分的神,见领袖就见领袖,挺平常的,心理上从没有要郑重其事的准备。有时应邀,有时想找毛远新,就奔菊香书屋而去。”张纪宇的话就像他的人一样朴素直白。 毛远新住处给张纪宇的印象,是书比较多。到他那里玩,多半是窝在房间里看一阵子书。“还能记忆得起的是在那里看过一位著名德国漫画家的漫画系列,可这位漫画家的名字现在怎么也叫不上来了。再有就是一些鬼怪的故事,看得毛骨悚然,不看又忍不住要翻翻。” “在毛泽东的院子里也很随便,我爬过院子里的树,还摘过菊香书屋院落里的梨吃。有一次我爬到树上,卫士让我下来,我就不下来。他们也没办法,也不能大声训斥,怕惊动了毛主席。” 也许是因为他母亲是负责中共领袖的保健的,和领袖的关系比较近,张纪宇还有印象和毛泽东及一组的人一起吃过饭,坐过毛泽东划的船。 “毛主席对孩子很随和,见面总喜欢逗几句。他跟我说过什么我倒记不得了,但有一次我和杨小二一块儿遇到他,他逗杨小二说:‘你叫杨小二。你为什么叫杨小二,不叫杨小三啊?’杨小二当时怎么回答的,我也忘了。” 这是在平时的周末、周日,孩子们玩一玩、闹一闹,对大人工作的影响不太大。但在寒暑假,孩子们玩耍吵闹得太厉害,就要影响大人的工作了。因此逢寒暑假,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会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做假期的辅导员,组织管理孩子们。 “组织起来”、“依靠组织”,是那个年代的格言隽语,孩子们也不例外,当假期离开了学校的组织,就组成了中南海临时小队的组织。临时小队长由假期辅导员指定,并像在学校一样,定期过队日。徐建林记得有一个假期,是李敏当小队长。张纪宇则记得他被“荣幸”地指定为管男生的副队长那次,队长是李讷。 队日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参观警卫部队的内务;到机关图书馆搞卫生,粘补破损的图书;甚至去中南海外面的居民区,帮助烈军属扫院子、抬水、擦玻璃。在暑假期间,还组织孩子们在中南海里游泳。 大多数孩子还都记得,去玉泉山或西山农场劳动的情景。那里有果园,还有奶牛场,负责中央的水果和牛奶等食品的供应。其实组织者的出发点是让孩子们不要断了和劳动的联系,不要忘记劳动人民,并不在于孩子们真能顶个劳动力,要完成多少劳动量,多数时候就是锄锄草。 到农场还是很让孩子们开眼界的。康辉回忆说:“农场的设备很先进,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其他地方还不可能有的捆草机械,就是当时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能把散乱的草打成规矩的正方形草块。特别新奇的是在奶牛场看见奶牛,都是进口的种,特别大,初看吓一跳。喂养奶牛和挤奶的机械设备也是进口的,最先进的。青饲料先经过粉碎,加拌大豆,然后喷在外面的一个大池子里,封起来,发酵一段时间再用来喂牛。我们就是在这里,比较早地领略了农业机械化。” 让孩子们难忘的,是“日理千机”的杨尚昆、胡乔木等父辈,也曾挤出时间,参加中南海小队极其“小儿科”的活动。 有一个星期天,杨尚昆和中南海小队一起去了钓鱼台。那时的钓鱼台,一点没有今天公园的轮廓,除了一些破损的古迹,只有一个个丛林繁茂,浓荫蔽日、鸟啭啾啾的小丘。孩子们在此煞有介事地玩着“抢红旗”的军事游戏;采集树叶、捕捉蝴蝶,以便回去做标本…… 中午,杨尚昆拿出他早就准备好的美国军用罐头,请孩子们野餐。性格开朗的杨尚昆笑着说:“这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从美国运来的,是我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你们尝尝,好吃不好吃?” 有杨尚昆的诙谐,有罐头佳肴,孩子们大快朵颐,开心无比。金戈的弟弟金矛很认真地说:“等我长大了,也要到朝鲜打美国鬼子,给你们缴获更多的罐头。”引起一阵哄笑。 孩子的稚气和可爱,也让杨尚昆心情爽朗,他拍了拍金矛的大脑袋说:“傻孩子,志愿军还能让美国鬼子在朝鲜活到那一天?” 停顿有顷,他又语重心长地说:“等你们长大,就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让全国的娃娃们都能吃上面包、牛奶和罐头,吃上我们自己生产的面包和罐头。只要我们的国家富起来,强大起来,什么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再也不要想来欺侮我们!你们说,对不对?” 孩子们听着,都瞪着大眼睛,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第六部分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第33节 “蒋介石把斯大林气死了”
一直在感受着欢乐的孩子们,在1953年春季才第一次感受新中国成立后的悲悯。那年的3月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了。消息向中国大众播报时,已经是3月6日。 张纪宇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风卷着尘沙的上午,他们正在校园劳动。学校突然通知,所有的人都回教室听广播。回到教室后,喇叭里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讣告,中共中央决定从3月7日到9日,志哀三天。 受建国初期一边倒的政治选择的影响,中苏友谊的强化宣传,斯大林被树立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形象,其威望甚至高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们的心灵,经父辈的一再灌输,盛满了对斯大林的感情。听闻噩耗,孩子们哭得昏天黑地,整个学校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徐建林回忆说:“孩子的感情是最真挚的。我们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是张鼎丞的儿子,他哭得可伤心了。还有一个孩子,一边哭,一边骂美帝国主义,骂各国反动派,骂国民党蒋介石,说是他们作恶多端,把斯大林气死了。” 孩子们的悲痛里,大概还隐含着一重社会主义阵营的统帅去世了,谁将领导我们前进的忧虑。尽管他们还都很小,但这是那个时代背景下,这种体制的国度的人们的思维定式。 每临领袖年事已高,或有了天不假年的预兆,就开始了接班的未雨绸缪;或领袖真的撒手人寰,谁是接班人像正等待打开的黑匣子,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要有一种惴惴不安。不光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就连另一个阵营的政治家们,也会感到焦灼。蒙哥马利跑到中国,一再提出要见毛泽东,见面后又一个劲儿地刨根问底谁将是他的接班人,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那次,全校的孩子都和大人一样,带黑纱,参加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两年后,我们育英小学内,又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悼念活动。”吴陕立最先向笔者忆起这件事:“那就是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在我们学校上学的钟筱兰、钟延辉的爸爸钟步云牺牲了。” 1955年春,亚洲非洲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万隆召开,中国政府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4月11日,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凤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11人,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客机,从香港机场起飞先期赴万隆。 该机飞行近5小时后,在北婆罗洲沙捞月西北海面上空突然爆炸,右翼起火。机务人员企图在海上迫降失败,飞机在撞击水面瞬间破裂,除3名机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