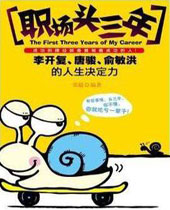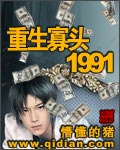怀旧的舌头-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比较相信关于“感官互动”的理论,这是我从小验证过的,比如边吃边看。具体表现就是有了一本好书时,我就特别想找些磨牙的瓜子、花生之类伴读;反之,有了好吃的小零食,我又急于找本想读的好书来佐餐,那时可读的书少,所以又促成了我为了享受美食把一本书反复读的好习惯。在这一过程中,味觉享受和视觉审美浑然天成,二者互相促进,缺一不可。那时还是70年代,没有今天这么多讲究的餐厅和酒吧,但是那时我的房间里就常常已经把吃的和看的混放在一起,摆出一付物质精神两手都要抓的姿势,一如今天酒吧咖啡厅里随处摆放的时尚杂志阅览架。
吃和看的互动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后来这个习惯与时俱进又有了极大的发展。发展趋势是和时代同步,就是书读的少了,碟看得多了。先是一些惊险刺激的大片,天天看得昏天黑地,后来看多了就发觉都是一个模式一个套路,看到结尾感觉像是中了导演圈套;以后又改看那些地下电影,就是特平淡又特深沉,节奏巨慢,看完之后几天都不想说话的那种。我烟酒不沾,所以这期间我依然不改边看边吃的习惯,看大片的时候我喜欢嚼脆脆的薯片,配上一杯冰可乐或者冰咖啡,可以起到压惊安神之功效;而看地下电影,最好是果丹皮鲜姜片一类,可以提神醒脑,不至于窝在沙发里沉沉睡去。
再后来,我就迷恋上了老电影。
我说的这些老电影都是二十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拍摄的,广州有个俏佳人文化公司专门出品这类老电影,特别齐全,我是他们的金牌会员,已经积攒了200多部。老电影的最大优点是不费脑子,特别放松。因为那是个意识形态高度强化的年代,角色都是脸谱化的,左中右敌我友一目了然,主人公都是信仰特坚定,爱憎特分明,浓眉大眼一脸正气;反面人物都是特阴险特狡猾,总揣着颗梦想变天复辟的黑心。但是你不用担心,最后结尾一定是乌云驱散阳光明媚,革命群众扬眉吐气阶级敌人垂头丧气。在当今每天疲于奔命,压力巨大又一事无成的日子里,看看这些老电影,有一种缓解紧张和心理平衡后的极大满足。而且我发觉看老电影时最好的配餐是老玉米,特别是那些大量拍摄于60、70年代反映农业合作化题材的电影,啃着老玉米欣赏就很容易达到一种情景交融的境地。
我相信“吃在吃外”,“味道在吃外”或者说的再悬点就是“境界在吃外”。如今有谁去餐厅还单单是为了充饥呢?现在餐厅里的家具摆设,服务小姐的服饰做派,餐具样式和墙上挂件,乃至灯光的明暗和背景音乐的曲子这些统统都比端到你面前的那盘菜更重要也更卖钱。回到老玉米和老电影这档子事,这个吃老玉米的隐喻性就一目了然了。我分析其实就是我内心深处企图用农业文明的简朴和单纯来抵御信息时代的嘈杂喧嚣,用昔日乌托邦式的坚定信念和方向感来抚慰今天的空虚和迷茫,再或者说,干脆就是一种既想享受现代化生活的高质量,又想保存古老审美情趣的精神分裂症状。
就这样,在某个燥热得让人懒洋洋的周末下午,我蒸好一锅热气腾腾的老玉米,拉上厚厚的双层窗帘,把空调冷气开足,再取出一张《艳阳天》的影碟放进机器,这时满屋玉米的香气扑鼻,巨大的液晶屏幕上村支书萧长春和饲养员马老四正在农业社的牲口棚里亲亲热热地唠着家常,“长春啊,四爷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此情此景,是多么的蒙太奇超写实后现代啊!
第一部分大仙:往事立马如烟 (图)
一度,我在“京客隆”超市买点儿“天福号”茶肠,在楼下小卖部拎回四瓶“燕京”,午夜写稿码字的时候,用平民化的喝酒习惯,蒙出几句贵族的文字来。后来弄清了,这“天福号”是北京的老字号,1738年就有了,在乾隆三年就开了张。看来多世俗的东西也有历史感,我就觉得“天福号”茶肠比“培根”鸡尾肠更适合中华民族的口味。 我这人对老字号的感情不是很深,不管是“老字号”还是“新字号”,只要能让我们爱好,只要人们能好上这一口,就会成为它们的常客。北京的老字号有很多,历史都挺悠久,有着脍炙人口的传奇色彩和代代相传的文化背景。但我对此很少涉猎,只管去吃,二十多年前,我吃过一些“老字号”或者“半老字号”,如今回想起来,往事立马如烟。 1979年,我20岁生日时,跟一发儿小去了“翠华楼”,点了一桌子菜,最后结帐才十块钱。虽然我当时在798厂当临时工一天才挣1块钱,一个月也就30块钱,但我这人生第一撮还算豪放,惟一美中不足的是,被一个叫“赛螃蟹”的菜给晕了一道,至今还耿耿于怀。“赛螃蟹”不就是“摊鸡蛋”吗,凭什么要误导人家消费者?也搭上我那时还比较农民,没怎么接触过螃蟹,要是比较渔民的化,绝对不会被“赛螃蟹”给蒙了。天蝎座的人比较记仇,后来我连螃蟹和鸡蛋都比较反感,很少让它们上桌,我老觉得是螃蟹和鸡蛋串通好了,给我这个第一次下馆子的主儿下了一套。 不过,头一次撮饭的感觉真爽,在“翠华楼”撮得肚歪,打着“北京白牌”的酒嗝,一路溜达到大华电影院,看了罗马尼亚电影《爆炸》。与其说是看了电影,不如说是“睡了”电影,在“北京白牌”啤酒的酒意中,我跟发儿小都着了,连油轮巨大的爆炸声都没把我们惊醒。 “处女撮”之后,我觉得外面的菜真比家里的菜好吃,好上这口了,便没完没了,经常约着发儿小和同事,于北京街头暴撮海喝。那时年轻,又能吃又能喝,越能喝就越能吃,刚刚自己挣了钱,立马就陷进肉山酒海不能自拔。交道口的“康乐餐厅”、鼓楼的“马凯餐厅”、东四的“青海餐厅”、正义路的“花竹餐厅”、前门的“力力餐厅”、东风市场(现叫东安市场)的“湘蜀餐厅”,这些馆子老去。 记得有一次就餐高峰时,跟几个哥们在“湘蜀餐厅”等座,那一桌是两拨人,一拨俩小伙子,嘎蹦利落脆,喝完酒扒拉完饭就撤,可那一拨一男一女像是一对,吃着聊着腻着,卿卿我我没完。我们哥四个索性要了八升啤酒,往桌上一礅,齐吼一声:“走着!”我们哥四个各举一升,一扬脖,见底儿,净!那对男女一看这架势,没心情了,呆不住了,麻利儿就撤。女的临走还说了一声:“瞧这帮人,真讨厌!”我跟了一句:“有话回家说去,别耽误我们吃饭。”我心想,你们两样全饱了,我们一样还没着落呢。还有一次在“康乐餐厅”等座,那时候点菜得到前台点,菜好了还得到前台取,经常是一边等座一边排队取菜。我的哥们排队买酒等菜,我负责占座,我坐着一个凳子,左右脚各搭着一个凳子,这工夫有人在我身后喊:“师傅,是你钱掉了吗?”我回头看地上真有两分钱,我心想两分钱也值得捡?趁我回头的工夫,脚没搭住一个凳子,被别人飞快顺走了。 涮羊肉刚兴的那段儿,我常去“东来顺”,因为我住东边,所以我特喜欢这个店名。撮“东来顺”有个讲究,这里的羊肉巨新鲜,所以上来要生吃三片,最后我发展到生吃五六片,后来敢生着吃生猛海鲜,就是那时候打的底子。我这人特爱吃醋,极不爱吃芝麻酱,所以在涮肉的时候不爱要料,就一碗醋加点儿辣椒油,吃嘛儿嘛儿香,“东来顺”的服务员还以为我瞧不起他们的作料呢,没少给我白眼。有一次涮完锅子,口巨渴,便来到东风市场冷饮店,狂喝圆肚瓷瓶装的酸奶。卖酸奶的姑娘看我连喝三瓶还要,就说:“大冷的天,你不怕拉稀呀?”我说:“胃好着呢,天越冷我越能吃凉的。”姑娘说:“你喝十瓶我看看,我跟你打赌,输了给你买包烟。”这不正撞我强项上吗?我一鼓作气直奔八瓶,姑娘拦住我:“我服了,来,输你一包‘翡翠’。” 后来好上了西餐这口儿,谈恋爱的时候充当冤大头,把对象往西餐厅领。1985年,跟一个798厂的女工在实验剧场看完《牧马人》,就近到“大地西餐厅”来点儿洋的。当时我身上只带着13块钱,点了四菜两汤外加面包正好在12块9毛8的关头打住。当时,我穿着“大地牌”风衣,所以要撮“大地西餐厅”,给女工背了一首北岛关于大地的诗:“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殉难者圣洁的姓名。”年轻女工正用叉子叨着酸黄瓜,突然下意识地用眼睫毛蹭了蹭餐桌上的假花。 1987年,跟报社的一个女孩谈恋爱,吵完架跟她去“三宝乐”吃饭,我一赌气拿起菜单扫了一眼,就跟服务员说:“从55到65,”然后把60元往桌上一扔。服务员说:“从55到65共11个菜,58元。”我说:“没错,你点点。”
第一部分朱大可:我的吃喝白皮书 (图)
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1957年一个冬日的正午,越过凛冽的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允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 我不知道奶妈的长相。她乳房的形状和气息超越了我的记忆,成为一个不可索解的谜团。她在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因肺病离去,而我则开始了吃“奶糕”的漫长历程,它是牛奶、面粉和蔗糖的混合物。我在奶糕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直到今天我还能记住它的气味,那种浓郁的香气,一直融入了我的骨头。十几年后,我在商店里购买了这种食物,企图重温周岁时的蜜月,但它的气味却与记忆相距遥远。这场失败的“怀旧”实验,解构了我对食物的童贞信念。 我7岁前的食谱是被大饥荒年代所限定的。我们全家骨瘦如柴(有照片为证),靠面疙瘩汤度日,那种食物是令人作呕的。在炎热的夏天,我和隔壁邻居的小孩——一对姐弟在家门口坐共进午餐。我坐在小板凳上,从小碗里扒着难咽的面团和菜叶,眼里噙着失望的眼泪。唯一支撑我进食的信念是坐在对面的女孩,她的秀丽容颜就是佐餐的美味佳肴,也是我熬过大饥荒年代的最高慰藉。我们芦柴棒似的小手紧密地缠在一起。 对食物的期待横贯了整个童年。我上小学以后,大饥荒年代缓慢地拉上了帷幕,商店的货架上开始出现那些曾经稀缺的食品。父亲远在浦东工作,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的黄昏是一个细小美妙的节日。每次父亲都会从他手袋里取出搪瓷杯,里面是期待已久的四个锅贴,有时则是两个热气腾腾的重油豆干菜包。这是童年的美食节,它每周降临在我生命里,向我打开世界美妙的大门。我小心翼翼地咬开锅贴的表皮,用舌尖轻舔着香气四溢的肉馅,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我的感官瘫痪在了粗砺的食物面前。食物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伟大友谊的纽带。 不久父亲因生肝炎而病休在家。为了治疗,他开始了凶猛的进补。而我则在一边助吃。他的冰糖炖蹄膀成了我最喜爱的点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燕窝,为剔除混杂在胶状物里的羽毛,我和父亲分别用拔毛钳清理了整整两天,我至今都能记住它半透明的果冻似的形态。还有一次,母亲搞来了一副不知什么动物的睾丸,烧熟后呈现为酱红色,父亲把它切成薄片,坐在餐桌前慢慢嚼着,表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在一边观看,发出大惊小怪的声音。这是短暂而富足的时光,但它仅仅延续了三年之久,就被1966年的文革烈焰所焚毁。 食物匮乏的年代重新返回了大地,变得更加悲苦起来。全国进入军事化管理,所有一切都需要限制性配给。古怪的票证出现了,从糖、猪肉、食用油、豆制品到肥皂和草纸,所有日常食物和用品都被打上定量供应的标签。虽然粮食并不缺乏,但却都是发霉变质的陈米,淘洗时,水会因米里的大量霉菌而染成绿色。每户一个月只有一斤猪肉和半斤豆油,必须极其俭省地加以规划。家庭主妇的智慧被紧急动员起来。她们要从极其有限的资源中,尽其可能地榨取生活的乐趣。 1971年,中苏边境发生大规模冲突,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父母开始紧急战备囤积,用积攒的票证采购了许多砂糖、盐、肥皂、草纸和火柴。这些东西后来却成了巨大的累赘。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把它们用完。那些细砂糖(俗称“绵白糖”)被分别盛放在几个大砂锅里,最后都长出了细长的虫子,噩梦般爬行在黑暗的壁橱里。 由于政府禁止农民私自养鸡和贩卖,吃鸡成了一种巨大的奢侈。有一次,父亲的农学院朋友从单位里搞来一只巴基斯坦引进种的公鸡。我们全家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之中。父亲亲自动手杀鸡和烹饪“客家葱油鸡”。他把鸡切成小块,烧熟后改为小火,用葱油不断浇淋,让葱香透入鸡肉深处。我从未品尝过如此鲜美的菜肴,连续好多天都在回味它的奇妙滋味。从此我坚持认为鸡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食物。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是我家唯一的盛宴,它怒放在清教主义革命的现场。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起来。我们形影相吊地行走在文革晚期的黑夜里。她提前退休,而我则在一家照相机厂里当了钳工。我们生活小康,无所欲求。母亲有时会带我去附近的乔家栅点心店,吃二毛五分钱一碗的鲜肉馄饨,店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顾客在这种高档食店里留连。而我们却在那里悠闲地小坐,望着大玻璃窗外的襄阳路风景,心情庄严得像个贵族。 文革结束后,国家食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我和密友“大头”经常出没于上海音乐厅,聆听交响乐团的演出,然后在再步行到淮海路上的一家饭店,叫上一客两面黄(一种在油里煎过的面条,上面浇淋着被切碎的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