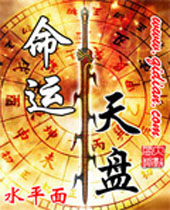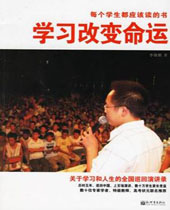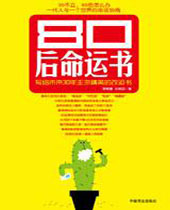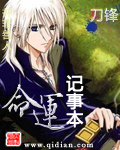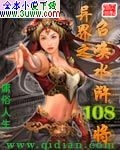104.命运的抉择-第34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士绅可谓是络绎不绝。最是头痛这种交际应酬的杨绍清巴不得能张双翅膀直接飞回南京去,好彻底摆脱地方官府举行的各类活动。因此在杨绍清等人从新安回来后的第二天,船队便扬帆起程离开了广州。而这一次为了躲避沿岸官府衙门的“骚扰”,杨绍清特地命令船队沿着海岸航行,和陆地始终保持十海里左右的距离。
不过沿海各省的官员们却并没有就此失去与船队的联系。事实上,正当船队以全速驶往上海之时,帝国的驿夫正骑着驿马从陆路奔驰。下一站的驿夫一听见前站驿夫到达的马铃声便立即跳上马,接过邮件。如此往复地将船队的航行情况及时向南京朝廷以及其他地方省份官府报告。这在中国官员们看来本是理所当然之事。可在随行的欧洲人眼中却成了一种奇迹。因为这在连年战乱通讯闭塞的欧洲大陆是难以想象了一种事情。显然就这一点上来看中国邮政远较欧洲邮政来得发达。
对此骄傲的欧洲人也有着一番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欧洲大陆拥有地中海,所以欧洲人选择了海洋;而中华帝国在陆上的疆域辽阔,所以中国人选择了陆地。它们在各自选择的领域里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当然这种解释很大程度上有自我安慰的味道。因为这一路东来随行的欧洲人可没少见识中国人庞大的海船和那些令人生畏的战舰。特别是在东印度群岛遇到的南洋舰队甚至让自负为海之子的英国人也叹为观止。不过中华帝国在水路运输上对欧洲人的真正的打击并不是来自海洋,而是来自于内陆深处的河运。
由于一路顺风,船队只花了8天时间便抵达了这次旅行最重要的停靠点吴淞港。航行至此,船上的欧洲人也算是彻底打消了他们先前对工作的顾虑。因为他们发现中华帝国的疆域远远超出了他们来之前的想象。这一路北上沿途漫长的海岸线几乎望不到尽头。据说这条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一路向北延伸直到世界最北端终年冰封的极地,形成一条漂亮的半弧形。从地图上来活像一把蓄势待发的弓,而架在这把弓上的箭矢就是帝国最大的河流——长江。这个形状据说给当时的随行的欧洲画师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在帝国殖民司会客厅的一处墙面上便赫然画有这样一副壁画,苍穹之下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战神张弓搭箭直指远处波涛汹涌的大海。而此刻船队正是要从吴淞口进入长江逆流而上直达帝国的心脏南京。由此中华帝国那错综复杂又非常广阔的内河航运网,便清晰地展现在了欧洲人面前。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无论是自然的河流,还是人工的运河,无不像血管一般汇入长江这条主动脉之中。沿着宽阔的江面从海上驶来的远洋商船将世界各地的原材料和商品运至长江沿岸的每一处重要港口。在那里货物会被散发到一艘艘体积娇小的帆船之上。这些帆船不但只吃水太浅,更无法抵御海上台风的袭击,但它们却能灵巧地穿梭于那些相对宽阔的长江细如毛发的大小河道之中,将货物运达内陆深处的目的地。同样的它们又将内地丰硕的物资和货品汇集到那些巨大的远洋商船上。由此帝国分布在东南地区的诸个工商业据点就被有效地串联在了一起。可以想象货物的转口为那些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并使许多生活用品的变得便宜起来。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运输体系。然而欧洲人却惊讶的发现,在中国人的经营之下整个系统运转得极其自然通畅。大到数百吨的远洋船,小到看上去随时可能被风刮沉的舢板,每一艘船都像工蜂一般忙碌而又准确地完成各自的任务。
对此来自号称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惠耿斯教授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中华帝国拥有着世界上最高效的运输邮政系统。在他看来,荷兰的效率来自法律的规范和对商业契约的严格执行。而中华帝国的效率则是源自于帝国臣民的优秀素质。这些中国人就像忙碌的蜂群一般守纪律,听指挥。因此中国的城市总给外来访客以一种大度安定的感觉。相比之下,这个时代欧洲的城市却是时常都处于骚乱的状态下。时不时地就能碰上衣衫褴缕的市民拿着棍棒举着烂番茄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暴动。如此状态下别说是效率了,连城市的正常运作都绝难作到。因此当时几乎每一座欧洲城市都会有相应的民兵组织随时准备镇压可能发生的动乱。
关于欧洲市镇的暴动问题,来自意大利半岛的博雷利教授感触就更深了。在过去的百年当中意大利半岛城邦中的暴乱和内讧就从未停歇过。而今在中华帝国巡游一番之后,他认为一个国家风气的好坏、民众道德操守的高低取决于这个国家民众所受到待遇的优劣。也就是说当政府的服务让民众觉得满足之时,民众自然而然就不会冒着可能触犯国家暴力机构的风险来破坏其现有的安定生活。反之一味地抱怨民众的素质地下,而不改善相应的公共措施,则难以让民众在低质量的生活条件下做到道德高尚。而在这一点上中华帝国显然做得很到位,从沿途繁荣安定的景象看来,这里确实比欧洲更适合居住。而从那些素不相识的中国平民眼中,博雷利等人也看到了一种在欧洲市民眼中绝难瞧见的安逸与满足。一方肯尽责,一方易满足。两相配合之下,才造就眼前这个安静祥和的国度。反观欧洲无论是君主、政府还是民众的表现都差强人意。
有了如此众多的种种对比之后,就算是最固执的欧洲人,现在也放弃了再在心中与中国人较劲的想法。并在接下来的旅途中老老实实地像个乡巴佬一样,到处好奇地东张西望起来。不过乡巴佬有时也会发一些不大不小的感慨。正如对于一个来自从房屋建筑都是哥特式和巴罗克式的城市来的人来说,中国城市的似乎少了点美感。因此在欧洲人眼中那些成千上万矮小呈弓形排在一条直线上呈直角交叉的房屋让人联想起一排排的营房。
当然相关的这些评论,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少在胡克等人的眼中,长江两岸富饶的田野、矗立在山丘顶上的宝塔、时而在堤坝上穿行而的过了人力车,以及那些河道深处用桩基架在水面上水上人家,诸如此类的异域风光都极富诗情画意。让早年学过绘画的他忍不住拿起画笔将这一路的所见所闻都描绘在了画纸之上。这一日晚餐过后,乘着天色尚亮,胡克又坐在船头开始描摹起岸边的市井风光来。引得一旁正在甲板上散步的杨绍清不由上前驻足赞叹道:“胡克先生画得可真逼真啊!”
“啊,殿下您好。”发现站在自己身后的是亲王殿下,胡克赶忙起身行礼道。在这个时代无论在哪儿一个国家,皇族在普通人的心目中都是高高在上的等级。这一点就算是在砍了国王脑袋的英国也是一样。
眼见打扰了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创作,杨绍清便觉得愧疚起来。却见他饱含歉意地开口道:“对不起,我一时激动打扰你作画了。胡克先生你还是坐在那儿继续画吧。我就不打扰你创作了。”
“殿下这没什么的。我只是在画速写习作罢了。座在这儿边画边与人聊天感觉也不错呀。要说创作的话。貔貅号上的伦勃朗先生才是真正的大画家呢。”胡克爽朗的一笑道。
“哦?伦勃朗先生也在画这运河风光?”杨绍清好奇的问道。其实早在他出发去欧洲之前,伦勃朗大名对杨绍清来说就已经是如雷贯耳了。孙露曾不止一次在他面前提起过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荷兰画家,以及他那副在后世价值连城的《夜巡》。为此,杨绍清还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呢。
原来《夜巡》并不是画的本名。这画本是1642年,由荷兰班宁柯克连长和他手下民兵共16个人每人出了100盾请伦勃朗画一幅集体像。谁知伦勃朗没有像当时流行的那样把16个人都摆放在宴会桌前,画出一幅呆板的画像,而是自己设计了一个场景,仿佛16个人接到了出巡的命令,各自不同的在做着准备。这幅画采用强烈的明暗对比画法,用光线塑造形体,画面层次丰富,富有戏剧性。从任何地方来看,都是一幅绝对的杰作。但是大老粗的民兵们可不干,大家都是出了100盾,为什么人家在画中那么明显,而自己却要隐身在后面呢。民兵们要求重新画一幅肖像。可是出于一个画家的艺术感出于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和创作方法,伦勃朗坚持不重新画一幅。结果民兵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伦勃朗最终败诉破产,妻子也在那一年骤然逝世。双重打击下伦勃朗离开了阿姆斯特丹隐居乡野。直到有一天一群来自东方的神秘来客扣响了他家的大门。他们不仅为他偿还了所有欠债,还出资将那副还未被兵营的煤灰熏成黑夜的“夜巡”给赎了回来。对此伦勃朗当然是感激不尽。因此用不着杨绍清多废唇舌,这位荷兰画派的灵魂级人物便收拾铺盖上了船。
见杨绍清一副兴致勃勃的模样,胡克当即也来了精神。却见他把头一扬,满脸仰慕的说道:“是啊,伦勃朗先生正在筹划创作一套描绘长江沿岸风景的油画。为此他还特地让船上的中国水手带他去参观岸上的市集呢。伦勃朗先生真是个奇怪的画家。别的画家都在讨论如何为女皇画肖像。他却喜欢画那些市井平民。殿下你说女皇陛下会喜欢他的画吗?”
面对胡克的追问,杨绍清略微想了一下后,欣然回答道:“胡克先生,你知道吗,在中国有一副国宝叫《清明上河图》,它真实地描绘了数百年前大宋王朝的国都的壮观景象。如果有人能将我中华朝此刻盛景也如此保留下来的话,女皇一定很高兴能收到这样一份礼物。”
第二部 96 行大礼中西产分歧 取西经使团得正果
弘武五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日,公元1654年9月6日,随着风尘仆仆的张骞号缓缓驶入帝都南京,这场漫长艰辛的远洋之旅就此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掐指算来离张骞号上次出现在南京刚好满五年零两个月。不过这并不代表中西文明间的接触就此停歇。正如当年张骞出使西域那般,一次伟大旅程的结束往往意味着另一场更为伟大的旅程的开始。而对于17世纪的中西文明来说更是如此。如果说访欧使团曾经让尚处萌芽状态的欧洲社会惊羡不已。那使团从欧洲带来的欧洲学者和技师给古老的中华文明所带来的冲击则更为深远。以至于后世的不少学者在提到弘武五年之时,脑中头一个反映出的大事件就是访欧使团的回国。因为打从这群老外来到南京城的第一天起,中西两股文化间的较量便就此拉开了序幕。而作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年轻的约翰&;#8226;胡克则以一种猎奇似的笔锋记录下了两股文明的首次撞击:
“我从没有见过这么盛大的欢迎仪式。码头的四周围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远处更有无数的男人和妇女聚集在自家的窗口看着我们。比起热情如火的广州人来,这里的居民显然要拘谨得多,也严肃得多。这也难怪,毕竟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强盛帝国的都城之中。不过首都欢迎仪式的排场显然要比广州的喧闹、多彩、豪华得多。锣声、钹声和喇叭声响彻云霄,各式各样的楼台亭阁用绸带和丝质帷幔装点得格外漂亮。码头上的官员都穿着色彩鲜艳的丝绸长袍,胸前还有绣有金色圆形的精美纹饰。据说中国官员学者的身份是与长袍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野蛮人或低践的苦力才会穿短衣。为了更符合中国人的打扮,教授他们都换上了大学博士专有的那种深红色绸长袍。我也套了一件牛津大学的学生长袍,虽然宽大而飘逸,可这里的天气太炎热了,穿着很不舒服。不过总比其他穿紧身外衣、套裤和长袜的欧洲人来得好。这些东方人虽然已经熟悉了欧洲人的穿戴,可在中国戏中,只有鬼怪才穿紧身外衣。所以至少我现在的样子不像个‘鬼子’。
当然无论我们怎么打扮,都不会比现场的中国官员来得更光彩夺目。如此众多的官员聚集在一起,远远望过去就像是一片神圣森严的森林。而站在黄色大伞底下的女皇陛下就是这片森林中独一无二的女神。与人们一贯对东方女皇性感、妖娆的描述不同,中华帝国的女皇穿着一套绣有金色花边的白色长裙,奇异的发式极富东方韵味。就算是最苛刻的清教徒也会评价这样的装束端庄得体。从这点上来看,比起埃及女王克丽奥佩特拉,这位中华女皇更像是东方的伊丽莎白。事实上,女皇的举止也很严谨。女皇仅上前拥抱了一下阔别五年之久的丈夫,便与其携手登上了一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却引来了周围其他中国人一阵诧异的惊呼。真是大惊小怪的东方人,我总觉得在这种的情况下女皇至少也得给亲王一个香吻才近情理。
不过接下来的程序却让人觉得有些麻烦。女皇在与亲王登上马车之后,周围官员和平民立刻就都跪了下来,然后弯下身来直到头碰地,同样的动作得重复三遍。这可比欧洲的单膝下跪复杂多了。可当时就是这种情况,近万名官员和平民被集中起来,整齐划一地一起做这套动作,而在两分钟的时间内皇帝的马车威严地穿过人群。现场的欧洲人当然也要学中国人那样照做。因为当全体中国人跪下时,单膝下跪的欧洲人就像是在弥撒中扬圣体时站着的信徒那样惹眼。不过那些天主教徒倒是做得像中国人一样利索,谁叫他们也经常做这样的‘体操’呢。
后来同行的吴告诉我们,一跪三叩已经是皇帝赐予的极大恩惠了。在中华女皇统治之前,正规场合下臣民必须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也就是说要跪三次,每次都要起立站直;每次跪地都要叩三个头。可既然女皇能将活动量减去了三分之二,那为何不能做得更彻底些,干脆像欧洲那样只单膝下跪一次。我将这个建议告诉了吴,结果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据说许多中国人都认为‘三跪九叩’的礼节是绝对必要的。并将自己能在盛大的场合当众向皇帝行三跪九叩视做一种莫大的殊荣。就算女皇现在简化了礼节,许多人还是坚持认为在隆重庄严的场合一定要行这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