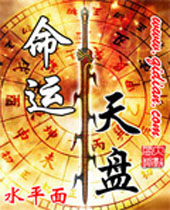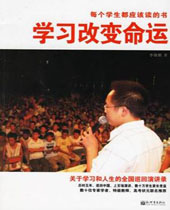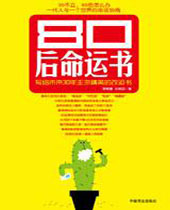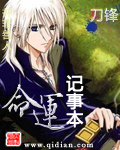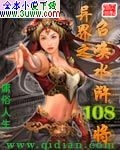104.命运的抉择-第49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依照当初孙露与大臣们达成的协定。皇子满15岁后,其课程会相应地将到调整。格物,天文,地理的内容会被大大削减。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经济,军事的课程。这之中自然也包口了之前一直被女皇阻挡在门房外的四书五经,以及目前风靡中原士林的《六韬》,《商君书》,《管子》,《笱子》等书。而今离两位皇子满十五虽还差几个月,可翰林院却早已迫不及待第为皇子安排好了课程,并挑选出了阵容强大的师资。
就这样在七月的一个艳阳日,隔着竹帘孙露以赞许地目光,注视着杨禹轩与杨念华双双在上书房向新来的师傅行了师生之礼貌。说起来,两位皇子对这几位信赖的师傅倒也并不陌生。他们分别是国会上院议长陈邦彦,下院议长王夫之,商学院院长李光先以及三湘书院的名士吴伟业。此外,一旁还端坐着上书房资历最深的国文师傅堵睿锡。
面对这三位名动天下的新同僚,堵睿锡丝毫没有一点儿紧张或忧虑。相反他却觉得异常的自豪,为自己的学生自豪。此刻的他总算是了解了女皇当年的良苦用心,明白女皇之前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在歧视国学,而是在为皇子打基础。那些看似无关的杂学,此时回头再一省视,至于天文地理则开拓皇子的眼界。如今两位殿下俨然已经为日后的深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女皇也就此将自己皇儿最擅学的年华叫给了华夏地精髓。
正当堵睿锡为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激动万分之时,却见为首的陈邦彦代表众师向两位皇子行礼道:“二位殿下。假期结束后,将由臣等三人将分别教授殿下新的课程。还望两位殿下日后兢兢业业,莫懈怠学业。”
“是,请师傅严加教导。”杨禹轩带着妹妹答礼道。
眼看两位皇子一副知书达礼的模样,在场的陈邦彦等人也是欣慰异常。却见他回头恭敬地向竹帘后头的女皇拱手道:“关于两位殿下地成绩,老夫与其他几位师傅之前都看过了。成绩相当不错。所以老夫以为不如今日换一种方式,由殿下向吾等提问。不知陛下意如何?”
“这。。。陈师傅,这恐怕有些不妥吧。”堵睿锡听罢犹豫着建议道。在他的印象当中,向来只有夫子考学生的,哪儿有学生考师傅的呢?
此时,却听竹帘后头的女皇沉声问道:“那其他几位师傅意下如何?”
“回陛下,为学生解答疑惑是为师者的职责。臣同意陈师傅的建议。”李光先不假思索地应和道。
“回陛下,臣也以为如此甚好。”王夫之跟着点头道。而坐在他身旁的吴伟业却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不动声色地拱手道:“请陛下定夺。”
“允,请诸位师傅自便吧。”竹帘地后头传来了女皇果断地声音。虽然孙露贵为帝王。但今天她却是以家长的身份在竹帘后头旁听的。因此孙露并不想对陈邦彦等人的教学方式及教学内容有所干预。
“谢陛下。”陈邦彦叩首谢恩后。回头便向两位皇子肃然道:“请二位殿下提问。”
面对这样地开局方式,杨禹轩与杨念华多少有点不适应。不过杨禹轩最终还是没能按耐住心中的鼓噪,壮着胆子开口道:“四位师傅,那学生就斗胆提问了。”
“殿下请。”陈邦彦鼓励道。
“不知师傅如何看待此次国会的修法提案?”杨禹轩抬起头正色道。
虽然杨禹轩一上就丢出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但除了堵睿锡略显局促外。其他三人都显得镇定异常。仿佛早就料到皇子会如此提问。只见为首的陈邦彦微笑着向杨禹轩反问道:”殿下觉得修法一事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现今京师大小报纸上不少名士都在就修法一事进行辩论。正如有些人说‘亲亲相隐’不合逻辑应该从我朝的律法中被剔除。而有些人则认为‘亲亲相隐’乃是伦常在律法中的体现,如果剔除则有违常伦。学生愚钝,觉得双方都有道理。所以在次想请教师傅解答。”杨禹轩礼貌地拱手道。
”殿下过谦了。而今朝野间关于伦常与律法地争议铺天盖地。殿下会产生疑惑也不足为奇。臣以为无论‘伦常论’者有那么光鲜的理由都不能掩盖‘亲亲相隐’的荒谬如果天下百姓均以‘亲亲相隐’为由袒护自己的亲人,亦或是象前朝那样要求百姓对自己的父母官‘亲亲相隐’。则朝廷的律法就不再会具有威严。届时民风堕落,吏制腐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朝廷必须剔除该项陋习,以免律法伦常化!“李光先头一个接口回答道。作为一个商学学者,李光先历来都是坚持法律至上的。事实上这也是多数商学学者的一致观点。因为一个高效健康的市场必须得建立在严明的法律规范之上。
不过在重农的一部分儒学学者看来,商学派的观点同样也是荒谬的。只见坐在一旁的吴伟业赶紧就反驳道:“孟子云: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国之律法怎能高国伦常秩序?”
“吴师傅,请何为伦常秩序?难道伦常秩序要求人们互相隐瞒罪行?要求百姓放任官僚对其的压榨吗?”杨禹轩适时地插口提问道。而这个问题也正市他一直想询问的。自小学习数理化的杨禹轩更习惯于以逻辑推理的方式来来思考问题。在他看来一个观点,一个名词都该有确切的解释,或限定的范围。而那种动辄就以“伦常天道”来含盖一切的做法,并不能让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信服。
“回殿下。《中庸》中曾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说人性得之于天道,故遵循人性统治天下是符合天命的。孝,娣,忠,信,义,廉乃是人最根本的天性,即伦常。就算是朝廷的律法亦不能违反伦常。因此,臣以为在律法中限定‘亲亲相隐’的范围确实必要。但就此要将其从律法中剔除则有违天命。”吴伟业义正言辞地说道。
果然,听完这段一气呵成的解说,杨禹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显然这个答案有点让他心动。不过此时的李光先很快就结果着对方的话锋据理力争道孝,娣,忠,信,义,廉固然是人之天性,可人的天性就只有善。就没有恶吗?难道对恶父,恶夫,恶主,也需要讲伦理吗?一个人若是犯了国法必定有过恶行,请问这范围又该如何划分?说到底‘法’本无‘情’。法若有请就做不到赏罚分明,做不到赏罚分明则无法威天下,无法威天下有怎谈得治理天下?”
“威天下?莫不是指以刑名绳下天下吧。暴秦的前车之鉴罄竹难书,李老师莫不是也想我朝重蹈覆辙吧。”吴伟业厉声责备道。
此时眼件两人争论逐渐升级大有成水火之势,在杨禹轩身旁一直没有开口的杨念华却突然微启朱唇道:“对不起,两位师傅,学生还是没有听明白。两位似乎在说同一样东西,又象是在说不同的东西。”
给杨念华这么一打断,吴伟业与李光先倒真是听了下来。事实上,在场的多数人都没有在意杨念华的存在。在众人的印象当中这位未脱稚气的皇女殿下更多的时候是以沉默的状态出现在女皇身边的。因此多数人将她今日的出现更多地看成了一种礼节而非实际的授课。但沉默的皇女殿下毕竟是开口提问了。于是吴伟业只好略显尴尬地向杨念华询问道:“请问殿下有何不解?”
“两位师傅刚才都说了律法与伦常。但两位师傅所说的律法与伦常听上去又都有区别。好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解释似的。”杨念华闪烁着明亮的眸子问道。
《命运的抉择》第二部 第二百六十二节 回皇女夫之巧解围 为皇家宗羲拟新法
面对杨念华疑惑的眼睛,在场的陈邦彦等人无一例外地都陷入了一片沉寂。还在这样地沉默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先前同样没怎么发言的王夫之向杨念华颔首:“二殿下,正因为每一个人对事物都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故而古人才会铸鼎立法。将对天道、伦常、刑律等等的共同认识刻在鼎上诏告天下”
“就像我朝的宪诰吗?”杨念华跟着追问道。
“二殿下说得没错。就像我朝的宪诰”王夫之微笑着应道。
“若是那样的话以宪诰中对伦常、律法的解释来修法不就行了吗?合则留之,不合则去之。宪诰中伦常与律法并没有冲突啊。”杨念华想了一下反问道。
“善。所以请二殿下放心。修法的提案国会很快就会依照宪诰得出结论,给民间一个明确的答复。”王夫之恭敬地说道。既像是在回答杨念华,又像是在对竹帘背后的女皇做保证。
一场原本针尖对麦芒的辩论,刹时就在王夫之与杨念华之间师生似地对话之中消弭了下来。不可否认,杨念华的这番话语在这些当事名宿眼中无疑是幼稚的。谁都可以清楚此次的修法之争背后带着太多的利益纠纷,并不是一个十四岁女孩可以理解的。然而谁也也不得不承认杨念华的这番话语同样让人无可辩解。
是啊,既然当初已经立过宪诰诏告天下,那就该依照宪诰中对伦常与律法的界定来决定是否修改《中华律》。否则,要么就无视宪诰,要么就干脆以自己的意志修宪。显然,无论是哪一条都是争辩双方目前难以做到的。
毕竟在中华朝宪诰是诸法之母,正如杨念华所言,任何律例的修改增删都不逾越宪诰。当然除了女皇的旨意除外。虽然在理论上女皇的旨意同样被宪诰所限。但在实际中手握兵权又被万民所仰的孙露就算不愿意遵照宪诰行事,其他人对其也只得无可奈何。不过到目前为止,孙露作为中华帝国的君王从未逾越过这条界限。就像女皇本人所说的那样,“一个明智地君王根本用不着破宪,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女皇如此身体力行之下。宪诰自然是被中华帝国上下视为了“镇国之契”。想要对其进行修改,同样成为一件难以实行的事。因为这其中所牵涉及的利益纠葛远大于人们的想象。
于是乎,一个十分诡异的局势就此摆着了众人面前。作为一个学说既然存在于世,当然是想自己的观点在世间推行。被统治者所接受,为万民所依仗。诸子百家莫不如此。而儒法道更是在这方面功利性极强。就而今的情况来看,士林间的学派不能有效地引起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于是这些学派在政治中体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就只剩下了“立法”一条。
如果那样地话,儒家从一开始就在宪诰中占有了优势地位。须知,宪诰中的诸多条款都是以儒家的典籍教条来诠释的。然而在另外一方面,宪诰中多数的诠释又与儒家典籍中的通常注解有着诸多出入。任何了解其内容的人都能觉察出《中华宪诰》的骨子里透出地是与传统礼教迥然不同的原则。
中华朝的士林怎么都没想到,当初权宜之计下的一纸文书,竟然会成为对他们所有人地束缚。借着今日为皇子上课的机会,陈邦彦等人原本想要试探一下女皇的态度。而皇长子也确实如他们所意料的那样提出了那个敏感地问题。却不想,双方才一交手,就被王夫之几句话给弄得不了了之了。
见此情形,陈邦彦下意识地憋了一眼王夫之。然而作为当事人地王夫之是一副若无其事地模样。而坐在他们对面的杨禹轩显然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可正当他想要进一步打破砂锅问到底之时,竹帘后头突然传出了母亲慈祥而又庄严的声音:“华儿,你有何问题要问师傅吗?”
“回母亲,孩儿刚才已经问了。王师父也已为孩儿解答。”杨念华回过身恭顺地行李道。
“恩。那好吧。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几位师傅辛苦了,各赏锦缎一匹,中午就留下来用膳吧。轩儿、禹儿你们随朕来。”孙露说罢,便欣然起身在一干宫女地簇拥下,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上书房。
虽然这样结束课程让陈邦彦等人多少觉得有些失落,但女皇既然这么说了,众人也只得起身恭送道:“谢陛下圣恩。”
接下来地午膳众人除了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客套话外,多少都显得有些索然无味。因此一用完膳陈邦彦等人便各自打道回了府。一路上与王夫之共乘一辆马车的吴伟业显然还在为先前的辩论耿耿于怀。却见他一抹胡子冷哼道:“这根本就是事先有预谋的。他们是不满意,陛下让我等也来给皇子授课。所以想借这次机会给我等来个下马威。”
“梅村,你多虑了吧。其实陈议长他们也只是在回答陛下的问题而已。”望着一脸愤然的同僚,王夫之淡然地安慰道。对于女皇如此的安排,王夫之当然心知肚明。若说不在乎上位者的态度那是在撒谎。这并不是说王夫之畏惧当权者的权威。而是作为一个读书人,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在心底总是希望能用自己所学一展才华。现今能给皇子授课乃是一个为天下学者所羡慕的良机。须知,历来为太早授课之人,一旦新皇登基必然会为新皇所重用。此外帝王儿时所学亦会影响到他日后的为政。在士林眼中在可堂上对太子施加影响,丝毫不亚于日后在朝堂上的明争暗斗。因此,也怪不得吴伟业如此在乎了。
“若是如此那是最好。”吴伟业口气嘲弄地说道。在他看来王夫之虽然学识渊博,为人谦和,但有时也太过软弱了一些。想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就埋怨道:“而农,刚才你真不应该那么快就打圆场。老夫不相信真辨不过李光先那厮。”
面对有些争强好胜的吴伟业,王夫之不为所动动地说道:“在下刚才也不过是在回答二殿下的提问罢了。”
“二殿下?”吴伟业眉毛一挑回味道。虽然王夫之称杨念华为“二殿下”,多少让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不错,杨念华确实是金枝玉叶,中华帝国也确实有女主的先例。但这并不代表杨念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能超过之前历朝的公主。更何况还有唐朝太平公主这个恶例在先。因此多数文臣士人都下意识地将杨念华排除在外。
“殿下身为陛下的次女,又尚未被册封为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