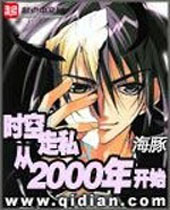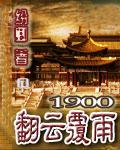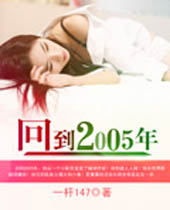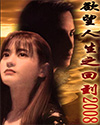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第14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说中的女人说,“我被罗马击中了。”男人说,“被它的完美?”女人又说,“不,被它的罪恶。”……罗马,就是罪恶!它与征服二字分不开。还有爱情,爱情完好无损,又破碎了,但它仍在那里!在那一片平原上,也在罗马这家饭店的大堂里。这一男一女的对话,一直持续到饭店的灯都熄灭了。男人本想与女人说最后一句话:当他看见她就立即爱上了她。而此刻,她睡着了。我忽然在想,男女之间的对话如果可以进行到底的话,不论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一定都是与爱情有关的。
沃维尔事件
我的窗外;刮着冬天的风;而不是夏天的风。冬天的风,号叫着,人们不让它吹进屋里。这种被拒之门外的感觉,与杜拉斯书中的那个村庄沃维尔,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沃维尔…让我感到一种你住进来就别走了的伤感与温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天,也许是最后一天,一个英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被德军击落。 飞机坠毁在法国卡尔瓦多斯省沃维尔的树林中,飞行员二十岁。 他起飞的时候 已经知道战争就要结束了,他微笑而梦幻般地起飞了。他或许相信 这次执行任务回来,就可以回到自己长大的那个地方了。
那天夜里,一声巨响惊醒了沃维尔。树林在燃烧,橙色的火光很亮。从断树中流出来的血也很亮。人们朝树林奔去,看见了发生的一切。一架飞机的残骸,一个已死的飞行员。 飞行员被卡在金属与乱树中间, 就那么卡着。 一种焦黑了的留恋, 在四周晨雾一样向海边蔓延。 飞行员在二十岁这个年龄停,留了下来, 成为永恒。
村子里的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抱下来。他们轻轻地抱着他,把他葬在了那座美丽的小教堂旁边。 人们给他立了一块浅灰色的花岗岩石碑, 他躺在花岗岩下边, 能听见教堂的钟声和孩子们唱的歌:“ 我永远忘不了你……” 整个村子的人, 都为这个年轻的飞行员哭泣。 他们点着蜡烛,为他祈祷。
有位老人每年来看飞行员,他也是英国人。老人在飞行员的墓前。一边放上鲜花,一边流泪。他不是飞行员的父亲, 他大约是他的老师 ,或是他父母生前的好友。 是这位英国老人,说出了飞行员的名字 克利夫—— 于是, 这名字被刻在了浅灰色的花岗岩石板上。老人来沃维尔 ,持续了八年。 第九年他没有来, 以后就再也没有来。 克利夫是个孤儿 那位英国老人不来了, 就再没有别人来了。 从此, 在沃维尔, 克利夫完全成了这个村庄的孩子。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 杜拉斯,写下了 “沃维尔事件” 她在写这篇东西的日夜里总想哭。 我发现, 杜拉斯是一个很爱哭的女人。 她流着眼泪, 回想着她所知道的许多死去的人们。 包括在战争中牺牲的哥哥。 她说, 她的哥哥的情况与克利夫不同, 他没有任何坟墓, 他被扔进尸体堆里。 消失在其他尸体之中, 无法区别出来, 没有人知道这个法国男人是谁。 这一点杜拉斯心里非常清楚, 没有人知道, 杜拉斯在法国的乡间别墅里思念着哥哥。 而这里不是战场, 战场在许多地方, 战场是大片的死亡, 绝不是一个人的死亡。杜拉斯渴望区别什么, 其实, 她的这篇东西就是在写一种区别,死与死之间的区别, 还有死后与死后的区别, 特别是死后的。 克利夫能够埋葬在沃维尔。
“沃维尔”这三个字而感动。 这个字很轻松, 它让人在感受着战争的沉重与残酷的同时,又感受到了一种安宁。 杜拉斯写作的桌子对面有扇窗户, 她抬起头能看见窗外来自西班牙南部的天竺葵, 还有蓝蓝的天空。 克利夫的眼睛, 也像天空那么蓝。 可是哥哥眼睛中的蓝色, 却不能保持到最后, 想保持也保持不住。 因为, 那里不是沃维尔哥哥死在战争期间, 死在许多人中间。 克利夫死在战争的最后一天, 这个, 最后让杜拉斯如此在意。 再过一个夜晚, 或许再过几小时就和平了。 这最后与和平离得真近,也真无情,我在流泪,杜拉斯写道:她不止一次地写道,至今我仍在流泪,她去看那个飞行员了。 去沃维尔,她必须看一眼那片被杀害的树木。
看一眼那块浅灰色的花岗岩石碑 ,看一眼那个质朴而温柔的村庄。 杜拉斯的朋友伯努瓦, 雅科来她的寓所看她。 他说 ,他想拍一部电影, 杜拉斯给他讲了飞行员的故事。 他被感动了, 开始拍电影 ,拍成了电影的名字与杜拉斯这部作品的名字一样,叫《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30
不必勉为其难争第一
●木 梓
我近期的头等大事,是致力于打消我3岁半的女儿奋勇争第一的念头。
有一天,从幼儿园接女儿,问她晚饭吃的是什么,她答非所问却充满自豪地告诉我:“我第一名。”黄昏的阳光照在她得意洋洋的小脸上,镀了一层金黄色。
费了半天劲,我总算闹明白,她的意思是说,她吃得最快,老师夸了她。结果我一路都在给她讲,吃好吃饱最重要,不用第一名,和小朋友们差不多就行。
我着实担心这种争第一的教育,会从这类一粥一饭的小事上开始影响我的宝贝,渗透进她的价值观,最终影响她一生的幸福指数。
以做妈妈的对她使用筷子和勺的能力,以及日常吃饭速度的了解,我知道她百分之百没吃够,也肯定吃不好。果然,那天晚上,她很早就缠着我说饿了。
这个第一,是勉力“争”来的,超越了她的能力范围,代价是对她自己的损害。人生不是竞技体育,不需要“永远争第一”。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现实地说,简直是永远也争不来“第一”———圈子稍稍拓开一点,就又有比你这儿强那儿强的了,哗啦啦一数一大串,谈何“第一”呢?
主流教育混同了进取心和争强好胜的概念。是的,有进取心的人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但上进和争强好胜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
上进是纵向的,是个人的、线上的比较。每往前走一点,每有一点长进,都可以让人对自己满意。“自我感觉良好”在汉语体系里永远含着些许贬义,但细想一下,这有什么不好吗?难道非得自我感觉很糟,才是美满的人生?我知道“幸福”的一种定义,就是“对自己满意”,这是一位很有阅历的大姐给出的,让人服气。
争强好胜,要点在“争胜”上,这决定了横向比较的方式。而“人比人,气死人”,那可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这种比较之下,永远都不会快乐。
我跟谁谁都差不多,凭什么他就如何,我就不能如何?抑郁、焦虑、不满、愤愤不平乃至嫉恨等种种负面情绪均根植于此。
争强好胜,让人对自己的状态不满,而长期困于对自己的不满意里,往往还导致对别人的不满意,好像别人哄抢了他的机会、他的资源,由此充满被掠夺感,受虐意识强烈。这种情绪恶性蔓延,会不可扼制地迁怒于人,致力于发掘别人的差劲儿、别人的不足,直至觉得全世界都欠自己的。
主流教育在这两个重要概念上的混淆,是很多不幸人生的开始。
一个很有智慧的忠告是,如果有一样东西,你踮踮脚尖就够着了,那就去够吧,这叫做努力,叫做进取;如果非要跳起来才能够到,就别费劲了,因为你努力着跳高,还是会落下来的,超出能力了,这叫勉为其难。那些咬牙切齿的攀升,用力过猛的向上,代价是对自己的损害。像我可怜的没吃饱的小女儿。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5
白天纽约,黑夜巴黎
●王文华
纽约和巴黎,代表了我人生的两个面向。纽约是白天,巴黎是黑夜。纽约是前半生,巴黎是下半场。
三十五岁之前,我认定纽约是世上最棒的城市。我在加州念研究所,毕业后迫不及待地去纽约工作。一做五年,快乐似神仙。我爱纽约的原因跟很多人一样:她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文化的中心。丰富、方便。靠着地铁和出租车,你可以穿越时间,前后各跑数百年。人类最新和最旧、最好和最坏的东西,纽约都看得见。
所以在纽约时,我把握每分每秒去体会。白天,我在金融机构做事,一天十小时。晚上下了班,去NYU学电影,一坐四小时。在那二十多岁的年纪,忙碌是唯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活着,就是要把自己榨干,把自己居住的城市,内外翻转过来。这种想法并不是到纽约才有的。其实从小开始,台湾人就过着纽约生活。纽约生活,充满新教徒的打拚精神和资本主义的求胜意志。相信人要借着不断努力,克服万难、打败竞争。活着的目的,是更大、更多、更富裕、更有名。权力与财富,是纽约人的两个上帝。而能帮你走进天堂的鞋,就是事业、事业、事业。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生活方式,为了保持领先,每个人都在赶时间、抢资源。进了电梯,明明已经按了楼层的钮,那灯也亮了,偏偏还要再按几下,彷佛这样就可以快一点。出了公司,明明已经下班了,却还要不停讲手机,摇控每一个环节。在纽约,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赶尽杀绝。在纽约,没有坏人,只有失败者。
每一件事,都变成工作。上班当然是工作,下班后的应酬也是工作。有人谈恋爱是在工作,甚至到酒店喝酒、KTV狂欢,脸上都杀气腾腾,准备拚个你死我活。
我曾热烈拥抱这种生活,并着迷于这种因为烧烤成功而冒出的焦虑。这种焦虑让我坐在椅子边缘,以便迅速地跳起来闪躲明枪暗箭。这种警觉性让我练就了酒量和胆量、抗压性和厚脸皮。但也养成了偏执和倔强、优越感和势利眼。在纽约时我深信:能在这里活下来的,都是可敬的对手。黯然离开的,统统是输家。人生任何事,绝对要坚持到底。半途而废的,必定有隐疾。在这不睡的城市,每天我醒来,带着人定胜天的活力,跟着法兰克辛纳屈唱〈纽约·纽约〉:「如果你能在纽约成功,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成功!」是的,在纽约,现代的罗马竞技场,我要和别人,以及自己,比出高低。
这套想法,在我三十五岁以后,慢慢改变。
第一件动摇我想法的,是父亲的过世。我父亲一生奉公守法、与人为善。毫无不良嗜好,身体健康地像城堡。七十二岁时,他得了癌症、引发中风,经历了所有的痛苦和羞辱。他一生辛勤工作、努力存钱、坚信现在的苦可以换得更好的明天。我们也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用在纽约拚事业的精神照顾他。但两年的治疗兵败如山倒,最后他还是走了。父亲逝世的那天,我的价值系统崩溃了。我一路走来引以为傲的「纽约精神」,没想到这么脆弱。
不止在病床,也在职场。当我在企业越爬越高,才发现「资本主义」在职场中也未必灵验。上过班的都知道,很少公司真的是「开放市场」、「公平竞争」。大部分的同事都觉得你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职场上伟大的,未必会成功。成功的,有时很渺小。很多人一辈子为公司鞠躬尽瘁,最后得到一支纪念笔。那些卷款潜逃的,反而变成传奇。
慢慢的,我体会到:世上有一种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更高、更复杂的公平。人生有另一种比「功成名就」更幽微、更持久的乐趣。那是冲冲冲的美式资本主义,所无法解释的。
我能在哪里找到那种公平和乐趣呢?我想过西藏、不丹、非洲、纽西兰。然后,我注意到法国。
住纽约时,法国是嘲讽的对象。身为经济、科技、和军事强权的美国,谈起法国总是忍不住调侃一番。法国是没落的贵族,值得崇拜的人都已作古。法国人傲慢,高税率让每个人都很慵懒。动不动就罢工,连酒庄主人都要走上街头。
搬回台湾后,普罗旺斯、托斯卡尼突然流行。我看了法兰西斯·梅思的《美丽的托斯卡尼》,其中一句话打动了我:「在加州,时间像呼拉圈。我扭个不停,却停在原地。在托斯卡尼,我可以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提着一篮李子,逍遥地走一整天。」
是啊!我在赶些什么?我耗尽青春用尽全力,拚命追求身外之物,结果我真的比别人有钱、有名吗?更重要的,我真的因此而快乐吗?远方有广阔的地平线,为何我还在原地摇过时的呼拉圈?
当我重新学习法国,我发现法国和美国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美国人追求人定胜天,凡事要逆流而上。法国人讲究和平共存,凡事顺势而为。纽约有很多一百层的摩天大楼,巴黎的房子都是三百年的古迹。纽约不断创新,巴黎永远有怀旧的气息。巴黎人在咖啡厅聊天,纽约人在咖啡厅用计算机。纽约有人潮,巴黎有味道。纽约有钞票,巴黎有蛋糕。
不论是政府或个人,法国人都把精神投注在食、衣、住、行等「身内之物」。就让美国去做老大哥吧。要征服太空、要打伊拉克、要调高利率、要发明新科技,都随他去。法国人甘愿偏安大西洋,抽烟、喝酒、看足球、搞时尚。当美国人忙出了胃溃疡,法国人又吃了一罐鹅肝酱。
讲到吃,法国有三百种起司、光是波尔多就有五十七个酒的产区。晚上六点朝咖啡厅门口一坐,一杯红酒就可以聊三个小时。九点再去吃晚餐,一直吃到隔天凌晨。他们在吃上所花的时间,跟我们上班时数一样。但讽刺的是:他们没有「All You Can Eat」。
吃很重要,但也要会挑时间,朋友介绍我去试一家法国餐厅,提醒我他们礼拜二、四晚上休息。「为什么?」我问。他说:「因为主厨要回家看足球。
法国人比美国人会玩。每年六月的巴黎音乐节,从午后到深夜,几百场露天音乐会在各处同时举行,人多到地铁都暂停收费。每年十月的「白夜」,平日入夜就打烊的店面,彻夜营业到清晨七点。每年夏天,巴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