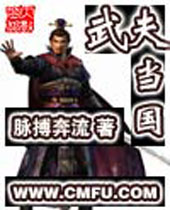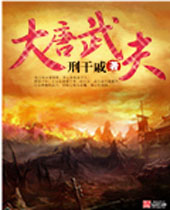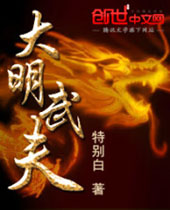武夫当国-第10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文年应道:“大人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
【圣诞节快乐,哈哈哈,各位大大快快乐乐哦。眼看又要过年了,大家抽空给家人打一个电话哦!】
第84章,实业赈灾
次日一早,何其巩从滦州发来电文,将大前天慈善宴会所筹得的款项以及换购粮食的账目做了详细的汇报。拍卖所得的收入是五万八千元,而募捐所得的收入是五万四千元,合计已经超过十一万元。
这个数目大大超出了袁肃的意料,先是拍卖所得的款子居然比募捐还要多,之后总数目还超过是十万,当真是天大的喜讯。他很清楚拿去拍卖的几件东西都值不了三万块,最贵的还是王磷同收藏多年的一副纪晓岚的折扇,但因为时代不算太远,而且纪晓岚的字画市面上流传的很多,再贵也贵不过一万块。
然而更让他感到惊奇的是,整个拍卖会卖得最贵的并不是这副纪晓岚折扇,竟然是自己的那支左轮手枪。据何其巩在电文里介绍,当时竞价这支手枪的人数超过了三十人,前后叫出了五十五次价格,最终以两千三百英镑的天价被汉纳根拍下。
两千三百英镑折合成银元足有两万之多,已然占去了整个拍卖所得的一半。
尽管心头惊疑不定,一支造价几十元的手枪配合几元钱的装饰,卖出一千倍的价格,恐怕这当真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拍卖。不过也未必没有合理的解释,既然是为了慈善,拍卖的竞价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说不定汉纳根是真心实意为了帮这个忙。
再者汉纳根是为英国人工作,京奉线也是英国人的利益所在,英国方面自然是希望山海关这边的事情能尽快结束。
抛开这些琐碎不去计较,这十一万元的款子只要合理利用,完全可以帮助所有难民维持两个月甚至更久的生活所需。
不过电文下面的内容很快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虽然募集了这笔钱,可是不管是滦州还是其他县城,所有粮商的存货很紧缺。一部分粮食的货物早在年初时就被关外的一些豪商扫空,即便有存货的商号也是只进不出。
经过这两天的收购,目前能以市价七两一石购进的粮食不足五百石,另外以十元、十二元高价购进的粮食,总计也只有一千多石。算上滦州几位大老爷捐赠的陈米,现在到手的粮食将近是两千石。
何其巩表示会尽快派人到天津、保定一带收粮,而第一批预备好的两千石粮食,则已经安排好七月二十八日凌晨的一列火车送到临榆县,当天傍晚应该就能抵达。
看完电文后,袁肃也知道目前市场上各种投机的勾当,只是这滩水实在太深,即便他有心治理也不是一两个月就能见成效的事。好在两千石大米是雪中送炭,再者总计十一万元的资金,在天津、保定肯定能够收到更多的粮食,完全可以支撑到中央下拨赈灾物资。
他立刻找来吴立可和陈文年,把这件事交代下去,让他们尽快安排好火车站的接应工作。
然而听完袁肃的话之后,吴立可忽然灵机一动,忍不住进言道:“不得不说,袁大人居然筹集到了十一万元的赈济款,当真是让我等乍然称叹。不过,若是袁大人仅仅以这笔赈济款购买粮食来接济难民的话,未免有一些大材小用。”
袁肃不动声色的看着吴立可,不轻不重的问道:“吴大人有什么见解?”
吴立可笑了笑,颇有深意的说道:“是这样的,袁大人您得知道这十一万元的款子可相当是一笔巨款。实不相瞒,我临榆县地处交通要隘,有铁路也有港口,一年总计税收不足三十万而已。这十一万元要想救活困在关口的那些难民,是完全有这个可能的,哪怕一时无法救助全部的人,也足以救助其中一部分呢。”
袁肃依然没听明白吴立可的意思,他有几分不耐烦的追问道:“吴大人到底想说什么?”
吴立可反问道:“敢问袁大人,您认为此次中央下拨赈灾物资合计能有多少钱?”
这个问题倒是把袁肃问住了,不管是前世还是今世,他只知道缓解灾情需要很大的功夫,但具体赈灾所用的物资有多少还真没个准。
“恕在下直言,照在下多年为官的经验来推测,不足十万人受灾中央根本不会放在心上。而今是因为这些灾民逼到京城大门口,又截断了京奉线铁路,所以才引起北京方面重视。因此,此次京城调拨下来的赈灾物资,总计最多只有十五万,最最多也决计不超过二十万。”吴立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道。
“是吗?”袁肃眉宇紧蹙了起来,他这时才明白吴立可之前所说的意思。
与其用这十一万元赈济款购买粮食延续难民的生存,还不如下定决心直接用这笔款项疏导难民。购买粮食只是一时之计,总不能养着这些难民一年半载的时间。而只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源,让这些难民能自行生活,方才能化解这次灾情。
“在下可不敢诓袁大人,上面能下来二十万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再多也不可能多出哪里去。说来,中央那边也是没有多余的钱,国家大局未稳,南方一片涣散,即便有钱也要用来稳定国家,哪里会把这几万灾民当作一回事?”吴立可意味深远的说道。
“听吴大人这么说,彷佛已经心坏成策,还请明示一二。”袁肃想了想之后,最终决定听一听吴立可的打算。处理这次灾情他是有责任在身,越早解决这件事,对自己越好,更何况自己也感觉到十一万元能够办很多事,若是单纯的收购粮食,到头来这笔钱终究是被那些黑心的粮商给赚去了。
“昨日早上开会时,袁大人您也说过,赈灾最重要的无非是治和养,最终目的是疏导这些灾民能够落地生根或者返回原籍,不至于见天的困在关口等着救济。现在袁大人有了资金,那赈灾之事就好办的多,按照以往的惯例,在下倒是可以提出两个屡试不爽方法。”吴立可一副头头是道的样子说着。
“是何办法?”
“其一是袁大人给每一个灾民派发一笔钱或者一袋粮食,让他们返回原籍。这个办法最快速也最直接,自古以来的赈灾都是这个法子。其二则是以这十一万元为本钱,拉拢地方士绅合资开办项目,吸纳这些难民的劳动力。”
袁肃自然相信这两个法子是官府屡试不爽的办法,第一个办法既简单又迅速,即便是治标不治本但也能很快给上面一个交代,至于第二个办法比第一个办法好,但是只适用于难民人数不多的情况。现如今外面有七万多人,这么庞大的人群怎么可能说吸纳就吸纳?
更何况,合资开办项目也要能周转盈利才行,否则依然无法持之以恒的起到安民目的。
“给难民派发一笔钱、一袋粮食让他们回去,如何确保他们回去之后能恢复生活?倘使不能恢复生活,那他们去而复返,岂不又成了一个问题。”不等袁肃开口,站在一旁的陈文年忍不住向吴立可询问道。
“陈大人所言极是,多少年官府赈灾无不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导致逃荒的原因不仅仅是天公不作美,有时候也是因为一时周转不灵。给难民派发一笔钱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周转,同时再与受灾地区的县府联络,下令县府做好接应、安顿的准备。”吴立可说道。
“一时周转不灵?这可未必如是。若是真正的天灾,而且灾情十分严重,你叫这些老百姓如何周转?”陈文年没好气的说道,他总觉得吴立可的话一派陈腔滥调,根本不可能彻底根治眼前的问题。
“唉,陈大人,若是按照您这么想,赈灾永远是无底洞,不仅填不满,而且还会滋生难民的刁性。说到底,天灾人祸总有过去的时候,他们逃荒在外已经这么多时日,故里的情况或许早有好转。只消各地官府与当地豪绅联络联络,放宽一些税费,许一下借贷,日子勉勉强强总能熬过去的。”吴立可可以在袁肃面前装孙子,但是在陈文年面前却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姿态,说话时颇有居高临下的意思。
“这些都只是草率的为了表面工作,长此以往只会祸患积深。”陈文年对吴立可说话时的态度很不舒服,变了脸色向吴立可呵斥道。
“历朝历代,赈灾无非皆是如此。若陈大人还有更好的办法,在下愿意洗耳恭听。”
陈文年顿时语塞,他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但却打心底里不认同吴立可的办法是好办法。
这时,默然许久的袁肃抬了抬手,止住了二人的争吵,他语气冷静的说道:“双管齐下,或可有所作为。即便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多多少少能解决部分的问题。至于剩下的问题,就只能等中央调拨赈济物资再另行安排。”
吴立可和陈文年立刻明白了袁肃所谓“双管其下”的意思,那就是一边派发钱粮遣散难民,一边开办项目吸纳劳动力。就目前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而且比单独用一个方法安置难民要好的多。
第85章,初露野心
“袁大人果然奇思妙想,双管齐下一定能水到渠成。”吴立可换上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毫不掩饰“拍马屁”的意思说道。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今临近各地都不景气,又能开办什么项目?而且显然不能是小项目,大项目的话前前后后筹措繁复,兼顾众多风险,一时半会还不能立见成效,如何能吸纳这些难民安置下来?”袁肃再次问道。
“这件事说难办也不难办,说不难办也得看是谁来办。”吴立可绕口令似的说道。
“此话怎讲?”
“袁大人,其实早几年咱们临榆县以及附近的抚宁县、卢龙县都有过大兴实业的打算。从前年年中到今年年初,在下与抚宁知县……哦,是县长,在下与抚宁县陶县长多次会晤,正打算集两县之力办两个大项目,其一是修建洋河水库,其二是共同承建南戴河大码头和附属的砂场。”吴立可说话时的表情渐渐显得一丝不苟起来。
“洋河水库?南戴河码头和砂场?这果然都是大项目,而且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莫非是因为资金原因而最终不得实施吗?”袁肃追问道,诚实地说他对这两个项目很感兴趣。不过他印象中倒是记得洋河水库修建于一九五九年,洋河可是属于内陆较大的河流,对于一九一二年现阶段的工业水平,实在是有一定挑战性。
“资金确实是一方面,不过因为是我们两县合力,勉勉强强还是能凑够第一期预算。原本的计划就是筹一期修一期,五年之内应该可以完工。主要的原因是水库要引进洋人的水车发电机械,我们先后与法国、花旗国进行交涉,哪里知道洋人狼子野心,说要由他们负责承建并经营发电厂才肯出让机械。”吴立可哎声叹息的说道。
“之后呢?”
“袁大人您可不知道,我们两县筹集的第一期资金是二十万,法国人承建要三十万,花旗国人承建要二十九万。这算个什么事呀?分明就是坐地起价!不仅如此,还要把发电厂的经营权让出二十年,二十年呐!洋鬼子就出一个发电的机械,就硬生生的剥削咱们二十年,别说二十九万、三十万,除非他们免费承建,否则换做谁都不会答应的。”吴立可越说越有情绪,语气愈发显得铿锵起来。
“这买卖确实不能做,洋人奇技淫巧自居,就是打算漫天要价来侵害我中国权益。”陈文年表情肃然的附和道。
“那码头和砂场呢?”袁肃不动声色的又问道。
“咱们临近沿海的地方,采集海砂本来就是一项生计,码头亦如是。去年年中时南戴河码头倒是建起来了,可是相隔不远的北戴河多是洋人的教区和侨民居住地,那些洋商为了保证自己港口码头的生意,与所有到山海关港口的船只签订条约,只许去北戴河靠岸,否则一律终止商贸往来。很多外地的货船就是靠跟洋人做生意来谋生,无奈之下只能跟洋人签约。好端端的南戴河码头硬生生的被挤垮了。”吴立可无奈的摇着头,唏嘘不止的说道。
“洋人当真是欺人太甚。”陈文年咬牙切齿的说道。
“南戴河码头到现在还欠几家银行几万元钱,因为资金短缺,开办杀场也成了泡影。”吴立可继续诉苦的说道。
听完吴立可的一番话,袁肃心中渐渐明白了对方之前所说的那句话的意思。
临榆县和抚宁县势单力薄,没办法跟洋人作对,虽然地处交通枢纽所在地,可重要的交通线路都被洋人掌握,因而财政上也是十分窘迫。
洋河水库和南戴河码头可以说是民族自力更生的两个工程,这两个工程也确确实实利国利民,而且就工程的规模来说也绝不算小。像吴立可所预料的那样,修建水库需要五年时间,足以解决一大批就业问题。南戴河码头虽然是与北戴河的洋人有竞争,可只要把码头做起来了,同样能够养活许多人,要知道码头衍生出来的周边产业可是非常之多。
总的来说,这两个项目都是因为洋人的干扰所以才告吹。洋人之所以敢如此放肆,全然是不把临榆县和抚宁县的地方官放在眼里。
而现在,他身为东直隶护军使,又是大总统的侄子,背后还与英国人有一份交情,若是由自己盘下这两个项目来做,必然是能够办成此事的。洋人就算再嚣张,也不至于明目张胆的干涉中国内政。
他甚至可以通过雷诺森的关系,周旋一下子这两个项目与北戴河洋商之间的冲突。
这些都不是问题,而唯一的问题是他还没有伟大到这种程度。
袁肃心里有一个结,那就是山海关并非他的地盘,此番前来是奉命主持赈灾,一旦灾情稳定下来自己早晚还是要返回滦州。他把十几万的资金投资到临榆县,前前后后还要为这件事与洋人周旋,最终得到好处的却不是自己!
表面上来看这属于道德的考量,但实际上这其中还有能力与功利的影响。
一方面没有这种高度硬要做这样的事,只会是打肿脸充胖子;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很快陷入兵荒马乱的局势,不是你吃他,就是他吃你,现实是不容许存在这份道德心。
不过,在一番沉思之后,袁肃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