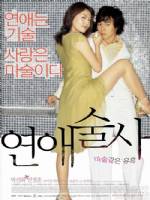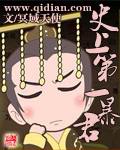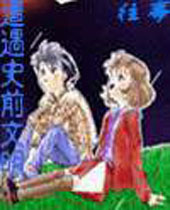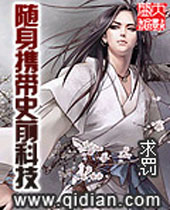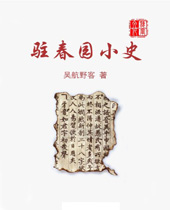西方哲学史-第1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芝诺暗中假定了柏格森的变化论的要义。那就是说,他假定当物件在连续变化的过程中时,即便那只是位置的变化,
413
214卷三 近代哲学
在该物件中也必定有某种内在的变化状态。该物件在每一瞬。。
间必定和它在不变化的情况下有本质的不同。
他然后指出,箭在每一瞬间无非是在它所在的地方,正像它静止不动的情况一样。因此他断定,所谓运动状态是不会有的,而他又坚持。。
运动状态是运动所不可少的这种见解,于是他推断不会有运动,箭始终是静止的。
所以,芝诺的议论虽然没有触及变化的数学解释,初看之下倒像驳斥了一个同柏格森的变化观不无相似的变化观。
那么,柏格森怎样来对答芝诺的议论呢?他根本否认箭曾在某个地方,这样来对答。在叙述了芝诺的议论之后,他回答道:“如果我们假定箭能够在它的路径的某一点上,芝诺就说。
得对。
而且,假如那支运动着的箭同某个不动的位置重合过,他也说得对。但是那支箭从来不在它的路径的任何一点上。“。
对芝诺的这个答复,或者关于阿基里兹与龟①的一个极类似的答复,在他写的三部书中都讲了。柏格森的见解坦白说是誖论的见解;至于它是不是讲得通,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讨论。。。
一下他的绵延观。他支持绵延观的唯一理由就是讲变化的数学观“暗含着一个荒谬主张,即运动是由不动性做成的”。但是这种看法表面上的荒谬只是由于他叙述时用的词句形式,只要我们一领会到运动意味着“关系”
,这种荒谬就没有了。
例如,友谊是由作朋友的人们做成的,并不是由若干个友谊做成的;家系是由人做成的,并不是由一些家系做成的。同
①芝诺的另一个誖论,内容是说希腊神话中的善跑者阿基里兹(Achiles)
的出发点如果在一只乌龟的出发点后面,他将永远追不上那只乌龟。——译者
414
第二篇 从卢梭到现代314
样,运动是由运动着的东西做成的,并不是由一些运动做成的。
运动表示如下事实:物件在不同时间可以在不同地点,无论时间多么接近,所在地点仍可以不同。所以,柏格森反对运动的数学观的议论,说到底化成为无非一种字眼游戏。有了这个结论,我们可以进而评论他的绵延说。
柏格森的绵延说和他的记忆理论有密切关联。按照这种理论,记住的事物残留在记忆中,从而和现在的事物渗透在一起:过去和现在并非相互外在的,而是在意识的整体中融混起来。他说,构成为存在的是行动;但是数学时间只是一个被动的受容器,它什么也不做,因此什么也不是。
他讲,过去即不再行动者,而现在即正在行动者。
但是在这句话中,其实在他对绵延的全部讲法中都一样,柏格森不自觉地假定了普通的数学时间;离了数学时间,他的话是无意义的。说“过去根本是不再行动者”
(他原加的重点)
,除了指过去就是。。。。。
其行动已过去者而外还指什么意思呢?
“不再”
一语是表现过去的话;对一个不具有把过去当作现在以外的某种东西这个普通过去概念的人来说,这话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的定义前后循环。他所说的实际上等于“过去就是其行动在过去者”。作为一个定义而论,不能认为这是一个得意杰作。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现在。据他讲,现在即“正在行动者”
(他原。。。。。
加的重点)。但是“正在”二字恰恰引入了要下定义的那个现在观念。
现在是和曾在行动或将在行动者相对的正在行动者。。。。。。。
那就是说,现在即其行动不在过去、不在未来而在现在者。
这个定义又是前后循环的。同页上前面的一段话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谬误。他说:“构成为我们的纯粹知觉者,就是我们的
415
414卷三 近代哲学
方开始的行动……我们的知觉的现实性因而在于知觉的能动。。。。。
性,在于延长知觉的那些运动,而不在于知觉的较大的强度:。
过去只是观念,现在是观念运动性的。“
由这段话看来十分清楚:柏格森谈到过去,他所指的并不是过去,而是我们现在对过去的记忆。过去当它存在的时候和现在在目前同样有能动性;假使柏格森的讲法是正确的,现时刻就应该是全部世界历史上包含着能动性的唯一时刻了。在从前的时候,曾有过一些其他知觉,在当时和我们现在的知觉同样有能动性、同样现实;过去在当时决不仅仅是观念,按内在性质来讲同现在在目前是一样的东西。可是,这个实在的过去柏格森完全忘了;他所说的是关于过去的现在观念。实在的过去因为不是现在的一部分,所以不和现在融混;然而那却是一种大不相同的东西。
柏格森的关于绵延和时间的全部理论,从头到尾以一个基本混淆为依据,即把“回想”这样一个现在事件同所回想的过去事件混淆起来。若不是因为我们对时间非常熟悉,那么他企图把过去当作不再活动的东西来推出过去,这种做法中包含的恶性循环会立刻一目了然。实际上,柏格森叙述的是知觉与回想——两者都是现在的事实——的差异,而他以。。。
为自己所叙述的是现在与过去的差异。只要一认识到这种混淆,便明白他的时间理论简直是一个把时间完全略掉的理论。
现在的记忆行为和所记忆的过去事件的混淆,似乎是柏格森的时间论的底蕴,这是一个更普遍的混淆的一例;假如我所见不差,这个普遍的混淆败坏了他的许多思想,实际上败坏了大部分近代哲学家的许多思想——我指的是认识行为
416
第二篇 从卢梭到现代514
与认识到的事物的混淆。在记忆中,认识行为是在现在,而认识到的事物是在过去;因而,如果把两者混淆起来,过去与现在的区别就模糊了。
在一部《物质与记忆》中,自始至终离不了认识行为与认识到的对象的这种混淆。该书刚一开头解释了“心象”
,这种混淆便暗藏在“心象”一词的用法中。在那里他讲,除各种哲学理论而外,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心象”
构成的,心象确实构成了全宇宙。
他说:“我把诸心象的集合体叫做物质,。。
而把归之于一个特定心象即我的肉体的偶发行动的同一些心象叫做对物质的知觉“。可以看到,据他的意见,物质和对物。。。。。。
质的知觉是由同样一些东西构成的。他讲,脑髓和物质宇宙的其余部分是一样的,因此假如宇宙是一个心象,它也是一个心象。
由于谁也看不见的脑髓按普通意义来讲不是一个心象,所以他说心象不被知觉也能存在,我们是不感觉惊异的;但。。。。。
是,他后来又说明,就心象而言,存在与被有意识地知觉的。。。。。。。。。
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另外一段话也许能说明这一点,在那段话里他说:“未被知觉的物质对象,即未被想像的心象,除了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的状态而外,还会是什么呢?”
最后他说:“一切实在都和意识有一种相近、类似,总而言之有一种关系——这就是通过把事物称做‘心象’这件事实本身我们向观念论让步的地方。”
然而他仍旧讲,他是从还没有介绍哲学家的任何假说之前讲起的,打算这样来减轻我们一开始的怀疑。
他说:“我们要暂时假定我们对关于物质的各种理论及关于精神的各种理论毫无所知,对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或
417
614卷三 近代哲学
观念性的议论毫无所知。
这里我就在种种心象的面前。“
他在为英文版写的新序言中说:“我们所说的‘心象’是指超乎观念论者所谓的表象以上、但是够不上实在论者所谓的事实的。。。。
某种存在——是一种位于‘事实’和‘表象’中途的存在。“
在上文里,柏格森心念中的区别我以为并不是想像作用这一精神事件与作为对象而想像的事物之间的区别。他所想的是事物的实际与事物的表现之间的区别。至于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即以进行思考、记忆和持有心象的心为一方,同以被思考、被记忆或被描绘心象的对象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就我所能理解的来说,这个区别在他的哲学中是完全没有的。不存在这种区别,是他真正假借于观念论的地方;而且这是非常不幸的假借。从刚才所讲的可以知道,就“心象”来说,由于不存在这种区别,他可以先把心象讲成中立于精神和物质之间,然后又断言脑髓尽管从来没有被描绘成心象,仍是一个心象,随后又提出物质和对物质的知觉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未被感知的心象(例如脑髓)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的状态;最后,“心象”一词的用法虽然不牵涉任何形而上学理论,却仍旧暗含着一切实在都和意识有“一种相近、类似,总而言之有一种关系”。
所有这些混淆都是由于一开始把主观与客观混淆起来造成的。
主观——思维或心象或记忆——是我里面现存的事实;客观可以是万有引力定律或我的朋友琼斯或威尼斯的古钟塔。主观是精神的,而且在此时此地。所以,如果主观和客观是一个,客观就是精神的,而且在此时此地:我的朋友琼斯虽然自以为是在南美,而且独立存在,其实是在我的头脑
418
第二篇 从卢梭到现代714
里,而且依靠我思考他而存在;圣马可大教堂的钟塔尽管很大,尽管事实上四十年前就不再存在了,仍然是存在的,在我的内部可以见到它完整无损。这些话决不是故意要把柏格森的空间论和时间论滑稽化,仅仅是打算说明那两个理论实际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主观和客观的混淆并不是柏格森特有的,而是许多唯心论者和许多唯物论者所共有的。许多唯心论者说客观其实是主观,许多唯物论者说主观其实是客观。他们一致认为这两个说法差别很大,然而还是主张主观和客观没有差别。我们可以承认,在这点上柏格森是有优点的,因为他既乐意把客观和主观同一化,同样也乐意把主观和客观同一化。只要一否定这种同一化,他的整个体系便垮台:首先是他的空间论和时间论,其次是偶然性是实在的这个信念,然后是他对理智的谴责,最后是他对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解释。
当然,柏格森的哲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或许是他的大部分声望所系的那一部分,不依据议论,所以也无法凭议论把它推翻。
他对世界的富于想像的描绘,看成是一种诗意作品,基本上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莎士比亚说生命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雪莱说生命像是一个多彩玻璃的圆屋顶,柏格森说生命是一个炮弹,它炸裂成的各部分又是一些炮弹。假若你比较喜欢柏格森的比喻,那也完全正当。
柏格森希望世界上实现的善是为行动而行动。一切纯粹沉思他都称之为“作梦”
,并且用一连串不客气的形容词来责斥,说这是静态的、柏拉图式的、数学的、逻辑的、理智的。
那些对行动要达到的目的想望有些预见的人,他这样告诉人
419
814卷三 近代哲学
家:目的预见到了也没有什么新鲜,因为愿望和记忆一样,也跟它的对象看成是同一的。因而,在行动上我们注定要做本能的盲目奴隶:生命力从后面不休止、不间断地推我们向前。
我们在沉思洞察的瞬间,超脱了动物生命,认识到把人从禽兽生活中挽救出来的较伟大的目标;可是在此种哲学中,这样的瞬间没有容留余地。那些觉得无目的的活动是充分的善的人,在柏格森的书里会找到关于宇宙的赏心悦目的描绘。
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假如要行动有什么价值,行动必须出于某种梦想、出于某种富于想像的预示,预示一个不像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那么痛苦、那么不公道、那么充满斗争的世界;一句话,有些人的行动是建筑在沉思上的,那些人在此种哲学中会丝毫找不到他们所寻求的东西,不会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它正确而感觉遗憾。
第二十九章 威廉。詹姆士
威廉。詹姆士(WiliamJames,1842—1910)基本上是个心理学家,但由于以下两点理由而在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创造了他称之为“彻底经验论”的学说;他是名叫“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这种理论的三大倡导者之一。他在晚年为美国哲学的公认领袖,这是他当之无愧的。他因为研究医学,从而又探讨心理学;1890年出版的他在心理学方面
420
第二篇 从卢梭到现代914
的巨著①优秀无比。
不过,这本书是科学上的贡献而不是哲学上的贡献,所以我不准备讨论。
威廉。詹姆士的哲学兴趣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的一面,另一面是宗教一面。在科学的一面上,他对医学的研究使他的思想带上了唯物主义的倾向,不过这种倾向被他的宗教情绪抑制住了。他的宗教感情非常新教徒气味,非常有民主精神,非常富于人情的温暖。
他根本不肯追随他的弟弟亨利,抱吹毛求疵的势利态度。他曾说:“据人讲魔王是一位绅士,这倒难保不是,但是天地之神无论是什么,它决不可能是绅士。”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意见。
詹姆士因为温厚热情,有一副给人好感的气质,几乎普遍为人所爱戴。我所知道的唯一对他毫不爱慕的人就是桑塔雅那,威廉。詹姆士曾把他的博士论文说成是“腐败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