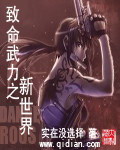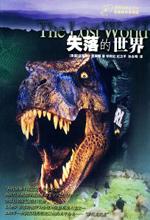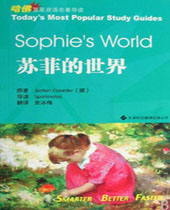世界伟大考古纪实报告之三破译的圣经-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认识的文字的碎砖头。
正当博塔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懊丧的时候,却有一个当地人跑来告诉他,说自己是来帮助博塔的,因为在他住的村子附近——个叫做科尔沙巴德的地方——就有许多刻有铭文的砖块,从古到今,村里的人都用这样的砖来砌炉灶。博塔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决定派几个助手去那个当地人所说的地方试试运气。一周以后,一个助手急急忙忙地从科尔沙巴德回来报告,说是当他们刚刚在那里挖下第一铲土时,一段墙壁就显露出来了,随后他们把墙壁清理了出来,竟看到上面有许多的图画与雕刻,在墙壁的附近还发现了石雕。
博塔马上带着留在身边的所有助手,动身前往十几公里以外的科尔沙巴德。博塔到达目的地以后,看见了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的图像——从蓄胡须的男子,到有翅膀的野兽——不仅与自己在埃及看到的图像完全两样,而且也与欧洲在当时发现的图像毫不相同。继续挖掘的结果表明,这个遗址就是一座亚述王宫。于是博塔断定自己发现了尼尼微,并迅速向国内报告,巴黎报界公布了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整个欧洲的轰动。因为这无疑证明了《圣经》所言,的确有一种与埃及文化同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的文化,曾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存在过。
为了使欧洲人能够亲眼目睹这一考古学上的巨大发现,博塔准备把一些石头雕像运回巴黎。开始,博塔打算用木筏沿河而下,将这些雕像运到底格里斯河的下游,然后再由海路运往欧洲。可是,装载着沉重的石头雕像的木筏,在湍急的河水中急速地旋转着,不久便沉没了,所有那些刚刚才重见天日的雕像,也都沉到了河底,又一次消失在世人的眼前。博塔在心痛之余,重新整理选择好一批石头雕像,先用大车将这些雕像运到底格里斯河的下游,然后顺利地装上了三桅船。几个月以后,在巴黎的卢浮宫展出了这些石头雕像,它们向世人默默地述说着历史上的亚述文化。
在法国人博塔宣布发现尼尼微稍后不久,英国人莱尔德来到当地人传说中由宁录亲手奠基的一座古城遗址进行挖掘。莱尔德在发掘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沿着一道挖得很粗糙的土台阶往下走,来到地下约6米的地方,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对人头飞狮之间。这些人头飞狮不是随随便便雕刻而成的,而是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最能表现睿智的无过于人头,最能表现威力的无过于狮子,最能表现速度的无过于鸟翼,人头飞狮代表着神的智慧、权威与迅猛。
我们从人头飞狮中间走过去,步入王宫大厅的遗址。我们两边都是巨大的有翼人像。有的人像的头部是一个鹰头,而有的人像则完全是人形,这些人像手里都拿着神秘的象征物。我们能够在这大厅墙壁上的壁画中,看到由一排排的祭司簇拥着的国王,还有手执枞树球果和法器的有翼人像,似乎在神树之前进行礼拜。在大厅周围的房间里面,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奇妙雕像与墙壁上的奇特铭文。面对这一切,我们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或者是亲眼目睹了东方的传奇。
为了证实自己所看到的不是幻影,而是完完全全的真实,莱尔德回到了地面上,眺望着近在咫尺的高高耸起的一个金字塔形的土丘——这是希腊古代的历史学家色诺芬在他的《万人进军》书中所描写过的阶梯型金字塔,当年曾经有一万名士兵在上面驻扎。这时候,莱尔德决定继续挖掘,用事实来证明自己才是尼尼微的真正发现者!于是,莱尔德来到库云吉克土丘,要在这个当年博塔曾经挖掘过,然而结果却是徒劳无功的地方,重新开始发掘。这一次,莱尔德成功了,在库云吉克土丘的泥土下面大约6米的深处,他挖掘出了尼尼微最大的亚述王宫。
这是亚述国王西那克里布的王宫,这位亚述王国的君主是以嗜杀在历史上著称的。正是他在公元前689年毁灭了巴比伦城:在强攻入城以后,他的军队见人就杀,所有的街道都让尸体给塞住了,并且把城中所有的建筑——从私人住宅到祭祀神庙——都统统拆毁,最后将亚拉奇都运河中的河水灌入整个城市,使巴比伦城陷入一片汪洋;同时,他还下令要让巴比伦,这个比尼尼微更加古老的城市,也就是《圣经》中提到的巴别,完全从地球上消失。为了履行他的这一命令,士兵们将巴比伦大地上的泥土,用船尽量运走,然后丢弃在荒漠之中,任其随风飘散。这位君主的残暴与狂妄,在他留下的一段铭文中得到了最好的表现:“往四周瞧瞧,就能发现世人都是傻瓜!”
可以说,莱尔德才算是真正与完整地发现了尼尼微。因为他通过对亚述王国最大王宫的挖掘,证实了尼尼微曾经的确是亚述王朝的都城。更为重要的是,后来由莱尔德的继任者拉萨姆,在这个王宫里面又发现了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一共收藏有将近3 块写满了楔形文字的泥版。在这些泥版上面,不仅记载着亚述王朝的世系表、史事札记、期廷敕令,而且还保存着神话、歌谣、颂诗等等。在神话之中,就有被现代文学史家称之为“史诗的元祖”的吉尔加美许神话。
1872年,英国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史密斯,开始对拉萨姆送回国的泥版进行翻译,使人们对吉尔加美许神话能够有所了解:在世界创造出来以后,出现了上天之子的乐园,不仅住所修建得富丽堂皇——有各种各样的房屋,包括巨大的粮仓——而且还用高大的城墙将乐园四周都围了起来,上面还有士兵守卫。吉尔加美许就是上天之子中的一个,他是神与人的杰作,三分之二是神的血统,三分之一是人的血统,因而是天生的首领与英雄,成为众人的统治者与崇拜对象。为了追求永生,吉尔加美许遇见了人类的始祖乌特一纳比西丁,并得知诸神在惩罚邪恶的人类的时候,仅仅只饶过了乌特一纳比西丁一家,并使他的全家获得永生。
史密斯一边紧张地翻译,一边越来越兴奋,因为这些创世神话,与《圣经》中描写的创世过程竟然如此地相似。可惜的是,拉萨姆送回来的泥版,却突然中断了。史密斯为此坐卧不安,最后,他在伦敦《每日电讯报》的资助下,飘洋过海来到库云吉克上丘,独自一人在堆积如山的泥土石块之中,苦苦地寻觅那些可能存在的泥版。也许是史密斯的执着最终感动了上帝,终于出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史密斯居然找到了包括吉尔加美许神话中断部分的那些泥版!
史密斯一共找到了384块残缺不全的泥版,其中记下了诸神用洪水惩罚人类,特别是乌特一纳比西丁一家怎样躲过洪水而死里逃生的故事。显然,《圣经》中的《创世记》,不过是根据吉尔加美许神话里的创世母题所进行的具有民族神话融合特征的宗教性表达。吉尔加美许神话的出现,不只是说明了从《圣经》到《古兰经》这一类宗教经典的神话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有一种更加古老的民族文化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曾经存在过。
至少有一个事实提供了这一文化曾经存在过的证据:无论是在尼尼微出土的泥版,还是在巴比伦出土的泥版,所使用的楔形文字都源于一种更加古老的文字!无论是古波斯文,还是巴比伦文,都不过是这种文字的变体,而且在库云吉克土丘下面挖掘出来的亚述王宫里,还曾经发现了由将近100块泥版组成的一部语言词典,它是在公元前7世纪时编制而成的,专门用于帮助人们学习那种古老的文字,即苏美尔文!既然有苏美尔文这样一种文字存在,那么就应该有使用这种文字的苏美尔人,而这两者对于苏美尔文化来说,都是它曾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出现过的铁证。因此,必须寻找苏美尔人的踪迹。
此时,人们已经根据《圣经》中的提示,成功地发掘出了尼尼微与巴比伦,并发现了亚述人与亚述文化,以及巴比伦人与巴比伦文化;另外,从底格里斯河畔上游的尼尼微,到幼法拉底河中游的巴比伦,城市离大海越来越近,而城市存在的历史则越来越古老。这就表明,很有可能在这两条河流的下游地区,将会发现更为古老的城市,或许那里就是苏美尔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是苏美尔文化的精华荟萃之地。
又是《圣经》提供了寻找的线索:挪亚的儿子闪的后裔,后来第一个与耶和华立约,并改名为亚伯拉罕的亚伯兰,正是出生成长在幼发拉底河下游一个离开大海不远的地方,即迦勒底的吾珥。如果联系到在《创世记》第一章的创世过程中对有关地理环境的描述,再加上从19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进行考古所取得的实际成果,20世纪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寻找苏美尔人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从1927年起,列奥纳德·伍利便开始在吾珥古城的遗址上进行发掘。这次发掘的结果,果然不出人们所料,当年的吾珥,正是苏美尔人的都城!
当列奥纳德·伍利在发掘现场挖掘到离地面大约10米深的地层时,他发现了吾珥王陵。在女王舒伯—亚德的墓室中,曾经进行了活人殉葬,除了女王棺材架的一头一尾各有一具女性的尸骨之外,两旁还并排躺着两行女性的尸骨,而在其中一排女性尸骨的最后,还有一具男性的尸骨。所有女性尸骨都戴着精巧的金头饰,这表明她们身前极有可能是伺候女王的宫女;而在那具男性尸骨的臂骨中还紧紧搂着已经断裂的、装饰着黄金与天青石的乐器,显然,他曾经是一位宫廷乐师。对于这一活人殉葬的古代现象,列奥纳德·伍利的结论是:“已知的铭文中没有一处提到过类似的殉葬,这种仪式的消失正可以说明吾珥王陵是多么的古老。”
在列奥纳德·伍利发掘出来的不计其数的文物之中,有两件最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苏美尔女王舒伯—亚德的头饰与上面有镶嵌图案的吾珥旗标。
女王的头饰是由蓬松的假发与三个用天青石和玛瑙制作的花环组合而成的,最上面的那个花环装饰有直立的金柳叶与下垂的金花,中间的那个花环则装饰有上扬的金榉树叶,而在最下面的那个花环上又装饰有悬挂的金环;并且,在假发头饰上还插着五齿梳,上面点缀着金花及天青石。此外,在女王头饰的旁边,还发现了螺旋线状的金丝发带,与半月形的大大的金耳环。由此可见,在女王生活着的公元前4世纪,苏美尔人在制作工艺手饰方面的能力,已经达到了非比寻常的高度,它显示出了苏美尔文化的高度发达水平。
如果说女王的头饰只是从个人生活方面来对苏美尔文化的高度发达进行了证明的话,那么,吾珥旗标则是从社会生活的方面来予以了证明。吾珥旗标由两块各自长为55.8厘米,宽为27.94厘米的长方形木板拼合而成,在一端还装有两个三角形的旗尾,是在游行集会时使用的,约制作于公元前4世纪。在这个旗标上面有三组平行排列的图案,是用珍珠贝壳与海螺壳制成的人像,每个图案之间用天青石镶嵌成的线条隔开,用沥青固定在木板上。最上面的图案是一个盛大宴会的场面,中间的图案是一个凯旋归来的场景,最下面的图案是一个战车奔驰的场面。
所有这一切,都在表明苏美尔人的文化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民族文化。吾珥旗标,不仅使人们能通过看到参加宴会的苏美尔人穿着的服饰和使用的器具,来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使人们能够通过看到进行战斗的苏美尔人身上的盔甲及其使用的武器,来了解他们的作战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使人们能够看到激烈征战的苏美尔人驾驭的战车与飞奔的战马,并由此来了解他们的战争艺术。如果对吾珥旗标进行完整的把握,实际上就像是一部关于苏美尔文化的历史性电影巨片的三个带有连续性的片断:战争、胜利、和平。
由此可见,以战争来争取和平,已经成为6000年以前苏美尔人的生存信条,并以战车的传承为标记,从近到远地直接影响着其后的民族文化的兴起与衰落。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曾经连绵不绝地响起过隆隆的因战车滚动碾压大地而发出的巨大征战之声:马其顿帝国的战车颠覆了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战车颠覆了亚述王朝,亚述王朝的战车颠覆了巴比伦王国,巴比伦王国的战车颠覆了……可惜的是,现存的历史并没有告诉人们,是巴比伦王国的战车颠覆了苏美尔王国!
然而,连绵不断的帝王征战,却形成了一个烽烟四起、生灵涂炭、文化急剧衰亡的漫长历史过程,整个战争的历史又提示人们:沿着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湖流而上,滚滚而来的战车洪流,曾经像河中的洪水波涛一样,一浪接一浪地横扫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位于两河流域下游方向的苏美尔王国以及苏美尔人,却全都突然地消失了,历史究竟要向现在的人们隐瞒些什么呢?
Ⅱ.08 谜底在金字塔之外
人们一般总是从两个方向来追寻远古的历史,一个方向是沿着众多神话提供的线索来进行追踪,根据神话母题来演示历史的流逝,因而人类有了神的历史渊源;一个方向则是沿着文化典籍展示的轨迹来进行跟踪,根据文明的更迭来描述历史的进程,因而人类有了人的历史发展。因此,各种各样的考古成果,往往不是证明了神的预言,就是证实了人的假想。事实上,所有从人类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其意义主要就在于:对远古历史空缺能够进行某种形式的填补。也许不少文物的确能够发挥连接历史片断的作用,而更多的文物则只是标示着历史片断的现实存在,从而留下一派历史的蒙胧,甚至历史的神秘。
几乎所有的发掘成果都在证实,苏美尔人是最先进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古代民族,因为他们是来自远方的黑发种族,在他们带来的石碑上的铭文中,自称为“黑头”。自从来到这个厚积着两条大河携带来的肥沃泥土的三角洲上重新立国,苏美尔人就发现既没有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