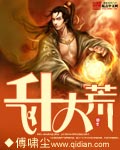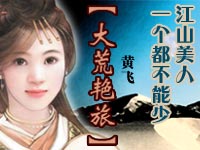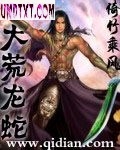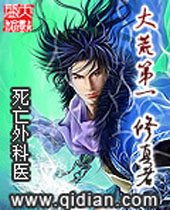吞吐大荒-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亲呢?悲鸿说,他不在。这个人就走了。等悲鸿父亲回来,问他有人来吗?悲鸿答:有人来的。他姓什么叫什么,悲鸿都答不出来。父亲就骂他,你这个孩子,一点不懂事。悲鸿笑笑,把手摊开。手心里画的人与来访父亲的人一模一样。
“悲鸿家隔壁邻居的老太太死掉了,家人在哭。为什么哭呢?生前没有给老太太拍个照片。悲鸿听见了,他说,不要紧,我来我来。他就画了一个老太太在河边洗衣裳。一看悲鸿画的老太太的样子,老太太的儿子说,这是我的母亲嘛,你怎么画出来的呢?悲鸿说,我经常看到她在河边洗衣服,我看见过她的样子,我就画了送过来了。
“还有一次,悲鸿父亲出去,关照悲鸿要好好读书。他等父亲一走,马上就叫许多学生来让他画,将这些学生的面孔画成小生、老生。悲鸿叫一个学生看门,当心他父亲回来。他父亲回来了,这个小孩子回来说,来了,先生来了!大家吓得不得了。大家脸上都画着大花脸。悲鸿父亲很生气,我走了,你就这种样子。回头一看,悲鸿把这些人画得真好,小生、老生都画得很好。
“悲鸿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有天才。从此以后,就教他画画。”
可见,像天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徐达章,这位普通的私塾先生,想让自己心爱的儿子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前程,而这几件小事,最早让父亲看到了儿子潜藏的慧根。徐达章无疑是徐悲鸿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一九○五年,十岁的徐悲鸿跟着父亲走江湖,乘船到附近的乡镇。父亲画画,儿子诗兴大发,写下一首五言绝句:“春水绿弥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风信好,舟过万重峦。”这诗出自一个少年之口,叫乡里乡亲们刮目相看。
二○○五年三月的一个上午,在南京徐悲鸿侄女徐泳雪家,她拿出不轻易示人的一卷画轴给我看。上面是徐悲鸿抄录的这首十岁诗。徐悲鸿写道:“先君率我过西至溧阳舟中小诗,忽忽三十余年 录此安弟丙子元月 悲鸿”
时隔三十二年,徐悲鸿之所以偏爱他的十岁诗,记得一字不漏,这是他对于少年生活的一种怀念,也是他给父亲交的一篇作业。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徐悲鸿时年十七岁,虽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但他消瘦的肩头却是沉重的。支撑全家生计的徐达章积劳成疾,病倒在床。徐悲鸿接过了养家的担子,他到宜兴县初级女子师范、始齐小学、彭城中学应聘国画教师,都被录取了。他同时兼职,谋得三份薪水补贴家用。他的一技之长,在徐家最无奈的关头,又撑起一片天。
人生的第一个机遇也就出现在这一年。
当时,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临近上海的江南地区得风气之先,人们手中居然有了报纸。一天,少年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性情之下,斗胆给报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大作。画题有趣,描绘了《水浒传》的一个角色,也是一出乡村舞台的戏剧画面:《时迁偷鸡》。
《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清末秀才,一位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老先生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偶尔翻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蛮有趣,画中的人物仿佛从《水浒传》跳到了农家的门前,乡土气息浓郁,姿态夸张而鲜活生动,竟然爱不释手,大笔一挥,给了二等奖。
这个小小奖项,在徐悲鸿一生诸多荣誉中微不足道,但它却似残夜的一道光,点亮了无名者的才华,给了这位乡村少年征服天下的极大自信。
尽管民国了,剪了辫子,父母包办的婚俗并没变。十七岁的徐悲鸿也订婚了,对方是一个未曾见面的农家女。他曾逃离家乡,徐达章抱病外出寻找,硬把他拽回家完婚。徐悲鸿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劫生,似乎饱含着他的痛苦与愤懑。
不过,在家境贫寒的徐家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长子能娶上媳妇,善莫大焉。而徐悲鸿的儿子出生,使得徐家有了第一个孙子,传宗接代有望。徐悲鸿父母做了爷爷奶奶,自然非常满足。徐达章给孙子改名吉生。
一个劫生,一个吉生,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对徐悲鸿的第一次婚姻,最了解的莫过于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老人道出当年那对怨偶毫无感情的原因所在:“徐悲鸿十七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了一个姓周的老婆,徐悲鸿为什么嫌她呢?嫌她小脚,不识字,不懂事。”
徐悲鸿反抗旧式婚姻的尝试失败了。而他对父亲的不满,似乎随着两年后父亲的病逝,一起消散了。徐达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带着人生遗憾撒手人寰,惟一安慰就是他的儿子。儿子是父亲最好的作品。
父亲教给他的不只是画技,还有中国人历代承传的道德与人品。尽管他后来求学西方,但他尊奉的私塾教诲,就像他晚年喜欢穿的中式长袍,言谈举止间无处不在,甚至影响到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直至后来的人生轨迹。
他要带着父亲的灵魂,外出闯荡。
二 千里良驹
一九一三年深秋,十八岁的徐悲鸿毅然离开宜兴故乡,再次投奔他心目中的福地——大上海。他在内心里感到了那座中国最大都市对他的召唤。尤其是《申报》多次登出广告,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并正式招生:“专授各种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板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讲义明显,范本精良,无论已习未习,均可报名。”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三个闯荡上海的年轻人在聚餐,摩拳擦掌地谋划生存大计。挑头的人叫邬始光,二十七岁,另外两个小兄弟,是十七岁的刘海粟与十九岁的汪亚尘。刘海粟原名刘,取意苏轼《前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更名海粟。汪亚尘原名汪松年,以“亚洲之尘”自诩,改名亚尘。
此时,一改中国画拜师求艺的传统做法,集体授课的美术学校已草创多处。官办的,有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国画手工科,教师是赴日习画回国的郑锦。私立的,有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主持人是学过英文与西洋画的周湘。而邬始光与刘海粟就是周湘的门徒,而汪亚尘早年喜爱绘画,后跟随浙江同乡邬始光学画。
这三个美术青年从日本料理店的后窗看出去时,不约而同地看到一张出租告示,贴在对面弄堂的墙上。他们兴奋地嚷嚷,吃过饭,就去租那间房子。因为他们谈论如何在上海立足,不如筹办一所传授绘画技艺的学校。于是,那间房子就成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地址:上海美租界乍浦路8号洋房。
一身乡土味的徐悲鸿,走进上海美租界乍浦路8号洋房。他交了半年学费十八元,外加膳宿费三十元。这笔钱对于他,绝对是个大数字。然而,他失望了。虽然名称好听,却不过几间租的房子,空空如也。仅有几位敢上讲台的,只是略知一二的初学者。他气愤的是,他画的几幅画竟被拿去,当了学校教材。
于是,他在一个夜晚不告而别。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懂得绝不能误人子弟,老师就得善待学生,这成为他的终生信条。
若干年后,徐悲鸿已是画坛翘楚,一个名叫曾今可的评论家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会序》中提到“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徐悲鸿当即在《申报》发表启事,说当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纯粹野鸡学校”:“今有曾某为一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刘海粟在《申报》反唇相讥:“美专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能以爱恶生死之。”他嘲讽徐悲鸿自命“艺术绅士”。
但刘海粟的回击,激起徐悲鸿的更大反感。《申报》新发《徐悲鸿启事》毫不客气:“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过。(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极为罕见的勃然大怒。
对于轰动沪宁的这一场笔墨官司,拥护徐悲鸿与拥护刘海粟的人,各执一词,有不同解读。其实很简单,这两位大师立身为人的个性不同。在徐悲鸿看来,对于一个学校而言,学生有没有教材之类,并不是什么大事。而对于一个学生,尤其是家境困苦的学生,根本学不到东西,等于一次被骗的经历。
作为一个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刘海粟则是另一种心态。后来邬始光退出,由刘海粟接手,继续主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又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的定语是“野鸡学校”,刘海粟却看作是以后上海美专的起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教水彩画与函授的汪亚尘深感愧疚,“误人误己,两不相宜”。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那时自己瞎画,还要用现在望平街一带还留着的擦笔画做范本,去教学生,连讲义都写不清楚,真是害人!”他不愿“莫名其妙地干下去”,自己赴日学画,还写信劝刘海粟也出国看看。他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教,又创办新华师范学校,亦为著名画家,培育人才无数,也是徐悲鸿终生挚友。
一九一五年,回到宜兴的徐悲鸿并没有放弃做一个画家的理想,他还得走出去。一个在上海当教授的同乡回来探亲,看到他的绘画出众大为赞叹,一口答应帮他找份工作,他便再次辞职,去上海寻找人生出路。
徜徉在黄浦江边的徐悲鸿,少年老成,踌躇满志。他的背囊里揣着砚台、毛笔和他的书画之作,长衫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除了几枚借来的银元,还有两枚自己亲手篆刻的方章,一枚曰“神州少年”,另一枚为“江南贫侠”。
怀抱幻想的青年贫侠,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苍凉。那个当教授的同乡虽然答应帮他找份工作,而且给当时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写了介绍信,李校长也答应可以考虑,谁知考虑的结果却是拒绝。其他的出路没个头绪,宜兴老家又来人捎信,说他媳妇得了病,叫他赶快回去探望。他匆匆赶回老家一趟,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说:“徐悲鸿回到家,他的妈妈陪媳妇到外面去看病了,不在家里。徐悲鸿买了一件皮背心带回去,和三十块钱摆在一起,他关照家里人说:我实在不能够等,有急事得到上海,我马上回去了,皮背心给老婆暖暖心,三十块钱给她去看病吧。以后徐悲鸿就回到上海,没有多少时候,他媳妇就病死了。”
乡村妻子病故不久,儿子劫生也因天花而去世。一年之间,徐悲鸿失去了他最亲近的父亲,也失去了虽然没有任何感情,却能给母亲带来安慰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儿子。尤其是失去父亲在艺术上的指教,让这位年轻人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无尽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的名字徐寿康改名为徐悲鸿,浪漫地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悲哀的孤雁,决心要穿越茫茫长空。
再来上海的徐悲鸿,抱着最后的希望在街头奔走,依然四处碰壁。上海滩如此之大,却没人愿意收留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黄警顽。这个与他素不相识的热心人,在他走投无路的倒霉关头,拉了他一把。
黄警顽说:“当时徐悲鸿穿了件蓝竹布长衫,对分的头发披拂在前额,手里拿着个纸卷儿,年龄同我仿佛,约二十多岁,但有些瘦弱抑郁。他经熟人介绍,到商务印书馆找《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我代他打电话给恽铁樵的。徐悲鸿回来告诉我:‘商务出版教科书画插图,恽先生说,我的人物画得比别人好,十之七八没问题。’
“过了几天,发行所刚下排门,徐悲鸿就带着满脸沮丧、憔悴的神情走进店堂,说是情况有变,人家不同意让他画,他难受地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只有你一个朋友,永别了!’说完,他快步走出门去。
“最初我还不很介意,过后一想:糟了!他不会去自杀吧?我感情一冲动,连假也没有请,就跟了出去,由四马路向外滩赶去,怕迟了会出事。我在外滩找了好久,才在新关码头附近找到了他。他正在码头上不安地来回走着,连我走近他身边都没有发觉。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膀说:‘你想干什么?书呆子!’徐悲鸿一看是我,禁不住掉下泪来。我们俩抱头大哭,招引好些人围着看。徐悲鸿头脑清醒了,听从了我的话,跟我回发行所。
“在路上,徐悲鸿告诉我,他因欠了旅馆四天房钱,老板在两天前就不许他继续住宿,并把箱子扣下了,铺盖已经当掉,他没有地方容身,只好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过夜,还常常受到巡捕的驱逐。昨夜通宵风雨,他饥寒交迫,想马上自杀,但想到我多次诚恳招待他,这才来向我告别。如果我不赶上去,很难说他最后怎样安排自己。
“我的人缘不错,就跟一个房间的同事和门房商量,让他晚上同我们住宿。我俩睡一张单人床,盖一条薄被子。伙食这样解决:中午他到发行所楼上饭堂,坐在我的位子上跟同事一桌吃。我熟人多,轮流上朋友那里吃。早点和晚饭呢,我每天给他一角钱,也就过去了。徐悲鸿每天到发行所店堂,看美术书籍,也看翻译小说。”
当徐悲鸿给一个宜兴同乡送画时,又结识了吴兴书画收藏家黄震之。黄震之把一间棋牌室借给他栖身作画,不过和他约定,只能在他们不打牌时暂用。即便如此,对徐悲鸿也是雪中送炭。他后来曾用名“黄扶”,以示他对两个黄姓友人的感激。
黄震之后来做生意破产,但徐悲鸿没忘记他。人们在以后出版的徐悲鸿画册中,可以看到一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