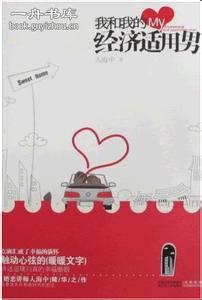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得到钱财以后怎样去花钱和存钱。他们需要一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新型道德观,因为他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根据地位确定义务的社会里,而是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义务是根据合同确定的,一般说来是根据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确定的。因而,一个迄今一直极其诚实的社会可能会变得极不诚实,直至人们懂得,为了履行以钱来表示的合同,对一个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都必须诚实地提供劳务或货物方面的服务。还必须有新的价值观;人们不再尊重原来优越的地位;首领、叔伯祖父和长者不再得到人们自动的服从。领导力量可能转向其他方面,新的领导人要得到或者应该得到像对老领导那样的尊敬恐怕要过很长的时间。旧道德的没落是经济变革中的一个比较痛苦的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道德家和人类学家通常反对变革,或是至少反对迅速变革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迅速变革会促使老的信仰和制度解体,其速度要比建立取代它们的新的信仰和制度的速度来得快。现在另一个引起人们很大注意的不协调的例子是,经济增长开始后不久出现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人口增加(当经济衰退伴有人口下降时同样是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出生率和死亡率均高,两者大致相等。当经济开始增长时,死亡率开始下降;起初仅仅是因为通讯联络的发展和贸易额的增长使得局部的饥荒得到控制,以后是因为公共卫生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下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出生率才开始下降。在此期间,人口可能会在30年至60年内翻一番。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认识到,如果他们要控制死亡率,他们也必须控制出生率(我们将在第六章再论述这个题目)。
面对变化的不协调现象,许多人在问是否能以“平衡”的方式,即防止某些信仰和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变得快来对社会变革进行调节。答案看来是,这是不可能的。一种文化的众多方面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以同样比例发生变化。一些方面感受到的压力比别的方面大,于是便发生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拉着别的方面一起变化,我们不可能总是预计到什么先变化,因为这在各个社会因其历史和传统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同样不可能预计到文化的哪些方面会被拉着一起变化,或者以什么比例变化。防止变化不平衡的唯一办法就是防止一切变化,但这是谁也无法办到的。
当然,虽然我们不能预见因任何特定事件而产生的所有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对变化的进程施加任何影响。例如,我们知道,工业化过去曾在许多国家造成城市贫民窟;但是我们也知道,如若采用适当的城市规划措施,实行工业化而不产生贫民窟也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在其他一些地方,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大批劳动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然后又倒流回去;我们知道,这种现象也是能够控制和杜绝的〔第四章第三节(三)〕。更加难以预测的是,人们对下列问题的态度会有什么变化,比如家庭关系,对待部族权威的尊重,宗教仪式或者合同义务的神圣性。一些人担心的是,旧的道德价值观随着经济增长的新酒倒入社会稳定的旧瓶而化为乌有。旧的关系瓦解到何种地步大概部分地取决于发展是如何主持的。如果这种发展是由蔑视老的政治,宗教和家族领导人的外国资本家和政府主持的,那么这种发展将会比由已经确立的领导人主持的发展更加迅速和有效地破坏现行权力结构。有时有人说,日本人改造西方资本主义,使之适应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这是不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是令人怀疑的。事实是,日本业已存在的领导集团主持的资本主义,使新的方式和旧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减至最低限度。当经济增长从阶级意义上讲最少革命性时,亦即当新的企业领导人得到老的政界、宗教界和社会领导阶层承认和赞助时,从它对人的态度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来说,它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也最少。这也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的巨大差别之所在。在亚洲,旧的宗教和政治制度要比非洲稳固,没有为西方的影响所彻底摧毁。而在非洲,欧洲的资本家和政府对既定惯例、宗教和生活方式,只要它们与欧洲人的利益相悖,就采取反对的行动或者采取蔑视的态度,其结果则是更大范围的土崩瓦解。
制度一旦开始发生变化,就会越变越厉害。旧的信仰和关系改变了,新的信仰和制度渐渐变得相互一致起来,并朝着同一方向进一步变化。尽管这样,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经济增长一旦开始,会永远继续下去;经济衰退一旦开始,便永远制止不了。
首先,一切增长往往有其规律性,这就是说,它开始时缓慢,逐渐加速,然后又放慢下来。这是因为刺激增长的每个因素最终都会接近极限。可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当收音机问世时,公众并不了解它们可能的用途,疑心重重;最初只销售几台,可是收音机逐渐变得很受欢迎,很快就像热饼一样抢手。但是在每家都有一台收音机时,销售额差不多便到了极限。一旦到了这个极限,销售额的增长率便陡然下降。第二年销售额可能增加一倍,第三年增加两倍,第四年增加三倍,但是不能永远每年都增加一倍,因为根本没有那样多的人。制度的变化也是这样。当提出某种新的原则时,它首先遭到反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原则会受到欢迎,人们开始热情地将其应用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去。但是必定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届时这个原则垄断了几乎能应用的一切有关领域。经济增长是对连续不断的刺激的反应,而每个刺激最终会达到极限。因此,持续稳定的增长只有偶然在新刺激的产生始终正好接上旧刺激的消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际上,我们能够指望的最好的情况不是一种稳定的增长率,而是由相对平静时期分隔开的连续的增长高潮。
但是,经验表明,即使是有节奏的增长也可能会终止。有些社会表明,在经济出现强有力的增长之后会出现停滞和下降——甚至下降到一无所剩的地步。增长之后可能呈现停滞,正像停滞之后可能出现增长一样。历史上也有增长加速和减速的转折点。对动态进程所进行的各项调查表明,人们最感兴趣的是转折点。因为紧接转折点之后出现的累积过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研究这些转折点给予极大的注意。
让我们先来谈谈加速问题。我们业已阐明,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抓住机会。因此,加速增长或者是由于产生了新的机会,或者是由于制度的变化使人们现在可以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由于上述两个原因。
新的机会也许是多种多样的。新的发明可能会创造新的商品,或者降低生产老商品的成本。新的公路,新的海上航线或者交通运输方面的其他改善都可能为开拓贸易创造新的机会。战争或通货膨胀可能造成新的需求。外国人可能来到一个国家,开展新的贸易,投资新的资本,或者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样一些新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现行制度之外的。情况未必完全如此,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章里研究制度对于创造发明率或外国资本流入数量等问题的影响。然而由于这些问题不是有赖于一国的制度,所以可能出现更多的机会,其原因与制度的变化无关,而机会的增多将会引起制度的变化。
也有可能在基本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发生变化,使行动自由增大。一种可能的、但是不常见的情况是,统治者改变主意,准许人民以先前严禁的方式进行活动。较为可能的情况是,国家受到某种冲击,诸如发生战争、饥荒、飓风、地震、瘟疫或其他灾难之后政权发生变化。这样的冲击有时会削弱喜欢保持现状的统治集团的控制,从而使权力落入锐意变革的人的手中。
因此,经济加速增长或者是由于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创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机会;或许是由于制度发生了变化,为抓住机会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实际上,加速增长的转折点通常同这两种变化都有关。经济状况已变得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大概是因为外贸的机会越来越多,而这又加强了那些希望朝着允许扩大自由的方向进行制度改革的人的力量。
革新者始终是少数。新思想最初总是由一、两个人或极少数人付诸实施的,不管是技术方面的新思想、还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商品或其它新生事物都是如此。这些新思想也许会很快就被其余的人所接受。然而更可能的是它们遭到怀疑和不信任,因此,即使有所进展,最初的进展也只能是很缓慢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新思想被认为是成功的,那时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此,经常有人说,改革是精英们的事,或者说,改革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某个社会领导人的素质。如果这种说法的含义仅仅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是革新者,而只是仿效别人所做的事情,那么,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如果认为这种说法的含义是所有这些新思想均为某个具体的阶级或集团所掌握,那就多少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每个革新者都是单个的人,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也许是先进的,然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又是同样反动的;他们同其他革新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是在阶级和亲属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都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有时有这样一种情况:革新者形成一个单独的群体,或者至少不得不成为一个意识到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因为他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障碍使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进行自卫或发起进攻。新思想最初并不是在任何一个阶级中产生的,但是,提倡者们很可能会发现,由于社会对他们的革新所进行的抵制,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
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比较富有成效的观察结果之一是概括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转折时刻进行改革时期最重要作用的是“新人”。这意味着,在那些抓住新机会或实行增加行动自由的制度改革的人中,很少发现是过去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时的统治阶级。首先,统治阶级通常满足于现状;他们不需要寻找新机会。只有那些对现行制度感到失望的人才寻找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实现他们的抱负的其它途径。同时,提倡改革的人既不是居于社会结构最上层的人物,也不是处于底层的人。处于底层的人可能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种姓制度中受煎熬,没有能力去抓住新机会;或者说他们可能太穷,太缺乏教育,缺乏勇气和传统的进取心。因此,新人来自社会的中间阶级,也许十分接近上层,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一定的个人自由和一定的活动传统。在日本,1868年出现的那批新人就居于贵族中比较下层的人物,他们对失去过去的特权感到恼火。在西欧,13世纪和14世纪出现的新人过去是农奴或他们的后裔,这些人逃到城市后得到了保护。在非洲,新人是失去了部落特征的人,这些人接受过一点西方的教育,他们再也无法适应部落的老模式。不用说,这种概括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些新人中也许有一、两名过去的贵族,也许还有一、两人来自最底层阶级,因为阶级状况始终会有个别的例外。这种概括只是说绝大多数新人将来自中间阶层。
其次,新机会也许会对现在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提出挑战。它们可能会改变土地的价值,土地是统治阶级财富的基础。新机会也许会对农奴制或奴隶制提出挑战,或者可能通过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把工资提高到使统治阶级感到难堪的程度。因此,统治阶级将对新机会持敌对态度,有可能出现一场权力之争,甚至发展到内战的程度。另一种可能是,新机会并没有在经济上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这是从减少他们财富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但是,最终将在政治上对他们构成威胁,也就是说,随着这些新人逐渐富有起来,他们将要求享有同样的威望和同等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取得妥协,因为统治阶级可能仿效那些新人利用新机会(例如,想一想过去拥有土地的贵族在英国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早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统治阶级还可以用通婚或使一些新人变成贵族的办法同意把一些新人拉进他们的行列。因此,新机会的出现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一场内战;但是,也可以在经过不是那么激烈和残酷的斗争之后达成妥协来实现。
“辉格党”历史学家往往突出革命在实现变革中的作用,而“托利党”历史学家却贬低革命的作用。辉格党认为,看来变革的高潮必然是革命——就像鸡蛋破裂孵出小鸡或蝶蛹破裂飞出蝴蝶一样。另方面,托利党指出,许多根本性改革是在没有爆发内战的情况下实现的。老的统治阶级可能采纳新思想,因此可能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者他们可能同新人妥协,把新人纳入老的统治阶级的行列。如果发生革命,那也要在新人崭露头角以后很久——也许要过好几个世纪——才会出现;因为只有当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和牢牢地站住脚跟以致能控制足够的武装部队来反对和击败政府时才能发生革命。到这个时候,他们谋求的绝大部分权利早就得到了。然而,这些说法是言过其实了。
这些说法完全适用于英国内战、法国革命或者美国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独立战争,因为无论如何这些革命所确立的观点即使在未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可能已被接受。但是,它们却不适用于海地革命、日本的维新、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20世纪欧洲和拉美相继发生的使独裁者掌权的起义。有些革命也许是“不必要的”,因此历史似乎顺应了它们的潮流;但是,另一些革命是同过去彻底决裂,甚至扭转了过去的趋势。
另一种观点认为,市民在使经济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