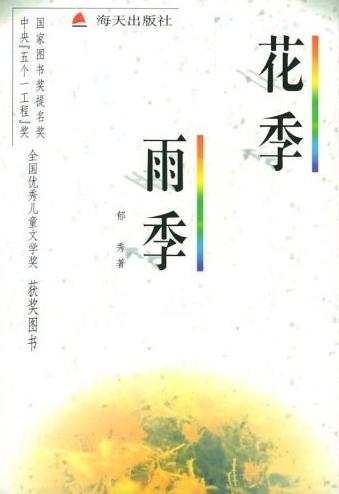风城雨季-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常征夹起一个虾球,不咸不淡道:“Shut up。”
店里生意最忙的时候,门口来了几个警察,食客们起初并没在意,直到后厨里起了喧哗。陶郁一脸惊惶地从后面窜出来,一眼看到餐馆正门外的警察,知道前后门都被堵了,情急之下慌了神。
常征和朋友正准备买单,见他一脸悲愤,常征起身问:“出什么事了?”
“查……查身份……”陶郁这阵子听同事们聊过,很清楚打黑工被抓就一个后果——遣送。
常征看了一眼前门的警察,趁没人注意这边,推着陶郁闪身进了洗手间,顺手别上门。
“脱衣服!”
陶郁:“……”
眼见对方三下五除二扒下T恤,陶郁有点发懵,人家谍中谍里为躲避追捕上演个亲嘴就是了,这脱衣服是要干嘛?常医生身材不错……他假装镇定地瞄了一眼,随即又唾弃自己,他妈的身材好就能在公共场所干这事?!
“美国抓黑工的警察,管不管扫黄……”陶郁支支吾吾问。
常征愣了一下,把手里的T恤甩到他脸上,低声道:“想什么呢?!让你跟我换衣服!”
“啊?哦!”陶郁总算反应过来,常征是公民可以随便打工,人家堂堂一个医生休息时间来端盘子,警察管得着吗。
从厕所出来,陶郁强自镇定目不斜视地走到常征那桌坐下,同桌的朋友拖着下巴皮笑肉不笑地看了他一会儿,伸出手道:“你好,我是Tony。”
“陶郁。”心不在焉地跟对方握手,陶郁眼角瞟着餐馆里的警察。
换上工作制服的常征走过来,白衬衫在他身上略显狭窄,他把一个黑本子放到陶郁面前,用对病人开医嘱的语气说:“这是您的账单。”
陶郁张口结舌地看着对方,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欲哭无泪地想人家帮了个大忙,就当请一顿饭答谢了。翻开夹子看了一眼账单,他恋恋不舍地从兜里掏出五十美元,有气无力地说:“告诉收银的,用现金给我打九折。”
常征看了陶郁一眼,要笑不笑地把钱收进夹子里,转身走了。
第三章
陶郁失业了。
经过这次突击检查,中国城的餐馆商店都得蛰伏一段时间,不敢在风头上用黑工了。陶郁的老板对他印象不错,给他结了这礼拜的工资后,许诺过一阵再找他。陶郁没有因此而宽心,他还得接着找活,不然手里这点余钱可不够他坐吃山空。
一起打工的一个叫六子的小孩给陶郁介绍了个差事,帮冷库搬猪肉。冷库也在中国城附近,给这些餐馆超市供货,由于出货量大,冷库每天都得补货,而这补货时间一般都在上半夜。
陶郁合计了一下,眼瞅开学了,白天恐怕要上课,上夜班合适,于是当天晚上按照六子给的地址,屁颠屁颠地就去了。
陶郁原本想着自己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干点体力活不算什么,可搬了两个晚上,就觉得浑身僵成了一扇梆硬的死猪肉,爬不起来了。他跟六子发牢骚:“那墨西哥人怎么长的?明明矬得像个土豆,居然力大无比,一手拎一扇排骨跟玩似的!”
六子不以为然道:“老墨都是牲口,以前我跟一装修队干,去雇主家里拆浴缸,老墨连工具都不用,直接抱着晃晃就生拽下来了,那浴缸还是拿水泥砌在地上的呢。”
陶郁乍舌道:“这跟咱们决不能是一个祖宗,这他妈是从犀牛进化的!”
六子“呵呵”笑着,发动那辆比他岁数还大的皇冠,排气管抖得好像拖拉机,顺路送陶郁回家。
“陶哥。”六子说,“你这样的文化人,何必跟我们一样当苦劳力呢?”
陶郁不以为然:“谁说文化人不能干苦劳力,你问问中国城打黑工的,十个有八个是硕士在读,还有两个是念博士的。”
六子一笑道:“能来留学的,家里就没有揭不开锅的,打工就是为了多几个零花钱,洗个菜端个盘子了不得了,像你这样的还真少见。”
陶郁心想,我们家确实没揭不开锅,可是我快揭不开锅了。这话他不愿意跟外人说,总觉得在外面宣扬家里事,甭管好的不好的,都像是敞胸露怀给外人看,不是长脸的事。
“你就当我是行为艺术吧。”他说着指指路边,“我到了,就停这吧,你也早点回家。”
六子开车走了,陶郁双手插兜往唐海南家走,刚走两步听见身后又有发动机的声音,回头一看是常医生下班回来了。陶郁一看表,凌晨四点,唉,同是天涯苦命人。
常征锁好车拎着书包走过来,还没靠近就不自觉地抽了抽鼻子,问:“找到新工作了?”
陶郁点点头。
常征:“不是杀猪吧?”
陶郁:“……”
两人轻手轻脚地回了家,各自洗漱。陶郁倒在沙发上,累得从头到脚没一处是自己的。正在半睡半醒间,感觉到有人动了动他的枕头。
“常医生?”陶郁半眯着眼,迷迷糊糊地问。
“没事,你睡吧。”常征说完,回自己房间关上了门。
陶郁这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中午,醒来时家里另外两人都上班去了。他从沙发上爬起来叠被子,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两张Subway三明治店的代金卡,一张二十美元。
陶郁笑了笑,把两张卡塞进了钱包里。
两天后开学了,再次踏进校园,陶郁莫名生出一种绝地重生的感觉。
本科时他念的是热能与动力工程,听起来跟能源搭边,其实就是修锅炉的。两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对这行业有了更多的了解,申请学校时转成了环境工程,他申的是博士,相当于国内的硕博连读。别以为他是一心向学,申请博士的唯一理由是从第二年起有可能拿到奖学金,念硕士就别想从学校骗钱了。陶郁没钱,出国的钱都是自己上班时挣的,没跟家里要一分。他的钱只够付第一学期学费,努努力打工能把第二学期撑下来,后面的他就指望跟导师混好了拿奖学金了,否则一直半工半读,最可能的结果就是钱也没挣到,书也没念下来。
美国念书跟国内不大一样,自己选自己的课,必修课每年都开,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选择今年上还是以后上,反正毕业前修完就行。这样自由选课的结果,就是同一专业同年入学的人,直到毕业可能也没见过几面,尤其工科很多在职研究生,上课来下课走,根本没机会交流。
相较于美国本地的在职学生,留学生们相互之间的接触倒是比较多,按规定留学生必须注册为全职学生,这意味着每个学期都要修够一定学分,上的课多了,碰面的机会自然就多,一来二去就熟悉了。陶郁相熟的留学生有五个,一个台湾来的,一个韩国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西班牙的,还有一个印度阿三。
台湾同胞名叫骆丰,来自台南,个头不高,带着一股淳朴的屌丝气。陶郁原本担心跟台湾同胞会有政治上的隔阂,但他很快发现担心都是多余的,骆丰同学压根儿不关心什么一个中国问题,他最关心的事是康熙来了今天请谁做嘉宾。
陶骆二人一开始并没有打得火热,因为陶郁这人不幸地对综艺节目完全没兴趣。但后来被搅屎棍一样的韩国棒子催化了一下,两人的同胞情迅速血浓于水了。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某天小韩和骆丰一起去学校超市,卖东西的小哥随口问小韩是不是中国人,小韩就出离愤怒了,质问卖货小哥为什么说他是中国人,并且指着骆丰问小哥为什么不说他是韩国人。骆丰和小哥都不太能理解小韩这种莫名其妙的炸毛行为。见自己的质问没能引起共鸣,棒子那种“全宇宙都是我大韩的”的毛病犯了,冲着骆丰喋喋不休“长白山是韩国的”、“粽子是韩国的”、“端午节是韩国的”……
以骆丰对政治的漠然程度,对这类挑衅一向持有“这干我屁事”的态度,但那天不知哪根筋搭错,忽然就热血了,面红耳赤地跟跟小韩争论起“historical problems”。
此时陶郁恰好从旁经过,轻飘飘撂下一句“韩国是中国的”,在小韩酝酿好反击之前,他又补充了一句“historical problem”,然后就走了。
据骆丰讲,陶郁走后小韩脸憋得通红,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最后生生被气跑了。
这两人在背后像小娘儿们嚼耳根似的,猥琐地笑了一阵,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第四章
芝加哥这个地方,一年里有半年在下雪,好时光是从五月到十月,但又雨水不断。
秋假前一天晚上,陶郁有门水化学。这天预报将有暴风雨,阴了一整天,直到九点下课的时候,雨来了。陶郁看着窗外风雨交加,犹豫了两秒,决定冒雨回家——他得把书包放回去,然后去冷库搬猪肉。
狂风裹着大雨从四面八方袭来,打伞成了摆设,陶郁索性收了伞在雨里狂奔,跑回唐海南家时,狼狈地像刚从河里被捞上来。他站在门外哆哆嗦嗦地掏钥匙,门从里边打开了,常医生扔了条毛巾出来。
“你今天休息啊?”陶郁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刚九点半,这么早见到常征,他还有点不习惯。接过毛巾把自己上下抹了一遍,放下包去卫生间里换衣服。
出来时他看见常征在大客厅里看电视,唐老师还没回家。陶郁敏感地察觉到常征有点不对头,这人平时虽然也不大说话,但今天的气压格外低。他想起来常医生早上是去上班了,今天不是他轮休的日子,以他们住院医一天十四小时还要加班的狂人工作制,这么早出现在家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常医生,喝水吗?”陶郁见时间还早,打算关心一下室友,平时跟常征交流的机会不多,也不好直接问人家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大家开心一下。
常征开着电视,心思却完全没放在屏幕上。他回来的早是有原因的,因为一起医疗事故。今天他跟着主治大夫上了一台手术,患者是个刚出生的婴儿,先天心脏三尖瓣闭锁。主治大夫本来认为手术条件不足,术前查出房室瓣存在返流。常征查了很多文献,有案例表明如果手术方式得当,这种情况是可以手术的,他的资料最终说服了主治大夫。术前他们考虑到了各种情况,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但术中婴儿突然全身僵硬,停止呼吸,后来虽然抢救回来了,但手术没能进行下去,长时间窒息可能对大脑也造成损伤。现在家属追究医疗责任,由于之前查出房室瓣返流的原因,这事就有点说不清楚。手术是常征一力主张的,但他只是实习医生,没有主治大夫的同意,这手术也做不了,于是现在上司被他连累得成了主要责任人,接受调查。
上司并没有责怪他,只是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年轻人不能为了手术而手术。常征一方面觉得对不起上司,但心里又憋屈。大家都觉得实习医生为了增长经验,千方百计上手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可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想的是做了手术,能让那个孩子摆脱先天心脏病的阴影里。
“常医生?”陶郁伸手在对方眼前晃了晃,“好么,我以为你让人点穴了。”
常征没接话,接过陶郁手里的水杯喝光了,又把杯子放回他手里。
陶郁心想这人倒不客气,他直起身想把杯子送回厨房,眼前忽然一黑,脚步顿了一下。
常征抬头问:“你怎么了?”
“没事。”陶郁缓了一会儿说,“起来猛了。”
常征若有所思地看着陶郁的背影,感觉这小子比刚见的时候瘦了不少,T恤穿在他身上好像被一根棍子撑着。
“你吃晚饭了吗?”常征问。
陶郁回想了一下:“下午吃了个热狗。”
常征走到窗口,看外面雨小了,他转身回屋拿了车钥匙,对陶郁说:“吃个饭一起。”
陶郁有点受宠若惊,常征这人一向不冷不热,除了上次在中餐馆里帮了自己,后来又给了两张餐卡,就再没有更深的接触,一个屋檐下碰了面也就是点头打个招呼,今天居然要拉他一起去吃饭?陶郁犹豫了一下,说:“我十点半得去上班。”
常征看了看表:“来得及,送你过去吃完饭。”
陶郁无奈地看了对方一眼,实在不适应这种用英文的语序说中文的习惯。
陶郁一路担心常征把他拉到什么高级餐厅,他可吃不起,结果车子停在路边一个墨西哥小快餐店,里面连座位都没有,跟国内大排档差不多。常征下车去买了两个Burritos,面饼里卷了米饭肉和菜——墨西哥版春饼。
外面下着零星小雨,两人坐在车里吃饭,狭小的空间里谁都没说话,常征沉默惯了,可陶郁在这种气氛里简直如坐针毡,没话找话道:“没想到你当医生的,吃饭也这么对付自己。”
常征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手里的墨西哥卷:“有肉有饭有菜,怎么对付了?”
“我不是这意思。”陶郁说,“你们当医生的那么高薪水,还吃路边摊?”
常征抹抹嘴说:“住院医薪水不高,念完医学院我欠了二十万贷款,现在的工资不够付贷款利息。”说欠钱的时候,他语气依然平淡,仿佛背着一屁股债的不是他本人。
陶郁吃惊地看着对方,他以前听说美国医生挣得比华尔街当CEO的还多。事实上医生的收入确实很高,这跟他们超长的工作时间是成正比的。美国本土医学院的数量只有那么多,每年录取的医学生名额固定,不允许增加,官方说法是保证教学质量,但这也造成了美国医生供不应求的局面,除非是本人学艺不精或有重大医疗事故,不然还真没听说过医学院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不过话说回来,医生薪水高,但还高不到刚毕业的小住院头上,偿还高昂的学费贷款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刀,有时候这把刀能悬个十几年。
陶郁忽然觉得跟常医生一比,自己眼下这点辛苦也不算什么,同样是起的比鸡早睡的比“鸡”晚,好歹自己赤字为零。他忽然觉得连这饭吃起来都有点食不下咽,他一手摸向钱包,小心地问:“这肉卷多少钱?”
常征侧头看了陶郁一眼,没想到自己的话让对方同情心泛滥了,这小子为钱愁得跟狗似的,竟然还有闲心同情别人。
“中文有句话,叫什么‘和尚’‘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