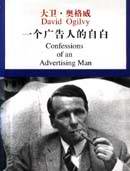自白-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进简书的单人病房要经过一整套与进手术室无异的消毒杀菌程序,病房里仍旧单调地响着仪器声,简书安静地躺着,形容憔悴,但幸而没有尽失生机。短短一天里两度相似的经历,心境却全然不同,黎蘅此刻站在病房里,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心情。
一个小护士跟着他一起进来的,迅速给简书检查过一番,就示意黎蘅靠近,轻声给黎蘅解释:
“特护病房里病人的所有护理全都会有专人来负责,家属陪床的时候只需要在病人清醒时给予安抚,其他时间最好不要碰到病人,也不需要额外的护理,病人现在还有心衰的症状,不能平卧,所以即使病人醒来了,也不能擅自调整床头的高度。”
护士说完,转头看向黎蘅,见他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才又掀开盖住简书的被子道:
“电极片是连接心电仪的,颈部的管子是输血的,还有胳膊上的留置针,这些平时都不能碰到,另外,病人出血还没有止住,家属要密切关注出血量,如果血量变大,要及时按呼叫铃。”
黎蘅只看了一眼,便觉得心脏仿佛被狠狠攥住了。
简书瘦削的身子被裹在过于宽大的病服里,胸口露出的一小片皮肤,清癯得能够看见骨骼的走向,身下的垫子上染了血,白色映衬出刺目的鲜红,看得人心慌。
护士轻轻将被子盖回去,转头见黎蘅紧皱着眉头,又宽慰了一句:
“昏迷对于患者来说,也是在恢复的表现。”
黎蘅点了点头,护士将简书病床上染了血的垫子重新换过,才收拾东西离开,走到门口,又对黎蘅道:
“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在病房旁边,有什么状况都及时按铃。病人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清醒,可能需要几天,家属可以多和他说说话,如果发现病人有苏醒的迹象,也要及时叫护士。”
黎蘅重新回到床边时,看了一眼挂在病房里的钟,才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四点。这整整一天,时间对于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有那么一刻,整个生命对于他而言,都成了没有意义的事情。如今坐在这里,看他爱的人小幅地呼吸着,心电仪上显示出他的心脏搏动缓慢而不规则,可还是执着地跳动着,黎蘅突然觉得,这一生能有这么一刻,别的事情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直至这一刻,黎蘅才终于落下了泪来。
(94)
然而事实上,就在果冻窝在新生儿室里,第一次张着嘴、挥舞着小肉手等奶奶给自己喂水喝的时候,简书就醒了。
从出手术室到简书睁开眼,二十四个小时都没到。
黎蘅见到过一个理论,说大手术过后醒得快的病人,要么是身体底子好,机能恢复比别人快些;要么是心里挂记着什么人或是什么事情,放不下心休息。如果这说法真有依据,黎蘅想,简书必然是属于后一种的,因为这一两年来的消耗,早已经让阿书的身体没什么底子可说。
于是黎蘅又不禁想,简书究竟是记挂着他,还是记挂着他们刚出生的女儿呢?黎蘅既希望是前者,又希望是后者,但又好像更愿意两者都不是——如果阿书能够什么都不牵念,不是就可以多休息一阵子了?
简书苏醒之后有那么一阵子,黎蘅觉得自己被绕在这些好像没什么意义,又似乎很有意义的问题里,来来回回地想,出不去似的,一面又看着医生站在病床另一侧,给简书做各种检查,摁着简书肋下,问他疼不疼,简书皱着眉点头,呼吸乱了两拍,又被动地跟着氧气面罩里恒定的气压艰难地调整过来;他们撤掉又一张染着许多血的垫子,并换上新的;他们给简书量了体温,说有些低烧;他们把血浆袋换上了新的,鲜红色的液体仍旧经由简书颈部那根看起来很痛的管子源源不断流进身体,然后似乎一点也停留不住似地,再匆匆回到白色的垫子上……
黎蘅觉得自己好像冷静得出奇,如同隔了一层茧在看着这一切发生似的,倒是医生,一面顾着简书,一面还瞟了他数眼,不知是带着怎样的理由。
医生走以后,黎蘅感觉被自己握住的湿冷的手指轻轻在自己掌心动了动,靠近了一些,才听到简书的声音。
“怎么……就哭了?”简书问他。
黎蘅愣了一下,用力眨眨眼睛,感觉眼眶果然是湿的,脸上也跟着觉出泪痕留下的异样感,这才后知后觉地想到,原来我是哭了。
简书不那么清醒,问过话就又昏沉起来,撑着不闭上眼睛,全用来盯着黎蘅看。
“我这是高兴的。”黎蘅说。
简书露出不解的神色,迷蒙地兀自想了一阵子,旋即点点头表示明白了,脸上却仍旧挂着一知半解的神情,似乎大脑里的能量还支持不住他完成“阿蘅因为高兴,所以哭了”这个思维的转弯。
黎蘅其实特别想抱一抱自己的爱人,用手划过他所熟悉的骨节分明的脊柱、平滑而漂亮的蝴蝶骨,最后落在他修长的脖子上;他也想感受简书的呼吸被自己整个儿地拥在怀里,这时候才像是彻底地拥有了他。然而眼前羸弱的简书,就像刚刚修补好的瓷器,比寻常易碎品更加脆弱的模样,那些将不同的液体运输进简书身体的管子,就是粘合这瓷器的唯一的力量。
这力量与黎蘅的力量不兼容,并且黎蘅明白,自己的力量并不能取代它,让简书生存下去。
好寂寞啊,黎蘅想,握着他的手,都还在想念他。
简书又动了动嘴唇,黎蘅仔细辨认了许久,猜出他说的是“晚安”。
这一点被药物和涣散的精力引发的小迷糊成功逗笑了黎蘅,他也对简书说了一句晚安,尽管知道这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
下午黎妈妈抓紧那宝贵的半小时探视时间,抓了黎蘅父亲一起来看望功臣,见到简书的模样,两老都是一阵沉默,凝重就挂在脸上,黎蘅能看出来,连父亲也心疼得不行了。黎妈妈一个劲地念叨,小书怎么瘦成了这样,当时看见不还好好的吗?声音压得低低的,抖个不停。黎父一直没说什么,到走的时候,才忽然对黎蘅说,等小书好了,抓紧结婚吧,黎妈妈泣不成声,只能在一旁不住点头附和。
是该抓紧结婚了,黎蘅想。
虽然阿书想做的跳伞一时半会儿实现不了,也不知以后究竟还能不能实现,但好歹应该领了证,宣了誓,然后光明正大地亲吻和拥抱,让大家都知道,简书以后每天都有人疼了。
第35章 贰捌、才敢说沉溺(二)
(95)
简书几天里断断续续地睡,又断断续续的醒,精力能跟上的时候,就睁着眼睛看黎蘅,黎蘅走到哪,那目光就追到哪,也不说话,只看着他笑,好像怎么看也看不够似的。
黎蘅就花大量的时间与简书对望,两个奔三的大男人互相瞪着眼傻乐,当事人倒丝毫没觉得怎样奇怪。
到除夕那天,简书已经稍稍有了些精神,能吃进去一点儿东西了,尽管低烧还是退不下去,人也不很清醒,但状况总算平稳了下来,血也不再水似的往外流了。
黎妈妈做了满满一保温壶的汤给简书送去,再三嘱咐黎蘅要仔细照顾。二老最近带着果冻,看这小公主身体棒得没边儿、能吃能睡的,更加坚定了“小书身体坏成这样,肯定是自家儿子没照顾好”的观点,来特护病房看望时,每一回都不落下数落黎蘅一顿,简书听了又觉得不忍心,声音细若蚊蝇的,还要给自家老公辩护两句。
黎蘅把母亲拿来的汤打开,病房里没一会儿就散开了食物的香气,药剂冰冷而刺激的味道短暂地淡了下去,好像这房间里终于有了点人情味儿。
简书没什么食欲,味觉被药物麻痹了,也不太能辨得清味道,只是看着黎蘅开心,他也觉得很开心,就着黎蘅喂过来的勉强吃了两口,但吃过之后,人就开始不舒服了,胃里胀得不行,还有些恶心。黎蘅看简书实在难受,心里疼得发慌,更加舍不得逼迫,摩挲着人的头发问他哪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简书摇了摇头,费力地喘了几口气,才对黎蘅道:
“不想吃了……”
这话是实话,却也带着一点撒娇的意味,听得黎蘅胸口一酥。
“那就不吃了,过会儿再吃。要不要喝水?”
简书想了想,还是摇头,皱着眉头道:“苦……”
“我给你调一点儿蜂蜜在里面?或者加一颗冰糖,想喝吗?”黎蘅锲而不舍道。
简书失笑,拉着黎蘅不让他离开床边,手指有意无意地挠着黎蘅手心,这动作也带了点儿撩拨的意味。
“阿蘅,”他说,“又过年了。”
“我们阿书最难的一年已经过去了。”黎蘅在简书头顶亲了亲,不敢碰他别的地方。
“每年除夕,都让你没法休息,还得照顾我……”简书沮丧似地叹了口气,头往旁边挪了挪,寻找黎蘅的怀抱。
黎蘅这会儿断不敢往床上坐,只好伸了一支胳膊去搂简书,半个身子悬空着,紧张兮兮的。简书看他这别扭的姿势哭笑不得,但也不说什么。他现在特别特别想自私一会儿,赖进他朝思暮想的、昏睡中都还眷恋的怀抱。
“我觉得像个轮回一样,”黎蘅说,“不过去年除夕,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你好,我当时见你,就想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你,让你再也不受半点伤害,可又怕你拒绝——今年,我至少可以随时陪着你,我们什么都有,还有了女儿,你也会好起来,我们会在一起,我以后每天都可以想,要怎么对你好,想明白了就立刻去行动,你会慢慢恢复健康,而且我至少不用担心,你会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黎蘅语气里夹杂着一些苦涩,简书知道,这话既是告诉他的,也是黎蘅说出来,自己宽慰自己的。简书安安静静听完他的絮叨,忽然问:
“女儿……怎么样啊?”
“好着呢,白白胖胖,小名叫果冻。哦对了,我给她想了个大名,还没定下来,得跟你商量。”
简书深深看了黎蘅一眼,笑了起来。
“我准备让她跟你姓,名字就……”
“姓黎吧,”简书打断道,“我喜欢能从她的身上,看见你的影子。”
黎蘅犹豫了一下,终于点点头,说也行。
简书又问:“名字呢?”
“乘初——‘乘初霁之新景’,她是咱们新的开始。”
“黎乘初,”简书跟着念了一遍,称心地笑起来,对黎蘅道,“阿蘅,你真厉害。”
“没有你厉害,这么难,还回来陪我。”
黎蘅说出这句,眼泪忽地就不受控制般落了下来。
“没事啊,我没有很难受。”简书真诚道。
身上的痛苦,再多上十倍也不比之前心里的煎熬。等待果冻出生的那段日子,每一秒都在害怕分离,越是离不开,恐惧就越让人无从适应。现在虽然难受着,心里却很放松,知道彼此还有很长很长的路可以一起走,连病痛都不能再让他低落。
“你多陪陪我,我就不难受了。”简书拉过黎蘅的手亲了亲,对他道。
(96)
简书转普通病房那天,说想吃家旁边一间店的粥。人已经许多天吃不下什么东西,每顿喝一两口汤都觉得胀,这会儿终于说想吃东西,把黎蘅高兴坏了,把简书拜托给母亲照顾,自己开着车去给人买粥。
回来的时候见黎父也来了,还把一小团的果冻也给抱了过来。简书抱不住孩子,只能放在自己枕边逗弄,二老搬了椅子坐在床边,也一个劲看着果冻手舞足蹈的乐。简书似乎在和孩子说这话,不过声音太小,黎蘅站在病房门口什么也听不到。
就这么看看,也觉得美好得仿若一个梦。
黎父最先察觉有人进来,回头看到是自己儿子,招了招手示意他进来。简书一见他就笑了起来,微微抬了抬手要黎蘅牵。
“第一次跟女儿见面,感觉怎么样?”
黎蘅直接坐在床上,拉住简书递过来的手,那触感仍旧冰凉,指间无意识的微微颤着,是还在脱力的表现。黎蘅满心就剩下疼惜,仔细地摩挲着简书的手,硬要给人搓出些热度。
“她认识我,我不认识她。”简书轻轻喘息着答道。
黎妈妈在一旁替简书告状:“这大小姐,看到她爸就多动症似的,刚刚糊了一巴掌在小书脸上,好险没碰到脖子上的针。”
黎父听了低低笑起来。
“没事,”简书道,“她就是开心,弄不疼我的……”
黎蘅看了看,简书确实没什么事,这才放下心来,冲果冻佯怒道:
“黎乘初,一点儿淑女样子都没有!”
果冻听见声音,停下动作茫然地看着黎蘅,半晌“咩”了一声,开始咂巴嘴。
简书轻笑起来,抬手擦掉果冻噗出来的口水,还要留神自己手臂上的留置针不被小姑娘的手碰到,对黎蘅道:
“她不习惯大名……不知道你叫她呢。”
“那得多叫一叫,小名顶多叫到上小学,就不能用了。”
“想那么远……”简书打趣了黎蘅一句。
黎妈妈噗嗤一声笑出来,插话道:“黎蘅这是深受其害,心里有阴影呢!”
“妈!”黎蘅不满地打断,然而无果。
“你知道他小时候小名叫什么?”黎妈妈笑得花枝乱颤。
简书期待地看了黎蘅一眼,见他一脸的不情愿,坏心眼地劝道:“你自己说,还少丢脸一点儿,反正最后……肯定要让我知道的。”
没等黎蘅开口,黎父忽然在后面一本正经道:“叫壮壮,我取的。”
黎妈妈更加不可自制地笑了起来,简书也憋不住,护着小腹上的刀口,轻声地笑。
“哎,你们行了……”黎蘅只觉得自己老脸一红,从此无法面对亲爱的老公。
二老在病房陪了好一阵,到中午才动身离开,果冻被留下和两个老爸多待一阵子,黎蘅信誓旦旦表示自己完全能照顾,倒是大小姐自己,见奶奶爷爷要走了却不带上自己,小嘴一瘪,便哭了起来。
简书心里知道孩子哭是正常的事情,但仍旧控制不住地心疼,调高了床头微微坐起来些,让黎蘅把果冻放进自己怀里哄。黎蘅乖乖照做,抱着果冻的手却不敢松开。简书产后出血刚勉强止住些,该排出的组织物却迟迟排不出,肚子也没见消下去。医生怕强行压腹让人排,或者注射宫缩剂,又要引发新一轮的出血,所以只能每天吊消炎的针水防止感染,让身体自行调整。
黎蘅自从听过这利害关系,愈发不敢碰到简书凸起的小腹,那些浸了血的垫子,如今每每想起,都牵动着他的神经,心痛得不行,唯恐简书再这么来一次。
两人这么一个吹箫一个捏眼地折腾了半天,才把果冻哄得缓过了劲,又开始往两个老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