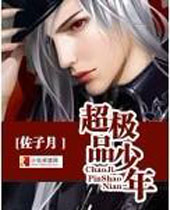故事_谦少-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记得他的,那天去找凌蓝秋,擦肩而过的那辆手术床,血滴落在医院地板上,那头熟悉的卷发。
他曾经笑着侧过身来,问我要不要吃他的巧克力糖。
我整个人都在发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发抖。借了警局电话,打给我老爸的主治医生,他是我爸亲传弟子,我爸昏迷那半个月,这个电话我记得滚瓜烂熟。
那边很快接起来。
“罗庆,我是肖林。”我问他:“二月十一,你们急救科收了一个被捅伤的病人,被捅了十九刀那个,他叫什么名字?”
“你问这个干什么,病人隐私……”
“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认识他!”
“他叫赵黎。”
我冲出警局,顾不得叫保安,开着车往医院赶。
路上闯了三个红灯,整个城市在下大雪,我去医院见一个重伤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幕总仿佛这样熟悉。
我赶到医院,罗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守在门口等我,我跟着他去ICU,看那个被捅伤的叫赵黎的人。
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在酒吧那一晚之前,我也未见过这个人。
但是我对这个名字的记忆这样深刻,深刻到近乎本能。
电梯上的红色数字缓缓上升,我心中似乎有个声音在一直喊:“快一点,再快一点!”
电梯“叮”地一声打开来,外面是医院漫长的走廊,我不知道这层楼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暗。我冲进走廊,看见了站在走廊中的那个人。
穿着黑色大衣,沉默,严峻而英俊的中年人,他身上的气场让人畏惧,看我的眼神似曾相识。
那个警察不记得他是谁。
我记得。
他是齐楚上一部戏的导演,如今国内这一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赵易。
走廊的窗口没关,冷风吹进来,我忽然觉得很荒唐。
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我不认识他,赵易我更是没见过,说起来,我们只是两个在酒吧萍水相逢的路人而已。
我最近真是混乱得不行。
…
出了医院,冷风一吹,整个人清醒不少。
更加觉得自己刚刚是在发失心疯。
刚回过神,电话就响了起来。
是齐楚。
“你去哪了,保镖说你扔下他们跑了,他们跟你的车也跟丢了。”他大概在什么活动现场,旁边嘈杂有人声。
“我没事,只是临时想起医院还有点事没处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他说谎,只是忍不住脱口而出。
医院门口很冷,外面的雨一直飘进来,我不等保镖了,自己开车回警局,表还没填呢。
虹桥路堵,我转身上立交桥,谁知道上去之后更堵,越开越慢,终于挤到前面一看,是车祸。
两辆车非常惨烈地撞在一起,其中一辆是辆保姆车,整个车头撞得不成样子,一地散落的汽车部件,警察已经拉了一条警戒线,正在疏通秩序,下大雨,一片白茫茫,完全看不清人。所有的车只能从车祸左边的一条狭窄路线缓缓通行,我开到旁边,被堵在那里。
这个视角恰好可以看到被撞毁的保姆车车头,医生护士在往外抬人,一片兵荒马乱中,竟然有个人影坐在一旁的车头上。
我以为是自己眼花,定睛一看,倾盆大雨中,竟然真的有个修长身影坐在车头上,全身透湿,越发显得脊背单薄,头发湿漉漉的,整个人如同落汤鸡。
我按下车窗,看清他的脸。
是电梯里的那个人。
他坐在那里,整个人都暴露在雨里,他穿着白衬衫,全部打湿了贴在身上,越发显得脊背像一张单薄的弓,肩上不知道是谁给他披的毛巾。
大概是发现我在看他,他也抬起眼睛,安静地看着我。
没有乞求,没有应该的惊慌,甚至没有一丝责备,他只是安静地看着我。
人群一阵喧哗,是从车里抬出了一个女人,裙子上全是血,已经奄奄一息了,医生护士围上去尽力抢救,而坐在车上的那个人只是安静地看着这一切。
他穿的衣服很好,脸上带妆。
我还是想不起他是谁。
但我知道了,他是个明星。
和齐楚一样的明星。
乐盈带的大牌明星,会像狗仔一样发骚扰信息给我吗?他会有什么企图,又能有什么企图?
后面的车按响喇叭,催促我快走,我加了油门,驶离这片事故区域。
…
我没有回去填表,我直接回了家。
我的生活在控制不住地走向混乱,千头万绪一团乱麻,然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是被困在玻璃罐子李的无头苍蝇,怎么转都找不到一个方向。
也许我知道方向的。
只是我本能地知道,往那个方向走下去,会有我不能承受的后果。
…
外面下大雨,我躲在家里,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拿着遥控器一个个台换过去,热茶喝下去,胃里却仿佛仍然冰凉。
六点的时候,娱乐新闻出来了。
知名经纪人乐盈在S城车祸去世,许多娱乐圈明星为之震动。
屏幕上用大字列出她当过经纪人的明星名字。
陈景,戴莹,涂遥……
娱乐新闻继续播,盘点身边家人遭遇过不幸的明星,一条条列出来,说明星身上的责任,说很多明星的身世都很坎坷,我端起茶杯来喝,听见一句:“齐楚也是父亲很早就去世……”
我脑中轰地一声,再抬起头看时,主持人说到别的地方,屏幕上没有一个字是关于齐楚的。
但我清晰听到那一句,绝不可能是我记错。
节目继续播,娱乐圈的各种花边层出不穷,又回顾这几天的大新闻,里面说到名导演赵黎在拍戏时被人砍伤,现在还没脱离危险,屏幕上放出他的照片,卷发,桃花眼,背景是在云麓传的记者招待会现场。
他对着我笑,就像那天晚上。
我想,我记起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了什么话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一直在沙发上这样坐着。
天色一点点黑下去,我始终没开灯。
…
齐楚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他一进门就打开了灯,然后才发现我。
“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开灯?”他站在玄关,一边把脱下的衣服往衣架上挂一边问我。
“跟你的那两个保镖被我换掉了,一天跟丢你两次。”他说话间,已经走进厨房自己找东西吃:“你没吃饭吗?”
他的声音仍然像十七岁一样好听。
我安静地转过头看他,他站在餐台前,也回过头看我,仍然是我十五岁遇见的那个人,仍然是我十五岁喜欢的那双眼睛。
“怎么了?”他再迟钝也发现了不对劲。
灯光落在他头发上,他的头发墨黑,眼神如星辰,白衬衫西裤,一身的落落无尘。
“你父亲去世了,是吗?”
像在平静水面上投下巨大冰核,我几乎能听见空气一点点结成冰的声音。
“你在说什么?谁跟你说这些的……”
我爱的人,是这世界上最拙劣的说谎者。
“是,或者不是。”我看着他眼睛:“你告诉我一句话就好。”
齐楚安静地看着我。
“是。”
我转身就朝卧室走去,他大跨步追过来,在客厅边缘抓住我手腕,他比我高半个头,常年慢跑,力气也大出许多,以前读书时也吵架,我尖酸刻薄,句句如刀,他吵不过我,只能扛起我,往床上一扔,我摔得七荤八素,也许能消停一会儿。
那感觉似乎就在昨天。
这些年的时光,一天天都清晰得像发生在上一秒。
怎么会是我记错了呢?
他抓着我手腕,我挣脱不开,两个人在客厅边缘较劲许久,我挣扎出一身汗,冷下声音道:“放开。”
“你听我解释。”
“你他妈给我放手!”我疯狂想从他的禁锢中摆脱,挣扎着往卧室走,他却把我逼到角落,两个人纠缠着,一起 跌进浴室里。
挣扎中不知道谁按到灯光,浴室一时间大亮起来,我看见他额头急出的汗,和眼睛里无从解释的焦急。
然而他要怎么解释呢?
他父亲去世许多年,我完全不知情,还在信他跟景莫延来往是因为他父亲。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就在这间浴室里,他还言之凿凿地跟我说起这个。
他一直骗我,骗我许多年。
最终挣扎不过,他抓着我手腕,把我困在浴室的墙角,手臂撑住墙壁,挡住了灯光,抓住我手腕,按我在墙壁上。
“不是你想的那样,”他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我父母的事太复杂,我没法跟你解释,我跟景莫延也不是你想的关系,我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情侣之间的感情,至少这点你要信我。”
他的眼睛墨黑,眼神真诚,瞳仁亮如星辰。
我却只觉得悲哀。
“你要我怎么信你呢?齐楚。”我只觉得无比疲倦:“我们的生活里,有太多谎言。”
他的眼里满是悲伤。
“你想知道什么,你在怀疑什么,只要你问,我都能回答。不要不问我,”他几乎是在请求我:“不要放弃我。”
我的心脏像被谁抽空了所有血液,紧缩成一团,我痛到似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脏还在跳动。
但我仍然爱他。
所以我告诉他。
“我只有一个问题。”
“什么?”他看着我眼睛。
他的声音这样轻,我想他已经猜到那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你一次,”我看见他眼里的光似乎在摇曳:“那天从酒吧喝醉了,你接我回来,在电梯里,我一直在问你……”
我看着他的眼睛,问出那个问题。
赵黎在酒吧问过我的那个问题。
“告诉我,马达加斯加的首都是哪里?”
他眼里所有的光,似乎都一瞬间暗了下去。
像烈火烧过的树林,满山的树都成了灰烬,只要风一吹,就什么都不剩。
我想,我见过这个眼神。
许多许多年前,在他家,在他母亲的脸上。
齐楚低下头,吻住了我。
他像一匹饿狼,或者一个溺水的人,他像是在疯狂地索取什么,又仿佛在确认什么,我闻见了唇齿间的血腥味,不知道是他的,还是我的。
他抱着我的力度,几乎要勒碎我肋骨,我本能地挣扎,手指抓过浴室的墙,却什么都抓不住。
下一秒,我被他带着,膝盖磕到浴缸的边,狠狠地跌落下去。
浴缸里放满了水,是昨天的,已经彻底冰凉,我在掉下去的那瞬间就沉到水底,无数的液体涌进我的鼻子眼睛,我整个人如同掉进冰窟,然而齐楚却抱着我,一起沉到浴缸底。
他仍然在吻我,我徒劳地睁大眼,冰冷的水里他的衬衫像水藻,我抓住他头发,他身上有好闻的气味。
仍然是我十五岁遇见的那个人,只是我闻得见他的绝望,我们都像是在沙滩上贪心的小孩,竭力地握紧每一粒沙,然而所有的东西仍然在无法挽回地从我们指间溜走。
我们什么都留不住。
胸腔里的氧气渐渐被消耗,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以为我们都要死在这里,溺死在这个冰冷的浴缸里。
然而没有。
我抓起浴缸边摆着的沐浴露瓶,砸在了他的头上,瓶子的喷嘴断裂开来。
他抓着我的力度松开,我挣扎着站起来,把他也拖出来,两人一起摔在浴室的地毯上,我想要找浴巾擦干他的脸,他却艰难地想要站起来,抓住我的手。
“肖林……”
我甩开他的手,扶着墙跑进了书房里。齐楚仍然追着我,我反手关上门,在他碰到书房的门之前,反锁住了房门。
我知道他骨子里藏着多危险的疯狂,那是足以把我们都烧得面目全非的东西。
他在外面敲门,叫我的名字。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不再回应他的呼唤。
但我要知道真相。
我全身都在往下滴水,整个人都在控制不住地发抖,书房一片漆黑,我开灯,坐到电脑前,开机。
无数的弹窗弹出来,我一个个关掉,水从我袖口流下来,我擦干,不让水流进鼠标里。
开机完毕,网络连接成功。
“肖林,开门……”
齐楚仍然在外面叫我。
我打开网页,进入搜索引擎。
齐楚仍然拍门。
我输入了那个问题。
回车。
网页变白,上面的进度条一点点前进,有一秒,我几乎要以为是我神经过敏,马达加斯加的首都还能是哪呢,不过是这世界上一个普通的城市。
然而下一秒,电脑屏幕直接闪烁一下,变成黑色。
机箱翁然而响,然而安静下来。
整个房间一片黑暗。
停电了。
我坐在电脑前,风从窗口吹进来,我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无数水流沿着我的身体滴下来,落在地上。
我如坠冰窟。
不知过了多久,我手上有温热的液体留下来,似乎很痛。
我这才发现我的手里仍然握着沐浴露瓶碎掉的喷嘴,打开抽屉,想把它放进去。
抽屉里是满的。
许多个沐浴露瓶的喷嘴,带着干涸的血迹,安静地躺在抽屉里,它们不知道在哪里呆了多久,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呆在那里。
它们每一个。都和我手上这个,长得一模一样。
…
我走到书房的门前,门那边已经没了声音,但是我知道,齐楚一定在那里。
我爱他。
他也爱我。
我们都无处可逃。
我在书房找到一块毯子,裹着毯子,蜷缩着靠在书房的门上。
“齐楚。”我叫他的名字。
他在那边轻声答应我。
但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们已经无话可说。
外面的大雨停了,风在呼啸,这么大的城市,没人知道还有这样狼狈的两个人,明明相爱,却只能隔着一扇门相见。
“肖林,我们去美国吧。”他忽然在那边轻声说。
“我在美国买了一个农场。”他说:“有河流,有草场,有苹果树。”
“我们去骑马吧。”他告诉我:“我会教你骑马,我会跟你一起看日出,我们可以建一座房子,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壁炉前看书……”
“跟我走吧,肖林。”他这样请求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