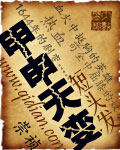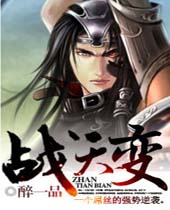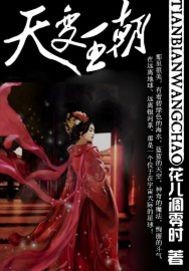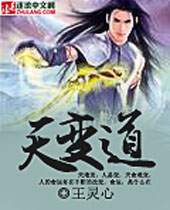�������-��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
����������ν�ʵ��ó�˽��Ǯ�����ܽ����**��ϵͳ���ڵ����⣻�Ǵ����ǰ����ε�ͯ��ȥ���ģ��Ҳ�˵���۹����������ʵ۾�����������ǧ��������˽��Ǯ����������������һ���˽��Ǯ���ó������������ȵ۹����������������ڷ���һ����������Ƕ�ô��һ�����֣�3000�������ӣ���һʯ��0��7�����ӣ�����������أ���Լ����4286��ʯ�ף���Щ������7��Ķ����У�һĶ��ƽ�����ٽ����أ��ܹ�����12���װ��ˣ��������Щ����ƽ����17���У�һ������ÿĶ������0��7���װ��ˡ�������ֻ��֪�����������һ���������յĵ��⣬����������ֵĶ��ٱ�����������һ�����֣�����������ȵ۹���������
���������۹����õĴ����������������һ��С�����ֿ��Բ��ϵģ�
����������Ҫ˵�ʵ�û���������һ�������ˣ�������������У���Ե۹����ô��ڵľ����Ҳֻ�DZ�ˮ��н������֮����������������ӵ��������������ã�����Ӣ��ʷ�۵�һ�ֱ��ְ��ˣ���Ӣ��ʷ���У���ʷ�ı�Ǩ������Ǽ����˿��Ծ����ģ���ʵ������ʷ����������һ���˵������ٴ�����������ʷ����֮��ʱ����Ҳ����С֮���ģ���ʷ�ı�Ǩ���ܸ�������Ⱥ�岫�ȵĺ����ƶ��ģ�
�������������������ڷ�����ĩ��ʷʱ�������۽�Ҳխ��̫����������ij������������������һǧ���������ӣ����ã��ĺ�ȥ�δӣ����ǵ��µ۹���������Ҫԭ����ʵ�ϣ������۹������Ӵ�ľ��û�����ij�����������������ӵĺ�ȥ�δӣ�ʵ������̫С�ˣ�������ɵ۹�������ԭ����Ȼ��һ��ԶԶ����������ֵľ������������˵۹������Ŀ��Ʒ�Χ��
���������������ؼ沢�����������ƣ���ĩ�ĵ���ݶ��������ȣ���ʵ�ڲ�֪�����˶��ٱ����۹��ľ�����Դ��50����60�����϶�ͨ����������������������У���ʾ�����Դ�ǵ۹���������֧��ģ���ʾ�����ԴҲ���ձ���������õġ����˾��ѹ������ˣ�����Ҫ��������Ӵ�ľ�����Դ�����������˵۹����������ķ��棻���������������Ӵ�ľ���ʵ���������ɵ��ļ�����ʴ�۹���ᡢ������ʣ�ġ�Խ��Խ�ٵľ�����Դ�����ǵ۹�����Σ����Խ��Խ����ء�
������������ǵ۹����ó���Σ���ĸ���ԭ��
�������������ھ�����ռ��ͳ�ε�λ�Ľ�����˼����Ҳ��Ȼռ��ͳ�ε�λ����������ĩ֮ʱ����ν�ǹ������ѧ�ߡ���Ա���ӣ���˭�Ұѵ۹���������Σ���ĸ�Դ��������ԭ���أ������ڷ������۹�����֮ʱ���ĸ�ѧ�߸Ұѵ۹������ĸ�Դ��������ԭ���أ�
��������Ҳ���������ֱ����£���ν�ʵ۵�˽��Ǯ�챻����Խ��Խ��Ҳ�������ֱ����£���ν�ġ����á���˵��Խ��Խ����۹��������������������ɵģ�Ҳ����ô�����ӾͿ�����صģ�
�������������ڹ��ũ��������Ͷ���������ʵ�пѹ鼺����������ơ��Ľ������ߣ������Ļ���õ����٣�ֻ�ǵ��˼ξ���俪ʼ��ֱ������ʱ��ȫ�����صõ����ɣ�������ȷ�����֣��ܶ�ﵽ700���꣬����������ֵĻ�����ʵ����һ��������Ķ�����������ﲻ˰�����Ӵˡ�������ơ���������ϳ���ֱ����ĩ����������һֱ������700�������ϡ�ë��������ġ��й����ͨʷ����������
������������1ʯ����120��������ġ���Ƚ���ġ��н��һЩ�������Ϳ���֤��������1��Լ�Ͻ���1��5733��ӽ�1��6������ô��1ʯ�͵���120���1��5733��Լ�����ڵ�188��8�н
����������������������估�����������ڣ������ˡ�1ʯ�ļ۸���7Ǯ��1������֮�䣬
���������������ġ�������۳�̽�����߲��ꡣ
�����������������зֳ��ơ������ƣ����ʾ���50�����ϡ������ݡ���֪¼�����أ��������ϵ�����Ķ�������߲���3ʯ�����߽�1ʯ�ࡣƽ����Ķ����2ʯ���㣬ÿĶ�����1ʯ2����1ʯ3�������ߴ�1ʯ5���������ʴﵽ60����70����ÿĶ������1ʯ6�롢1ʯ8������2ʯ�ģ������ʴﵽ80����90��������������ﵽ100�������پ������й�ͨʷ���й���������ʷ����
����������ע5�������ڷ�����ĩ��ʷʱ����Ҫ��ũҵ����Ϊ������Ȼ���������ľ��ã���ʹ���Ǹ����е���ν�����������ӣ����������������������ӡ�����ȴ��ʹ���µĹ۵���û��̫���ʷ��֮�У���������ֻ�е���ũҵ��������֤�۵㡣
�����������µ۹�����������Σ��֮�е���Ҫ��ԭ���ǰ��������ؼ沢�������ض����ֵ�Խ��Խ�ߵġ�Խ��Խ�ձ�ĵ��⡣�۹��ľ�����Դ��50�����϶�ͨ���������ʽ�����������������صļȵ����漯�����У����ҡ����塢���š��ϲ�̫�ࡢ������������𡢴����ˣ��������㹻�����ˣ������µĻ�����Щ�ȵ����漯����������Խ��Խǿ��ľ�����Դ��ȴ�������ɵ����������Լ������棻�������������ʳ���������С�����������������Դ������������ʴ���ձ�����ֽ�ʣ�ľ�����Դ��
��������¢���Եġ��߶�ĵ�����ռ�۹�������Դ�ı���Խ��Խ������ǵ۹�����Σ���ĸ�Դ���ڡ���ʵ�����Ƿdz��Զ����ġ���ʴ��Ͷ����������Ӷ��ߵľ�����Դ��ʵ��������ν�����á��Ķ���ʮ����
�����������Դˣ���˵���ǹ�����Ķ��ֵ��ˣ��������Ҳֻ�Ǻ�����ʣ�˭Ҳ���ҶԴ�ȥ����������Ǹ�������ʵ�ڵ���վ����ͳ�ν��Ķ����棻������Ǹ�������������ʵ���Dz���������ϻ��ˡ�
��������һ���˵���ʵ�û��ʲô���˵ģ�һ�����ڱտ�˵�ʵۡ�̰�ơ��ֵù�����������û��ʲô���˵ġ��������ҵ���ͳ�ν�������������ͳ�ν����Ǻ����ʵ��̫�����ˡ�һ���Ҵ���������ۣ��ǿ϶������Ծ�������
�����������dz��������۹������ĺ���������˵���ǵ۹�����Σ������Ҫԭ�������Ϊ�����˵��ͨ����Ϊ�۹�����ֻҪÿĶ��ƽ������20���ף��Ϳ���һ����ȡ��ǧ�����������������۹�������������֮ʱ��Ҳ����û����ȡ�������صĸ�˰��
�����������������ؼ沢��������أ�һĶ�ĵ�ƽ��������Ȼ�Ѵﵽ��100�����ҡ�����Զ����������֡�
�����������������ֿ��Կ����������۹��ϰ�������ƶ������Ҫ��Դ��������Խ��Խ�ձ�ġ�Խ��Խ�ߵĵ�����ɵġ����������棬�Ǵ��������۹������ҡ����塢�ϲ�̫�ࡢ���š��������������ȵ����漯�Ź�ͬ����ģ����Ե۹������¸���û�иҰѵ۹���Σ����Դ���ڴˡ�
��������һ������Ȼ�ģ�����ձ�ũ��ӵ���Լ�����أ��ǵ۹����������յ��ǵ�˰�����ϰ��ն����Ƿdz�С�ģ�
��������һ������Ȼ�ģ�����ձ�ũ��ӵ���Լ������أ����ձ�ũ�������Ͳ�������Σ��֮�С�
����������������֮������۹�������������ڷ�ɢ���Ը�ũ���У��ǵ۹����Ҳ��û������ȥ���ģ��͵˰��©˰��������֮���۹�������˰�վ��ܱ�֤��
�������������ֹ۵㣬����ĩ��ԶҲ�����Ϊ�����Ĺ۵㣻��Ϊ���ֹ۵�����սͳ�ν�����ġ�
���������������Ǻ��������۹������Ĺ۵㣬��Զֻ���ڵ������ṩ��˼���������ܣ�ȴ��ԶҲ�ܲ�����ͷ������������֮����ʹ���Ǻ�һǧ����Ψ��ʷ�۷�����ʷ��������Ҳ��Զ������Ψ��ʷ���ڷ�����ʷ���ٻ�����֮��������ʷ����ij���ˡ�ij�����˵����������¿��Ծ����ġ�
���������۹�����ذٷ�֮**ʮ�������ٵ��������У��������ɻ��ҡ����塢�ϲ�̫�ࡢ���š���������������ɣ���������Ե۹��������ɵ��ֺ�����������������˰����ֻ��ʹ����˰�ռ��٣������Ǹ�ͨ���������ʽ�ѵ۹��IJƸ����������Լ����У���ʹ�ձ�ũ����������ȴ���±��������ǻ�ͨ�����л㼯��ǿ����Դ�������ƹ��ż��ţ�ʹ�۹�����ȫ��ܻ���
�����������µ۹������ĸ���ԭ���ǵ۹��ĵ�����Խ��Խǿ���ˡ��۹������������������۹����������Լ�������յ��µ۹�����һƬ�������֣��۹����һƬƶ�
�����������ġ���һ�¡�������������
��������������ʱ�䣺2009��9��18��9��35��54������������5369
���������������ϻ����´���ϡ�ĺ����������賿ȴ����������ͷ��û�г����Ѿ�����������������ôһѹ�����dz����ѵ���������������������Ͻ��˺ò����ꡣ
���������������죬����Ҫ��������������·�����ӵ�ͷ�IJ���������������ŷ�����ɧ���з����ۿ��˿������ٴ��ɵ�˯��������
���������������Ǻô�һƬ��������Ĺ��������˵��棬һ��������С���������ڹ�������ʵϲ�ˡ���Ƭ������·��������Ӳ�����������п��Ŀѳ����ģ����ڲ�����أ�����Ҳ������࣬���Ե�������ϱȱ��˼�Ҫ������һЩ��
����������·���������ĵ軧���ӹ���ʵ�ڐj�̣�ÿ��ɰ��˶��ҵ�����֮��Ҫ����˰��˰������Ҳʣ���¼����ȡ��Լ�Ҫ��ƺȣ���������Ҳ����Ҫȥ�����ϳ�����������ϱ�ۿ���Ҫ�������ޣ�Ů�����˰��������䣬ҲҪ�ð켸�����Ĺ��۵����Σ����ǻ�Ǯ��·����һ���Ӷ�ָ����Щ���Ϲ���������
������������������ڣ�·�������ò�ÿ�����������ϵصIJ�����ܡ���������������͵�ϣ�·�˿ڿ�ժ���ϳ��㲻��͵����Ҫ����Сɽ����Ұ��ҿС�
��������������Сɽ����������ҹ���Ⱥ��ӵ�����ɽ�������Ѻö˶˵���������ˣ������д��ٵİѹ���Ҳ�����������ò���������
������������ķ���̫�ƣ��ؽ��Ļ�һʱ�ò���������Ǯ����һ�����ˣ������ȼ�Ҳ����ֻ���̣�Ҫ�������ϵ�Ǯ���п�ԣ�Ļ����ٴ�һ�������磬�����������ȱ���á���
����������������ָͷ���㣬��Լ����������Щ���춯������˯��ȫ�ޣ������ʯͷ�ͳ�����
����������������֮�£�ӰӰ�´¿�����ͷ�и���Ӱ���ڹ���֮��ε���������ͷ�������ְ�ʯ�鶪�����������������������ҵĹϡ�����
�������������ϡ�����ʯ��������Ǻ�Ӱ��Ȼ�������𣬴�����ʹ��
���������벻���Ǹ��ˣ�
�������������ĸ���������û������������˵����·�����Ȳ�����˼������Ϊ�˸�СС�����ϾͶ�ʯͷ����ȷʵ��ֵ�á����ǽд��ӵ�����֪������Ҫ˵�Լ��������
����������û�¡�û�¡��������˸�����Զ�ͻ��ǵؽ��ͣ���ת����һ��ҹҲ�Ҳ�����ɽ��·����ʵ���Ƕ��ذ�������Ȼ����������û�п������ˡ��̲�ס���ȳ��ˡ�ʵ�ڲ�������͵�ԡ�����
���������������������ˡ�·����Ц�Ǻǵؿ�����ȥ����һ�������С��˵��ô͵��͵�أ��ڿʾ;���ժ��ʳ�������Ҹ����Ҹ�����ء��ס��������װ�磿��
���������Թϵ��Ǹ������ˡ�ԼĪإ����͡���Ŀ�����ò�����˵�һ����Ƥ�ҡ�ֻ������ͷ��ֻ�д��������ϵ������ֳ��������ڡ�ʵ�ڹŹ֡�
��������·���������ʱ��Ҳ�����ϴ�����������ǧɽԽ��ˮԶ�������ش�ʳ�˺Ͳ�˹�ˡ�������ǰ������������������л�������ű���Щ���˻�Ҫ�Ź֡�
�������������ܰ׳���عϣ�����Ǯ�������š����ס�����ô����װ�磿�����������ó��Ż������̵�ֽƬ��Ҫ�ݹ���������·����Ҳ�Ǿ��ȡ��ʳ�ͬ�������⡣
���������������������ˣ���·���������Դ�����Щ���ɵķ��٣���������б������ӣ����˽��ϵĶ��Ь������֮�⣬û�ио����ﲻ�ԣ����ɲ���ﶼ������������ô����
��������ɽ·���Ѿ���������������ף�����������װ����
�������������������Ծ���һ�㡣
����������Ҳֻ�ж����˺������ү�DzŴ������������µظɻ�Ĵ����Ӳ����㣬Ҳ߯�Ȳ��ǣ�����������ũ�˴����ӵģ���·�������ʣ�������ͷ���������̷������½����ĺ��У���
����������о�����ͷ�ˣ�������������Ĺ�·һֱ�Ҳ������߸ߵ�ͨѶ��̨Ҳ����������ǰ�Ĺ���װ���ũ��Ͳ�Զ���Ĵ�ׯ���������������Ӧ�еģ��ѵ���Ҳ��Խ�ˣ�
�������������˺��������Ļش��ţ���������ɶ���Ҿ����½�����ɮ�ˣ�������������ɽ������������κ�����һ���Ϊ�������ԾɵĴ��ε������ء�����
�������������Σ����ȥ�������ˡ���·����ˬ�ʵĹ�����Ц���������������Ǹ���ɽ��ɲ���ҵİɣ�����������Ҳ��֪���ˣ��ֲ��û���·�أ�����֪��**ʦ���¡�����
������������Ȼ�Ѿ����ף���ǰ�ķ���Ҳ�Ͳ������ˣ��ҽС����������İɡ�������Ҳ��Ը������ἰ�Լ�����·�����һ�仰�ҹ�����ɽ����ת������һ�����ϣ�����ʪ��˵����Ҫ�����������ֶ�����ͨ����֮��С��ѯ�ʣ���·����ܲ����ȸ��ҵ��ʳ��ʵ���Ƕ��Ľ�������
�����������ģ���ͨ�IJ�������ͨ�����֡�ɽҰ����֮�У�����������������������Ҳ��֪���ж��١�
���������������ֵܣ���������ЪЪ�ɣ�������������¶ˮ��ʪ�ˡ���·���������������Ҵ��ĸ������ӣ��㽫��ʳЩ���������Ҵ��㵽������Ҽ������չ����࣬������ˮ���ü��롭����
��������ȷʵ�Ƕ��ˣ��ڸ������������������ʣ���������Ҳ��������
��������ɽ��˼�뵥����Ҳû����������ӣ��������ز���ʶ��·��ҲԸ��ʩ��Ԯ�֡�·����Ц�ſ��������̻��ʣ������̹��ӣ�ʵʵ��װ����Ҷ�����ϻ���������һ��ڡ�
�����������Ǹ�ɶ����·��磬������ܲ��ܸ���Ҳ��һ������һ������������Ȼ���ᣬҲ�кü�������䣬һ����û�����̱������̵����ܣ�·����������������������������̱�����������
�����������ٺ١�ԭ����Ϊֻ�е����IJź���ڣ�ԭ�������������е�Ҳ���̡���·������������֮�ѹ�������̻ҿ�ȥ����װ�ĺ���������Ĵָ��ʵ�ˣ��ͻ���һ���ݸ����ġ�
������������������ϱ���·���������·�������ǹ�������ʿ�䣬������Ҳ�DZ��ɡ��������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