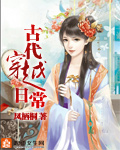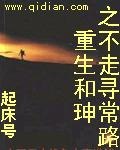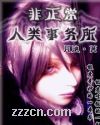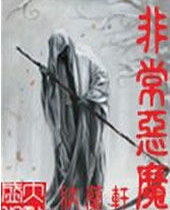�������ճ�-��102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
����������Ŷ������νһ�ᆰ�������ˡ�����λ�а˳����ɳ����ǣ���Ī�ǣ��չ���������֮�ġ���
����������ȻҲ�������棬�Թ����塣
�������������Ȼ���ʣ�����л���ࡣ��
���������������Ұ��ġ����룬��̫ʦ����Ӧ��֮����������Ψ�����������ƣ�����ͿͲ��ᡣ
��������������ˡ��ᳵ����С�档
����������Ӫ����¹������
����������³������ԣ���
����������³���ԣ��չ���������á��������Ի��
���������¹���ɫ��������������Ȼ����
����������Ī�ǣ���̨��֪��������æ�ʡ�
����������ȻҲ�����¹������ĸ�֮����棺�������չ��棬�����Ѷ�Ϊ֮����
�������������������ѣ��������ʡ�
������������ƥ������˽ͨ����֮�ġ��κΣ�����Զ��δ�顣���ֳ���������ڣ�пݹǣ�ʱ���ࡣ���д˼ơ����¹�һ����Ц������������Ϊ���ϵ����������������ҵȡ�����ϸ��ӣ��ưԹض�����
�������������д��¡������������γ��ѣ����ұ����ֵ���Ϊ����
������������ƥ�������ȡ��к���Ŀ���������������¹������Ե�����ֻ�裬�����ˡ�����
��1��162��Ӧ���·�
�����������Ŵ˶��ơ�����һʱ���ɲ���������̨�˼ƣ�ʵ���ڡ���
�����������������ˣ����ò�Ϊ�����¹��Ե����������ҿ;ӹ³ǣ����˱�Ϣ�����в������������������پ����ݡ�С����ս֮�أ�����ܵ����ϵ�ʮ��������
������������ʹ���������������üƣ��ǣ����ɷ���Ϊ��������Ͼ��˳����ˡ�
����������֪����Ϊ�ˣ��¹����Ȱ���������������в��塣�ҵ����ܣ���������������
�����������м䣬��������һ�֣���³���ԣ���̫ʦ����Ӧ��֮�����β����У��ҹۺ�Ч����
����������ν���¼���Ȩ�䡱������֮�⡣�¹����üƣ����˻�ҵ���Ǵ��ɷ���Ϊ���ҿ��綼����֮����ʤ����Σ������ƽϡ�
������������ʥ���ߣ�ӦʱȨ�䣬����ʩ�ˡ������ܡ���Ϊ���ޣ���Ϊ���⡯�����¹�֪��Ȱ���ã����ɿ�̾��
�������������������ԡ��չ飬�Ĵ���ϣ��������ڡ�
�����������丯�壬���Թ���ʵ��
��������ν������ͬ������Ϊı������˵������Ͷ�����ࡱ���¹���ı��Ҳ�����㣬��ʿҲ�����ʼ��ǣ�������֮���顣����ֻ����ͬ���죬�ศ��ɡ������Ե����������
��������ƽ�Ķ��ۡ��չ����������ݣ����϶������������⡣�����������ѡ��¹��϶�����̫ʦ�ܾ��Ѷ������ϵ±�ϯ���ض���Ȼ³������ȴ�ԣ���̫ʦ�����·����ϲ�������Ͷ���ϸ�����ȡ�¹����ƣ�����Ψ��³��֮�ԡ�
������������������Ϊ��С��Ǹ�ǽ��������ʳһ����ء��������������ش˳ǡ��ϲ����ٰܡ��չ��棬ʱ���ࡣ����һ���غ���������ɡ��������ֿɵá��αذ�ʩ���ƣ�����ŭ��Թ��Ϊ����������
����������Ի������������������У���������������ӡ���
�����������Ǵ�����
���������¹����䣬��Ͷʯ��ˮ�������ض���һ̶��ˮ��
�����������������Ϲۣ�ǿװ�������ı��������������������Ŀ�Դ����ҿ��綼�Ϲ�֮������ʤ�븺�������ƽϲ��١�
���������Լ�������Dzʹ���ϱ��������ݡ����½�֪��������ʦ�ڼ������ϸ��ӣ�Ϊ��ս�پ��������������С�����֤����ԴԴ���ϣ���������綼����;���ӣ��Գ�����һ���������������ˡ���˾��������������
���������������������֮�¡������������ڲᣬֻ�ȶ������̣���֮���ڡ�
���������˰�����������������ı�����˺��Ҵ�ɡ���ǰ���߹�֮�ң��ڷ�Խ��ɭ�ϡ�Ψ�֡�������������һ����ߡ���ֶ���ˣ����ղ������Ͼ������ֵ�����С�ޣ�����ܲ�ס������ο������ֵ�����ǽ���������ꡱ��
�����������������٣�ԶδԪ��������Ȼ�����ĿȾ��һ�����ʡ�������й��С�
����������Ի�������²�˵�����²��ɣ��������̡���
������������֮�⣬�ѳɶ���֮�£�������˵���ѽ����֮�£����ؿ�������ȥ֮�£���������
��������Ȼ��Ψı��������ɲ����
������������������ͬ����飬����һ�ġ��ܵ�ͽ�ڣ������ŵȣ��β�롣���м������壬Ψ����ͼ֮�����Լ����磬�㽫��˾�������飬�����г���
����������Ϊ����������֪��
���������������ϸ����ʵͨ����
���������綼��̫ʦ����
���������������꣬�渵���������˾�����ϵ����£��ԡ���ƽ���ꡯ��������ƽԪ�ꡯ������ǰ��������Ϊ����ƽ����֮ǰ�����������̡���ƽ��������ƽ���꣬�������ɡ���ƽԪ��֮��̫ʦ����������������Ⱒ��֮���
����������������ȷ������֮�š�������˾����֤����������ɲᡣ������̫ʦ�����������ס�
����������ƽ���꣬�����گ���⣨�����費����ǰ�����⣬����������ƽ��������ƽ���꣬������£����༸����Ǩ����ֻ�����в�ӡ����⡣������������ϵ��
��������Ψ�г�ƽԪ�꣬����硣��̫ʦ�к���֮�������������Դ����������������������֤������������ɡ�
������������������ڣ�������μ������һĿ��Ȼ��
������������������ʣ���ȴ��֪��ƽ֮���������Σ���
����������δ��֪Ҳ�������껰��һת�������룬ֻ�����������˾�س����ӡ���
�������������伱Ҳ�������䲻�⡣
�������������Ի�������ϸ�������������֮�ء����۰���֮��������ࡣ����̫ʦ���У�������Ҳ����ֻ������������࣬���ϸ��ӣ��ؾٲܵ����Ρ����һ���������¿���������˱�Ϣ��Ʃ��Ӥ���ڹ���֮�ϣ����䲸�飬���ɶ�ɱ��
���������ܵ�����Ϊ����������Ϊ�ұ����ˣ���������ǫ������᷸��ŭ������������������
������������ʤ��֮���ϡ����ڣ���ƽԪ�꣬����֮�
�������������Ƴ��ϣ��ٹٷ׳��ݳ������������������꣬��������䣬�������š�
��������ϯ�䣬�������������أ���ͬ������
���������������Ц���������Ϸ�����������������������̻ǣ����������֮�䡣���룬�����������ز����������档��
����������̫ʦ���Լ��ǡ���������䣬�����Ի����Ȼ����������У������죬�����������𡯣������֮�������������֣����������ص䡣������һ֮�ʣ�������̩�����ڳ��������Ϊ���ϸ������ˣ���֮���ӡ���
�����������������꣬���ü��չ����̫ʦ��������ơ�
�����������и����Ů�����̶��롣
������������������ʢ���������ͣ��˼伫ζ���������������ʡ�
����������̫ʦЦ�������β���ϻһ�ۡ���
����������Ŀ��ԣ��Բ�֪���ԡ�Ī�ǣ�ϻ��֮��¹ش�֡�
��������������䣬������ľϻ���֡����������է�֡�
����������Ī�ǡ�������˼�������䲻���Ŀ��
���������������꣬��æȡϻһ�ۡ�
��������ϻ��֮���Ӷ�Ŀ������Ŀѣ��
���������������ڣ�������̫ʦ��Ц���ʣ����ɽ����֮��������
������������Ҳ����������ͷǧ���ص�����Ȼ���͡�
��1��163����������
���������Ȳ����³�˷����
������������֮����˾�����ѱϡ��ϳʳ��ã�������ר�����顣
�����������粻���������ϡ�
����������˾�����ϵ����£����������ı����֤���ԡ���ƽ���ꡯ��������ƽԪ�ꡯ������ǰ��
�������������������䡣
���������ٹٽ��ԣ���ƽ���꣬�����گ����費����ǰ�����⣬���������̡���ƽ��������ƽ���꣬������¹�Ю�ƽ�֮�ҡ�������������˷ǣ��ҡ��������ѷ����в�ӡ������������⡣
��������Ψ��ƽԪ�꣬��͢��Ǩ�綼����̫ʦ�к���֮����������ǰ�ʱʽ��м���ѭ��
��������Ȼ�����Ӳ��س��������벻����
������������������������Ŀ���ʡ�
����������ȻҲ������ʷ��ة�����������౨����������������������裬ϲ����������Ч�ļ��߹���������������ᡣ����ԥ�߹������ڻ�ˮ���ʳơ��������ᡯ����
����������ԭ����ˡ���ǣ�����������Ӳ�Ȼ���أ��������������߹����ᣬ�к���ɣ���
�����������߹����ᣬ�����������ᣬ�˽�������ѵ��������ϰ����ʿ���������١�ʮ�Ĺ���������Ϊ���ˡ���������ʮ�Ĺ������ۻ��У�������ݡ���������ʵ����
����������Ī�ǡ��������������ʵ�������������������Գ����������ᡯ����
�������������ǡ��������������ࡣ
������������֮���ԡ��������ᡱ��������������������Բ�ȡ����֮�����Լٳ�������֮�š����������������ù�����ֻ������ӡ�¡���һ�ƣ��²ְ��ȣ���ʬ���ꡣ
�����������¼ȡ�ǣ�����㡱�����䣬��Լǣ�����������аٹ٣���֪�²���Ϊ�����£����������ֹ���γ��ܲ������ࡱ�������ǡ�СϺ���������㡱������λ������������Ȩ֮����Ϊ�˴��������������нڡ��ز����Ю�������֮�С�����dz����裬�ٽ����ᣬ����ǣ���������ϼ�����ˮ����Ϊ���Ա�Ҳ��
������������˾���ݲ��˽ᡣ
��������Ī�ǻ��ң�һ�����ײ��ɡ�
�����������������١���֪����ʧ��Ȩ�����ء����£��ʹ����ա�
�������������dz������ᣬ��ֻȡ����֮�ء�������һ�ԾŶ���
�������������£����������ٹٽ���һ������
��������ν��������⣬�������ӡ�����������ƫ�ģ�����δ�ܿ��������ǰ���֮����вܵ�ͽ�ڣ�ӻԾ���ԡ������߹��࣬������������������˻¡���
����������̫�������ԣ��������裬в��ı��֮�£�������Ī������Ŀ������������й����ͣ�Ϊ��ʧ��������ز�ڵ��ji������Ϊ�������ף����͵ò������ͣ���ôΪ��֮�˱��ʧ������а֮ͽ�ò����ͷ�����ôΪ��֮�˱��Խ����������Ի�����ͷ����ţ������С�����͢���磬�������ۡ����£����ɲ��졣��
���������Ͼ�����Ŀ���á���������������С����ı������ݲ����¡���Ϊ�������ᡣ�����������֣�Ⱥ�۲����ͷ���������η��ڡ����ܷ��ڣ����±��ҡ�
����������̫��һϯ�����������������������������֣�����Ҫ�����ɷ�����
��������������Ȼ��ͷ����̫�������Լ��ǡ���
���������칫������ܵ����ڿ�һ�ʡ����ԣ���������࣬����֮���������������˻¡�
����������̫ʦ��Ϊ��Σ�������д��ʡ�
�����������ϳ������顣����̫ʦ�����°ݡ�
���������Ŵ��ԣ����вܵ�������ϲ������̫ʦ���չ�������˧�����ò�����ֹ��
����������������Ϊ��Σ����������ʡ�
�������������ȣ����顣���ٹ�ͬ����
������������ˣ��㶨����֮��߹��࣬��������������˻¡��������������
�����������Ϻ����������꣬�����౨�����������£��������࣬�����������̡�����
������������һ�����ٹٻ�Ȼ��
����������ν�����̡��������Բ���������̣�ʼ���Ϲš������顤˴�䡷�����������̡�����Ի������֮�����ߣ�����ͭ����ʼ���ûƽ𡣡�
�������������������̣�ȴ������ͬ��������ԣ�����֮�У��������̣��µ��ȡ��ף��Կ��ꡣ����ѣ��������Ĺ涨���������Ϲ���ͭ��ǰ���ý𣬽����̣�κ���Ժ��þ������ţ��ָ�ͭ���ơ��������ơ�Ԫ�ó���������ͭǮ��
����������Ȼ�������������Կ���Ǯ��
��������˾��Ǩ�����ΰ��顷�����ԣ�����ƶ����¸���������ꡣ�����ܹ��̡��ɼ����̣������ߣ���Ϊѫ��߹٣�����ǿ�����ӡ�
������������˼��ʱ̫ʷ�������������������㷣ͭ����ɵ����̫ʷ�����ڡ����ΰ��顷�п�̾��������Ī�ȣ���������Ϊһ�ԡ���
���������Թ�������
����������˵��ʷ�ϱ������ܣ���ܶ��顣����Է�ͭ�����Ϊ���ˡ�
�����������룬����۽���һ��Ϳ�أ��п��������������Ϊ����֮�ʵ������������δ����ܳ������ᡣ��β��ܷ�ͭ���
��������������������ʦ����ѧ�����ʳ�����Ե���������֮�����д˵ȣ�����֮�١�
����������̫����ŭ����Ц������֪���࣬����ͭ���Σ���
����������̫�����ٰ���һ�ۣ���֪����
���������������꣬�����������ɻ�������ᣬ�����������ڡ�
����������ϻ�к�����������ʡ�
����������������ᣬ���Կ�����������¹�Ŀ����
������������ľϻ���������
��������һʱ��������
�������������ѿڶ����������ǡ�ҹ�����ǡ���������顯��Ҳ����
�������������ǡ���
������������飬�˴���ս��ʱ��������������Ϊ�����顱���롰����赡�����Ϊ��������������������赡�����͡���
��������������ǡ����䣺����ӯ�磬����ҹ�⣬�������ҡ����������ӡ���Ի�������֮�飬���֮赣���֮�߸���ʧ֮��ƶ����
������������ʱ���ơ����顱�������������������顱�ȡ�
����������ʰ�żǡ����������������������ӱ�����̨鿣��أ������������Ĵ�������֮���ǣ�ҹ��֮���¡�����Ի����������Ǯ�����ң�ҹ�����Ǹ��ޱȡ�����
�����������Ǻ�����˵��ҹ���顣
�����������ˣ�
��������������Լ��ͬ�����̿��ѡ�
��1��164����������
�������������������Ժ͵�һ��ּ��������Э����ȡ���衣
����������̫ʦ�������ţ����ϴ���֮����
�������������˹�����ԥ���롣���粽���ã�Ϥ����ȫ���ܵ���ƴ������������Э����Ի���������ƣ����ɵü桱��Ψ�С������ȡ���ơ��������˹�����Ϊ���ƣ�����������
�������������Ĺ�����������Ϊ��Ԯ���������չ��棬��������֮�ģ���Ȼ���ҡ������������ݣ���������ϵ£�һ�ϸ��¡�
�����������ϵ£����ó¹�֮��������ʱ������������ν��̰������á��������IJ�����������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