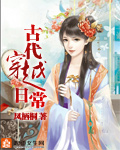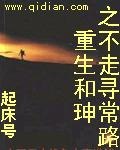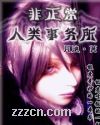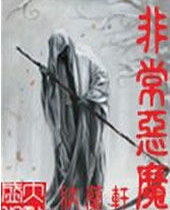�������ճ�-��114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ʷ��������ѿڶ�����
�����������������⣿������ⷢ�ʡ�
�������������¡�����̲ܣ���Զ���������ϡ����������о��壬���Ը��ӡ�
���������������γ����ԡ���������֪�´�
�����������ز����ʣ����������֪��������Σ���
����������������żã������������������ʵ��Ի��
�������������£���˾�գ����м��ӡ�����������ã�ֻ��Ƭצ��
�������������������ԡ�������Ӹ����ʡ�
��������������Ⱥ��������ʷ�������֮��Ҳ��������Խ���ƶ�������������Ϊ����˾�ձ����뺺�й��ϡ���ʷ����ﶭҲ����
������������ũ��������֮���֡�����Ϊ���ӡ���˾�գ����ٺ�ũ���������ϡ�����Ϊ��������Ҳ��������������
����������������Ȩ֮����Ȼȴ���ɣ����·��ϣ��������ӡ�ʷ����Ϊ�����ϣ�Ȼ�Ͼ��ֳ��ȵۣ�������λ��ͳ�����붭���Ϊ�ֵܡ�����ڱΡ�һ�Ա�֮�����ﶭ�ϣ��϶���˳�ʷ��֮�⡣���ϵ£���Ϊ�˳���������Ϊ�����Ǽ����������������ǣ������������������������ӡ����ٳ�ʹȻ��
����������ǰ���ԡ�ʷ�����Ϸʺ���Ӵ�λ�����������£����в�ȱ��Ȼȴ����ԼԼ��λ������֮�ϡ�
�������������������¡�
���������ȵ�����̨�ϣ�����֮�ʣ����¶�گ�����յܼ��������Ӽ̡����Ǻ��������������飬�����Ϸʺ�Ϊ�ۡ�ʱ�ơ��µۡ����µۣ�Ϊ��������˳�����ǽ�õ��ˣ���������������оϳDZ��ң�����֮�䡣�ۼ����������ݣ�������������������ʽ��ʱ�̫��گ��ϵۡ�������گ������ʷ��Ϊ�ۡ�����ʷ��ٰ�ʷ���ˣ�����Ⱥ�ۣ���������֮��������Ū�ɳ���������̫��Զ�ݺӱ������ݵ�������ʱ�����š����ݡ����ˣ�����ĥ����������Ϊ����������������Ȩ���з�ʷ�������������أ��������ۡ�����̫ʦ�ﶭ���ܳ���������ϵ£���Ӧ��ϣ�Ǩ�����¡�ʱ�����ա�
����������䣬�ܽڵ�����̨���飬�������ϵ�گ�顷���ɡ�ʷ����Ϊ���������ϣ����ƴ��ɡ�����������������������ɡ����˸���覴ã������������֡�ȴ���ɷ��ϣ������٣����������ǹ졣
�����������費���ף�����ı�𡱡������Ǽ������ܹ����
������������˾�գ��ض��ɡ������һ���еġ�
��������ͬ��Ϊ���������ɲ�֪�����ϵ�Ϊ�ˡ����㣬��ǰ�����������г������ϵ£���뽫�Ž��ɡ�������ʷ��ҡ�����װ��֪��ɱ֮����졣�º��ݻ�Ȼ��������ǣ��ڲ��������չ飬������ɡ��������ɸ�����
�����������������ˣ���˼���졣��������ᣬ��ʱ���ԣ������£����ż�������
����������Ŷ������������һ㶡�
������������������ԣ������ۣ����������Ƴ����ˡ�����ټ���֮������˾������ı��Ȼ�����¹�̨�����������ĺ͡���
���������������������Ҳ����������㶨�ƣ��������˾�գ����Ƽݡ���
������������������������ᣬ������ȥ��
��������������گ�����������ɽ���Խ�����������ɣ�������ս��
��������������Ӫʿ����ӵ��̨�����й������Χ�����ϵ£�ж�����ЯӪ�к�������������
���������������ܲ٣�ߵ�����¡���
����������˾�����������������ֹ�糣����ʧ�������档
����������л���¡������ϵ£���л������
�������������������⡣
����������������أ�Я�����������У�������ȭ�����ݼ�˾�ա���
����������˵���������ͬ����λ�������ϡ����ò��ϵ������κΣ������������£����ò���ͷ����
�����������ݼ����������ϵ£�������ʡ�
����������˾�յ�֪������̿ͣ��dz������������������Լ����ࣺ���������ԣ���������������롣��
�������������£������������ϵ£����������Ȼ����֮�£���Զ�����硣��
����������˾�գ����⣿�������������裬����ɫ�糣��
��������������¹�Ŀ�������ϵ£��콫�����Ϸʺ����飬ת�����ӡ�
���������ɻ��������ӹ���ȷ�������ϳ�����������
���������Ϸʺ�ʼ����������ܲ�ʶ����ϸ���������ԣ��������ӣ������ҡ�����ǰ���ϡ����ϵ¿ڳ����������ָ��
�����������Ϸʺ��ԣ����·dz��ȵ�Ѫ�ã��˶�̫����������֪��Ȼ�����ϵ£�ֱ�Բ��䡣
����������˾�գ����ԡ��������أ�ɫ������
�������������£�Ȼ�����ϵ£�Ŀ����硣
��������������Ҷ��ӡ�
�������������ж��Ͼ���������ɥ������
�����������ϵ£�������ǰ�����ȵ�ʱ��̫ƽ�����Žǣ��Գơ�������ʦ�������ٷ�ˮ��˵���Ʋ����������Ƶ��̻����£�ת��ڿ��ʮ����䣬ͽ����ʮ�����ῤ���ࡢ�졢�ġ������������ԥ����֮�ˣ�Ī����Ӧ��������ʮ���������̽�����Ҳ���������ˣ�С������ǧ�ˣ�������˧�����֡����г��̷�נ������Ϊ��Ӧ����Լ�Լ����꣬�����գ���������𡯡�Ȼ��δ�����ҡ����������Žǵ��ӡ��������ܡ����·�����
��������һϯ�������ö��Ͼ������ˣ��������¡�
���������������£����ϵ���������֮�ˣ������¿�֪�������ܡ�֮�Һ�����
��1��142����������
��������һ�䡰����֮�ҡ����ȵ�������������ִ�������档
���������й���У�ѻȸ������������š�
��������������֪�����ϵ£��������ʡ�
�����������ޣ��ޡ���������֮������Ա硣
����������̫ҽ����ڡ������ϵ���֪��֮͢�¡���ʱ����̫�ʱ�����齣�ʱ��ʱ��������̫ҽ���ŷΪ�����Ρ�ȡ��̫���N��һ�۱�֪��
�����������̫꣬ҽ���ŷ�챻Ѻ����С�
����������̫ҽ�����˾�գ�ͷҲ���ء�
�����������¹٣��ڡ����й�������Ӫʿ��Χ����Ͱһ�㡣�ŷ������ӡ����ο�����С�������¡�����Ϊ���ޣ���Ϊ���⡱����˾�գ��������ʡ�̫ҽ����Ҳ���
������������̫�ʣ��N���ڡ�����˾�գ�ֱ�Բ��䡣
�����������ڡ������������ˣ���˵���档͵�����ӣ��ٿ�������̫ҽ���ŷ�п���֪��
������������˾�գ�����ɱ�ġ��ѵ������е�������̫ҽ�ֱ�ԡ���
�������������������ӿ��ڣ��ŷ��������ǣ���̫���N�ڴˣ�˾�չ�Ŀ����
������������������̫���N�������ŷ�����Я�����粽���롣������������κΣ�ǰ�����أ�һ�����ơ��������ӣ�����˾�ա�
�����������ϵ£�ϸ���N����ʱ�����д������£��dz��ȵۣ���̫������Ҳ����
��������������˾�գ���֪�����ͯ�ӡ�����Ψ�ֲ��ϵ£������⣬������������������ᣬ������Ȱ��
������������������⣿�����ϵ£�ʤȯ���ա�
����������ʱ����̫��������̫�ͷ�נ�������ӣ�����ƫ���Ϊ�����ͯ�ӡ�����Ϊ�κ����ӣ�������ǧ��������������Ե�����ͯ���꣬ͯ���ȣ�һΪ�������ӣ�һΪ��̫���ӡ�Ȼ���������ӣ�����Ϊ�Ρ�˾�գ���ɱ������
����������Ŷ�������ϵ��ض��ɡ�
������������ǰ���κ�Я������ʿ�������ƽع��ӡ�����ͯ����ʣ�ͯ�����㡣��ȡͯ���ȡ����ǽ����������ӡ�ʹʧ���ӣ���̫��һ�����𡣱��С������گ���������������ӡ����Dz��У��������֡���������گ���������ںӱ���������ֶ֮����
��������������֮�⡣�κ�����������ʱ����Ǩ�������˷ǡ���ο�֤�����ع��ӣ������������ӣ����Ƕ�̫���ӡ�
�����������磬˾ֱ���ţ��ڰ����������м����ѳ���������顷�������̿͡�����֮�䣬���ޱ�Ȼ������
����������ʱ������̫���N�����أ�������������֮��������綼���ӡ�����֮�䣬�������Ǻϡ�
��������Զ���ܳƣ���֤��ɽ��ֻ��Ȩ�Ҵ��ɡ�
���������������������Ҳ�����������ˣ����ϵ���㶨�ƣ��������ٰ������ˡ���
�����������ڡ���������Ӫ�л���֮ʿ��������
�������������������������������
����������������
�������������£����ҡ����£����ҡ�����������֮ʿ�����´��������ڣ���ס�š�
�����������ǰ����������У���һ�����������족������گ������ɫ���ġ�
����������˾�գ�����Ҫ��ѯ�ʣ�����������֮Ů���ڡ���
�����������ף���������¶���죺��˾�գ�����СŮ����
��������������ƫ������ϵ²������ʡ�
����������δ�ڵ��С���������ʵ����
������������ʱ��������
��������������گ������
��������һ�нԲ��������ϵ����ϡ�
���������м�С������گ�����ر�ɭ�ϣ�����Ī�롣��ʷ���ˣ������������ȼ����ϵ¡��ٽ���ʩ��Ϊ������˾��ӡ�ţ�DZ��گ�����ڶ���һ�ţ���Ŀ��֮�¡��ö���֮�����ƻ���ľ������Ů��ʳĸ��Dz�ͳ���������Ϊ��������������м��ţ�����Ϊ�����ز�����©���������ϣ���ǿ������ǿ���֡������С�����类����ı�����ơ�
�����������������������䡰�������ԡ���Ȼ�������������Ƿ���֮�������У����ϵ£���ʱ�˿̣��붭�е�����ʡ�
���������������ˣ����ϵ���֪��š�
������������̿ͣ��dz����б��⡣��ʷ�ŵ��ӣ�������
����������ν��ƾͼƣ������������ǣ�����֮�ء�
�����������ϵ����Ե�����������������������������
�������������������������ƻ���������Ӫʿ��������Ѻ�´�
�����������ɷ�˵�����ϵ£���ȭ��������������Ƽݡ���
����������������ᣬ���������½׳��
���������������������ٺ��������£���ʷ��ة������˾��˾ֱ���ţ�����������
�����������������¡���
����������������
��������Ѫս���ա��綼���ơ�
�����������ϵ½�������������������������Է���Ժ��ô�λ���ڳй���У�ר�����ᡣ
����������ʱ������Ѷ����ٹ٣��Գ��ܵ���ͬ����飬�Ķ�������֮��������˷����������ߣ����Է������ӡ�
����������ƾ�ٹٴ�ǹ�ལ����֮�ʷ������ϵ£�����Σ��������һ�
����������ʷ��ة�������ԡ����Ű����ٴ���ӱ�������֮�£��ӳ����顣���˻���֮��Ҳ��
����������˾�����ơ�
�����������ڣ��綼���ӣ��Ƿ��¡��Zگ������λ���͡������ۡ��綼֮�䣬���ڡ��������Ļ̻̣�����һ�����飬�ܹ�������
���������綼��˾�ո���
���������ȹ۽����Ϸʺ����飬�ٿ���̫���N�������Ƕ�����������ʼ�ϲ����������ϣ���̫�ʣ����д�ı����
�����������ϵ£�����һЦ���������Ͻ��ڡ������Ӽ��Ů������̫�ʣ���������������ɽ�Ǯ��ӯ�����ҡ������ֻ�ͭ��ɽ���̲�֪�㡣�����С���Ŀ�����顯���Զ��ɽ�������壬�ɺ�����
�������������£�����Ϊ�����ظ漻���������Ž��ԣ���ֻ���붭̫�ʣ��Բ�����������α��֤����
�������������ɡ������ϵ£����мƽϣ������ȴ�����������
��������������֮�⣬�ȸ�ʷ����������������ᡣ
����������ȻҲ�������ϵ����У�һ����â��
����������������������ȴ�����Զԡ�
������������������ԡ�������α�������ۡ���֪���κ�����ͯ�ӣ��dz������ˡ����룬����������롣Ȼʷ����Ϸʺ����飬������Ϊ�档
��������ֻ���������¡�ҪɱҪ�У�Ϥ����㡣
��1��143������Ī��
�������������ܺ�����֮���顣���ϵ£�������£����ɺ�ǡ�
���������Ͼ�������Ѫ�𣬲������졣���ӣ��綼���ӣ����ݴ��ɡ�������ټ�������Ȼ���ϵ£���δ��ɱ�ġ����ӱ�����Է����ʱ��ɳ����ݡ�
����������˼ǰ�����ס�����������δǿ�ɡ�
�����������漻��������������ǰ����������Ȩ֮����һ�ԾŶ������ж��ۡ����ȸ�֪������һ�����£����ϵ²��Ҳ��ӡ���������������Dz������ǹʣ�Ȩ�����ף��ȸ�����ʷ����ǣ�����֮�ߡ�
���������������綼��������⣬�����������Բ��ϵ��ʰٹٹ��ǣ��綼�����ڽ���ֻ�벻����Ψƾ˾��ӡ�ţ����ܳ��ǡ����ϵ�����Σ�ѣ������綼��ʧ������������û��
����������ʱ������⡣
����������˵����Ұ���⣬��Ϊ�ܵ������������������ɡ��������ӣ�����ͬ���ο����������ݣ������������ͽ���������������壬������Ұ��
���������Զ���֮�ң����ϵ���ս�پ�������ס���������뺺�й��ҡ��ض�Ⱥ�ۣ���������Ϥ��Զ�ܡ��綼���⣬�Գɲ�˾�գ�һ���á��Բ��ϵ£�ֻ�����죬�����ɡ�
����������ȥ�������������Ψ��Ӧ�䲻������ʷ����ơ�˼�����������ϵ£��������š�Dz˾ֱ���ţ���������
����������ҹ��˾�ո���
�����������������ĸ�����ͨ������®�����Ͷ�̡���
����������®����ȣ������ϵ�����һ������������һ������
����������������
����������ȣ���������������š��ڽ����������˳ơ������ˡ���Ⱥ�ɻ���˼������ش���أ����ĺ��Ȼ����ϵ£��ز���ʶ��ð������������Ҫ�¡�
�����������ݼ�˾�ա���������ϵ�����Σ����ǰ�������������ں���ȣ�������ۣ����ɵ��ǡ�
�����������ĺ��������������������ϵ£����������
����������л˾�ա�����ȳ�л������
���������������������ϵ£��������ԡ�
������������������������ȴ�Ի�����³������������Դ�������磬��δ�������
�����������ĺ����Ϊ������������ȷ������������ϵ�����䱭���ʡ���ǰ���ٱ����֡������춯����ˤ��Ϊ�š����ҵ����֣�һӵ���ϡ����ɷ�˵������ȶ�����ࡣ�չ飬����֮�IJ����ޡ����Ǽ��������Ŵ����������������������Ǽ������࣬�ճ�˯���ѡ����ϵ����ǣ���������㣬�����������ܷ��������Ե������Ž����������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