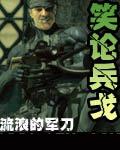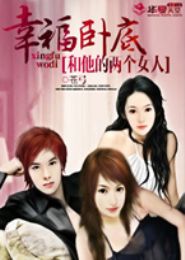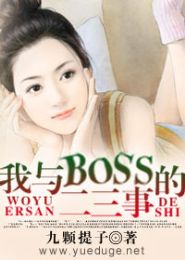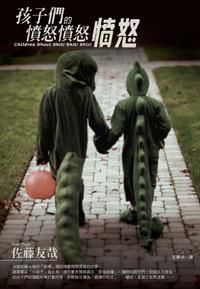愤怒的两晋南北朝-第18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1月15日,盖吴自称天台王,设立文武百官,与北魏政府彻底决裂。
拓跋焘相当不爽,经过一番部署,于446年正月14日,亲率大军先行讨伐变民首领薛永宗。
大军抵达东雍州,直逼薛永宗的大营,宰相崔浩进言道:“薛永宗不知陛下御驾亲征,军心一定松懈,现在趁北风强劲,应立即攻击,必能一击制胜。”
拓跋焘同意,两天后便包围了薛永宗的大营,薛永宗战败之后,与家人一起投汾水自杀。
薛永宗的族人薛安都,之前占领了弘农,得知拓跋焘亲征,且薛永宗已经兵败,自知无力对抗,果断放弃城池,南下投奔刘宋。
薛安都是当世虎将,加盟刘宋对于刘义隆来说,当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虽然刘义隆开始不觉,但惊喜就是因为在意外之时出现,才令人感觉赏心悦目。
拓跋焘几乎片刻也不想停歇,解决了薛永宗,立刻朝着盖吴推进。
正月17日,拓跋焘西渡黄河,抵达洛水桥,这时听说敌人驻屯在长安以北,认为渭河之北,田没有粮,野没有草,打算到渭河南岸,沿渭河向西。
但当他把计划告诉崔浩,却并没有得到支持,崔浩说:“打蛇要先打头,头如果粉碎,尾巴就毫无力量。
而今盖吴军营距离我们只有60里,用轻骑兵袭击,一天就可到达,一到就会把他击破。
击破盖吴之后,再南下长安,不过一天路程,多一日行军,没有伤害,如果到渭河南岸,则盖吴必定会从容不迫地进入北山,短期内就不容易剿灭了。”
这一次拓跋焘选择不接受,固执己见地沿渭河南岸,向长安进发。
正月26日,拓跋焘抵达戏水,盖吴得到消息后,果断焚毁了粮草辎重,纷纷逃入北山,魏军徒劳无功,且毫无应对之法,拓跋焘不禁大为后悔。
可惜后悔也不能做出任何改变,只能接受现状而已。
2月2日,拓跋焘还是如期抵达长安,悔恨之下,在周至、陈仓、雍城等所经之地,下令凡是与盖吴互通消息的汉人和其他非鲜卑人,全部杀无赦。
(本章完)
第376章 太武灭佛()
愤怒是人的通病,当自觉受到侵犯或是现实达不到心理预期,熊熊怒火就开始燃烧了。
但同样是愤怒,不同人的宣泄方式自然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些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解气了,有些人摔摔茶杯酒碗,最后怒气也能消散,还有些人像刘义隆和拓跋焘这种,手握大权,解决愤怒的办法就“高明”得多。
拓跋焘的暴脾气一早就显露了,相比刘义隆的不动声色,他是个典型的直肠子,喜欢就鼎力支持,不喜欢就立即刀剑相向。
盖吴起义使得北魏貌似平静的环境终于暴露出潜在的危机,这是拓跋焘绝对不想看到的。
地方官员贪污成性,这种事瞒不过皇帝的密探,但拓跋焘既无力解决,所以只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众顺从他的意思,糊弄地过日子也就是了,一旦把残酷的现实揭露出来,拓跋焘恼羞成怒之下,可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谓的农民起义,有时不能盲目定性,说是“逼上梁山”,或是“贱民就是矫情”,都不恰当,应该综合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既不能因为农民脆弱的表象而忽视其邪恶的内心,也不能无视他们求生求存的最原始最单纯的欲望。
北魏此时的大环境已然混沌不堪,虽然拓跋焘一统北方,可是相应的国家建设尤其吏治建设却没能跟上,而单纯依靠武力是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
因此盖吴的出现有其必然,盖吴本人固然有一定程度的投机倾向,可如果北魏民众生活愉悦,衣食无忧,也绝不会有那么多毫无关系的人群揭竿而起,跟着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冒着灭族的风险造反。
拓跋焘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固有观念的禁锢,或许军事成就十分可观,其他方面就稍显逊色,终究难望苻坚之项背。
杀掉那些与盖吴互通消息的人,拓跋焘怒气仍盛,于是做出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决定。
崔浩笃信道教,厌恶佛教,从未间断在拓跋焘跟前抨击佛教的虚无怪诞,还浪费大量资源和财产,应该铲除。
除了信仰矛盾,佛教发展到这个时期,内部确实出现许多问题,至于浪费资源和财产,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崔浩的建议还是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全是出于一己私愤。
但拓跋焘认为崔浩只是一心排除异己而已,担心会惹出大麻烦,并未对佛教赶尽杀绝,虽然颁布的政策很苛刻,但佛教仍有余地。
直到盖吴起义的出现,让佛教也随之遭遇重大危机。
拓跋焘抵达长安后,半好奇地进入了一间寺庙,于是一场祸事由此开端。
因为皇帝的到来,侍从官员依例在寺庙进行安全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在和尚卧室竟然发现好多武器。
拓跋焘听到报告之后,瞬间暴跳如雷,叫道:“这岂是和尚该有的东西,一定与盖吴勾结!”下令屠杀庙里的所有和尚,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而就在抄庙时,这场大祸终于走向高潮,将士们又发现了许多酿酒的工具和州郡长以及富豪委托寄存的财产,数目繁多,不可胜数,更发现几间窝藏美女的地下密室,经过询问得知,这些美女竟还都是被偷拐来的良家女子。
拓跋焘每听一项报告,心里就像被电击了一样,接二连三的怪事在寺庙发生,拓跋焘最后已合不拢嘴,脸色异常难看。
崔浩趁机进言,劝拓跋焘杀掉天底下的所有和尚,焚烧所有佛经,捣毁所有佛像。
拓跋焘听到这种建议,也不再感觉震惊了,为了保守起见,特别让人先四处调查其他地方佛寺的情况,结果与长安的大同小异,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慈悲为怀的幌子,极尽龌龊之能事。
于是长安的和尚先倒霉,全部被屠杀,佛经和佛像也被摧毁。
拓跋焘接着下诏给平城的留守朝廷,让留守朝廷通告全国,仿效长安模式,在国内开展灭佛运动。
诏书上这么说道:“从前东汉的昏君,迷惑于邪恶的假神,破坏伦理纲常,自从古代以来,九州之内从没出现过这种事!
言语荒唐,空话连篇,不合人情,在不安定的社会中,使人眼花缭乱,受到迷惑。
因此政治教育不能推行,礼乐仁义与之败坏,天下之大,全成废墟。
我继承天命,打算铲除虚伪,保护真主,恢复伏羲神农时的太平世界,其他的全都清扫干净,消灭到不留一点痕迹,从今以后,胆敢仍事奉胡人神祗,塑造偶像、捏泥人、铸铜人,全家诛杀。
有非常的才能做非常的事,除了我,谁能除掉这个多少年留下来的假神!
有关单位应通告全国各军区、各镇、各州,对辖区内所有佛寺、佛像、佛经,全都捣毁,所有僧侣不论老少,一律活埋坑杀。”
主持留守朝廷的太子拓跋晃,偏偏是虔诚的佛教徒,崇信佛法,之前就一直向父亲宣扬佛教的好处,但没有半点效果,现在佛教面临灭顶之灾,也没有力量扭转局面,只好尽量拖延诏书颁布的时间,使国内寺庙提早得到消息,各自逃生。
正是借着这个时间差,国内许多僧侣得以活命,部分佛像和佛经也得以保全,延续了佛教在北方的有生力量,为将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可是偌大的佛寺毕竟是躲不了的,更藏不下,北魏境内所有佛寺在短时间内全都被铲平,一座未留。
宗教信仰向来是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信仰对人造成的冲击更是火力十足。
对于个人而言,信仰是神圣的,但须知信仰本身其实有是非黑白之分,高低贵贱之别。
当有了信仰,势必冒死捍卫之,因此无论什么信仰,其实都潜伏着巨大的杀伤力。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选择信仰时,就显得尤其郑重。
世间宗教多如牛毛,究竟选择哪一个作为终生陪伴呢?
不同宗教的教义也许有很大差别,专家给予的评价也千奇百怪,但有个最基本的标准值得深省,是否会对旁人造成伤害?
不管引人向善还是引人向恶,只要不妨害旁人,大可肆无忌惮地信奉之。反之,可能其教义说的很冠冕堂皇,但当信奉之后,发现那些光明璀璨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无数人的鲜血和灵魂,仍然不能掩盖其邪教的本质。
这是关于真正“信仰”的逻辑,其实佛教发展到北魏时期,许多问题已脱离了信仰本身,成了被别有用心之人操控利用的工具,这也是遭到拓跋焘血腥镇压的根本所在。
当然在北魏国内是有相当一部分教众是严格信奉佛教教义的,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教义,当然算得上是乱世中的一盏明灯,是诸多苦难民众的心灵鸡汤。
如果拓跋焘是佛教徒,即便佛教内部出现问题,最后可能仍会包容,遗憾拓跋焘本就信奉道教,如今又逢敏感问题,佛教大劫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相比惩奸除恶的道教,急脾气拓跋焘当然选择后者,何况道士还能修仙长生(理论上说)。
(本章完)
第377章 陆俟奇谋()
这场浩浩荡荡的灭佛运动,让崔浩极为欣喜,终于完成了他多年来的夙愿,道教正式成为北魏国内一家独大的教派。
所谓物极必反,崔浩此时堪称位居自己的人生巅峰,从另一方面来看,还意味着他的人生马上就要走到下坡路,而且是急转直下。
因为他得罪了一个人。
虽然他平生得罪过无数人,但有个人却是他无论如何都得罪不起的,那就是当朝太子拓跋晃。
许多鲜卑官员与崔浩的关系也不好,但因崔浩是国家一品要员,所以没有哪个官员能挑战其权威,甚至拓跋焘也对他言听计从。
拓跋晃就不一样了,他可是尊贵的储君,未来的主宰,身边围绕一大群朋党,且都是为了捍卫太子荣耀和自己政治前途,而不顾一切的极端分子。
崔浩仗恃自己的才华和智谋,以及皇帝的宠信,在朝中独揽大权,异常强势,尤其在成功说服皇帝消灭(表面上)佛教之后,更加无所顾忌,认为国内已无人能找自己的晦气,除了皇帝以外,谁都不放在眼里——包括太子。
但崔浩聪明一世,终究在过于顺畅的环境里犯了平常人都会犯的错误,那就是得意忘形。
崔浩的两重身份就已经为他划定了行动的界限,一是汉人,一是朝臣。
在鲜卑人政权,汉人身份意味着他无时无刻不在经受鲜卑人的明枪暗箭,一旦被抓住小辫子,立即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
身为朝臣,无论做得有多成功,都只是皇家的服务人员,对皇帝和未来的皇帝(也就是太子)是最应该心存敬畏的,除非想要造反,不然就一定不能与他们对抗。
崔浩同时犯了这两项错误,一方面无视鲜卑同僚的威胁,另一方面还不把太子当回事。
因为灭佛一事,拓跋晃对崔浩恨之入骨,而崔浩丝毫不知收敛,曾推荐冀、定、相、幽、并等五个州的知识分子数十人,头一次起用,就让他们担任郡长。
以崔浩的能力和地位,做这些事原本也掀不起多大风浪,但却成了太子的突破口,在此大作文章,上疏拓跋焘说:“在此之前,征召延聘的人才,担任现在的职务已经很久,他们辛苦勤劳,还没得到回报,应由他们优先升任郡县长,崔浩推荐的人,则填补他们的空缺,况且郡县长的主要工作是治理人民,最好也该让有行政经验的人担任。”
但此时拓跋焘还对崔浩非常宠信,任由崔浩放手去做,崔浩便固执己见,终于分派那些人到职,让太子异常尴尬。
从此二人的矛盾越发深刻,终致不可调和,而最终拓跋焘还是选择站在族人和儿子这边,无情地出卖了昔日的战友。
那是几年后的事,实际上拓跋晃已开始暗中筹划扳倒崔浩了,一个天大阴谋悄悄酝酿着,主人公崔浩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大势将去,才追悔不及。
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未知,无论未来是喜是忧,听从内心的指引,一步步把未来变成当下,乃至过去,正是此生最大的意义所在。
当完成这些事,不论结局如何,已经是成功了。
当然不同的人,想法也千奇百怪,心中定义的成功更截然不同,未必都能悟透这一人生的本质。
聪明如崔浩,他追求的境界也超乎常人,试图把握精神的制高点,要将自己的意志传播大江南北,自己的信仰普及四海八荒。
这注定是一项万般艰巨的任务,但崔浩发现虽然有诸多问题,进展却还是不错的,于是更坚定了信念。
而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都注定由他全力承受。
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后果,而且不管中间多少曲折,最后都会施加在行为人身上,正如佛教所说,因果都在循环之中。
盖吴在国内引起这么大风波,最后也难免会吞食自己种下的果子。
446年2月,逃到北山之后,盖吴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毕竟微弱,于是再派使节到刘宋上疏刘义隆,请求派军支援。
刘义隆当即下诏,任命盖吴为关陇军区司令长官、雍州督导官,封北地公,下令雍梁二州出动武装部队,驻防边疆,作为盖吴的声援,并派使节送去印信121颗,让盖吴代替朝廷任官封爵。
然而盖吴并不解渴,处境并没有得以改善,前景不容乐观。
这时金城传来消息,当地人边固和天水人梁会,联合秦州益州境内各民族一万多户,占领了上邽东城,叛离北魏,周边的氐羌一万多人、匈奴休官部落和屠各部落二万多人,纷纷起兵响。
盖吴大喜过望,对未来不禁又充满了期待。
不过起义军虽然此起彼伏,但北魏国力还没有衰退得那么严重,并不致因为局面的叛变而危及全局。北魏秦益二州督导官封敕文,很快就斩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