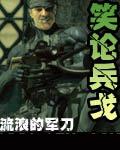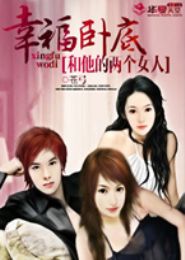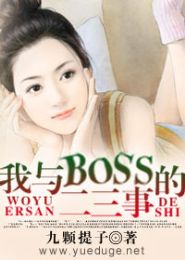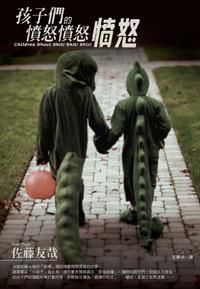愤怒的两晋南北朝-第2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朝廷中枢,这才有了后来的萧齐。
两人的遭遇也出奇的像,贾充与你起争执的时候,对方往往会拿这段黑历史朝廷讥讽,褚渊的性格低调得多,一般不跟人起争执,但仍挡不住四面八方的诽谤。
对于毫不在乎的人,任何言语的中伤都不过风吹日晒,根本不会往心里去,偏偏褚渊还极重名节,终于积郁成疾,在萧道成去世的同年即482年8月21日,就在家中永远闭上了两眼,享年48岁。
褚渊的儿子褚贲一向瞧不起父亲的作为,依例守丧三年之后,再也不出来做官,把南康公的爵位让给弟弟,他自己则退隐在父亲墓旁,直至老死,权作为父亲赎罪。
褚渊之后,当朝的红人们还有:萧赜的弟弟萧嶷、王僧虔和王俭叔侄、王晏、茹法亮、柳世隆、李安民、陈显达、王敬则、垣荣祖和垣崇祖兄弟、胡谐之、戴僧静、等等。
萧嶷身长七尺八寸,很注意自己的仪容形象,仪队和侍从们也都非常有礼,而他对哥哥十分崇敬,时时处处不忘君臣之别,任何事都不独断专行,开支也十分节俭,虽然贵为宰相,心细如丝,比地方官都要小心谨慎,所以萧赜虽对兄弟们猜忌,却始终待二弟十分优厚,萧嶷至死都是一身荣耀。
王僧虔和王俭都是琅邪王氏的领军人物,王导的嫡系后裔,靠着豪门世家的大背景,想被人忽略都难,稍微有点才华就更惹眼了,可惜王俭英年早逝,几年后就死掉了,不然应该能在后来的乱局中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
王晏也属琅邪王氏,但与王僧虔不是同一支,才华也有限,之所以受到器重,是因为高超的谄媚工夫,在萧赜没有称帝前,担任萧赜的秘书长,极力地奉承长官,后来萧赜称帝,顺理成章地把他提拔为心腹重臣。
茹法亮比王晏更会来事,虽是小吏出身,但把领导侍候好了,就是可以手握大权,牢牢掌控郡县长的升降调补,各地的贿赂每年多达数百万之多,他曾经在大庭广众下放出豪言:“何必靠那一点俸禄过活,就在这个大门里面,一年轻轻松到手一百万。”
王俭曾向萧赜反映,但萧赜认为这种人好管控,并不予处理。
柳世隆是柳元景的侄子,柳元景被害后,他也受到牵连,仕途失意,后来参与讨伐刘子业,重回朝中任职,并在地方当差时结识了萧赜,成了好友,萧赜上位后,果断把他提拔进中央。
李安民参与了代宋的多数战役,虽无大功,好歹混个脸熟,加上先前的告密之功,受到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陈显达这些人都是元老级名将了,为萧齐立下汗马功劳,不管哪个皇帝上位,都绝不能忽略他们的力量。
似乎“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真的成了一则真理,大到国内外,小到家内外,都概莫能外。
就算是普通百姓,有时也会觉得亲人不如外人值得托付,萧赜虽是一国之君,也有样的感慨,宁愿宠信茹法亮那种小人,对于自家兄弟却总是不能做到心无旁鹜。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当事人,只因越是关系亲近,越是放得开,很少能保有起码的互相尊重和敬畏。而正因关系亲近,当事人遇到这种情形,往往就觉不能理解,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不能像外人那样可以设身处地地进行体谅。
萧嶷之所以会被重视,与早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包括联合对抗父亲、全力协助称帝、等等,后来处事也是如履薄冰,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觉悟。
萧道成临终时,曾特别嘱咐萧赜,要让萧晃留在京师或京师附近任职,不要派到偏远的地方,同时告诫说:“宋国如果不是骨肉互相残杀,别人怎么能乘机兴起,你们要引以为戒。”
类似的话,几乎每个朝代的开国君主都会说,然而后来若干年后也总是会发生萧墙之乱,这是个怪圈,古往今来的统治集团都在圈子里难以跨出半步。
萧赜这一代还是不错的,虽做不到苻坚那样宽宏大度,但也并没有步刘宋皇帝的后尘。
484年10月18日,萧赜征召南徐州督导官、长沙王萧晃进京担任立法院副总立法长。
按照一惯的规矩,亲王在京师只可拥有武装侍卫40人,而萧晃喜欢威风,离开南徐州时,秘密运送数百人使用的武器回到建康,被治安稽查官查获,就要没收,萧晃一时兴起,竟把纠察员投进长江。
萧赜得到报告后大为愤怒,打算把他交付军法审判,萧嶷不住叩头求情说:“萧晃的罪固然不可宽恕,但陛下应想到父亲对他的钟爱。”
萧赜赶忙扶起他,也跟着流下了泪,终于对萧晃不再有杀机,但也不再亲近。
武陵王萧晔的性情也有点直率轻狂,有一次到皇宫参加御宴,喝到半醉趴到地上,帽侧的貂尾都沾上了肉汁,萧赜笑道:“肉汗把貂尾都弄脏了。”
萧晔不假思索地答说:“陛下爱惜羽毛而疏远骨肉。”
萧赜顿时黑脸,但并没有被愤怒支配头脑,仍然是只做到不亲不疏而已。
“克制”是统治者的必修课,这门课不过关,很难有所作为。
不论是愤怒还是欲望,如果不能很好地克制,后患无穷。刘宋后来的皇帝们就是过于肆意妄为,终于灭门亡国。
这一时期的中华大地上,南北两个大国的统治者还是比较理智的,倒是塞外的柔然汗国,有点“胡作非为”的意思。
早在464年7月,雄壮威武的郁久闾吐贺真逝世后,儿子郁久闾予成继位,也是从那时起,柔然汗国才开始有了纪年。
郁久闾予成也不时挑衅北魏,当然也总是以失败告终,后来开始秘密联合南方的萧齐,约定夹击北魏,但路途遥远,配合并不容易,一直到死也没能取得突破。
485年底,郁久闾予成逝世,儿子郁久闾豆仑继位。
豆仑是个大人物,注定留名史册的人,他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把汗国推向没落,生性残忍凶暴的他,部属不过规劝了几句,竟灭了别人全族,部众开始离心。
一直到487年8月,豆仑不顾内部危机四伏的现状,再度攻击北魏边境,结果损失惨重,国内怨声载道,高车部落酋长阿伏至罗,拥有部众十余万人,一直都是柔然汗国的藩属,眼见豆仑越发肆意妄为,苦劝无果之下,愤然脱离柔然,与堂弟阿伏穷奇,率部众向西进发,自称高车国王。
兄弟俩感情亲密,分别统御各人的部众,阿伏至罗在北,阿伏穷奇在南,部众尊称阿伏至罗为候娄匐勒,即天子,尊称阿伏穷奇为候倍,即太子。
豆仑此后多次攻击高车,但都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只好向东迁移,以致内乱越发激烈,昔日繁华不再。
(本章完)
第429章 冯后之死()
北魏也有很多知名的文臣武将,只因统治者的风采更加夺目,所以在世人眼中并不算突出。
即便如此,仍有一人足够吸引举国的注意力,那就是高允。
高允的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资历上面,毕竟在那个年月,能在政坛活跃半个世纪的人物并不多见,寿命到50岁的人都是少数。
时任高级国务官的咸阳文公高允,一生事奉了五位皇帝,在朝廷三个院都担任过要职,凭借老实憨厚的形状、朴实无华的性格和中庸的政治手腕,前后50多年没有受到责罚,冯太后和拓跋宏都对他十分尊重,在他进宫的时候,总是让禁宫高级侍从官苏兴寿,下台阶搀扶。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高允,晚年生活越发简朴恬静,虽然身居高位,但心情与普通百姓一样,早晚读书,教导身边的人向善学好,亲朋旧交也从不忘记。
拓跋弘当年夺取刘宋的青徐二州时,把当地有声望的豪门强族,都迁移到平城,其中很多人都与高允有着亲戚关系,高允倾其家财对他们进行援助救济,让他们得到安顿,又在其中遴选有才能的人,向朝廷推荐。
类似的事例有很多,高允在国内的威望与日俱增,冯太后和拓跋宏显然已把当国家的吉祥物来对待了,待遇颇厚。
高允平生很注意保养,一直没生过大病,487年春节刚过,略微感觉有点不舒服,但起居作息仍和平常一样,但几天后便在睡梦中离世,享年98岁,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死亡。
北魏朝廷特别追赠他高级咨询官、最高监察长,丧礼十分隆重,对高家的赏赐也十分优厚,自从北魏建国以来,对逝世官员的赏赐从没这么多。
另有为孝文改革出谋划策的谋臣们,或许知名度不如高允,但也堪称国家的栋梁,任城王拓跋澄,齐州督导官韩麒麟,监察院皇家监察官李安世,皇家图书馆主任高佑,员外散骑侍从官李彪,等等。
拓跋澄是拓跋宏的堂叔,性情沉稳,做事老练,是拓跋宏最得力的皇族助手。
韩麒麟多次上疏献计献策,包括在北方六镇兴筑长城,防御柔然的入侵,禁止奇珍异宝的流传,简化丧葬仪式,鼓励人民耕田种桑,捐税少征丝绸、改征谷米。长城一事并没有下文,但其他举措,拓跋宏很快就给出了积极回应,是孝文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安世最大的贡献当然就是均田制,可谓惠及后世的良策。
高佑针对官场的混乱局面,提出只认人才、不问关系的用人办法,认为帝王可以因私人的喜好而赏人钱财,但绝不可因私人的爱恶而委派官职。
拓跋宏对此十分欣赏,但他作为关系户的铁粉,却终于没能落实这一办法。
高佑后来出任西兖州督导官,镇守滑台,认为郡和封国都有学校,县和村应该也有,创造性地下令设立县级初级中学和村级小学。
李彪曾作为使节先后六次出使萧齐,口才和应变能力在国内无人能及,也为孝文改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痛陈奢侈浪费之祸,提议建立粮仓备灾,广泛选拔黄河以南的人才,重视亲情,提倡孝道,等等。
除了这些人,北魏幕后的那个大人物当然是最不容忽视的,冯太后纵横北魏几十年,绝对是整个南产朝时期最有成就的女人,也一定能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名列前茅。
然而就算是活了近百岁的高允,毕竟也有离开人世的一天,冯太后并没有那么长寿,49岁就病逝了。
进入490年,冯太后的身体就已不堪重负了,拖了大半年后,于9月18日驾鹤而去。
她的死揭露了一个奇异的现象,那就是孝文帝的“孝”。
关于拓跋宏的孝顺,冯太后在世时已表现得很充分了,被各种打骂都不记恨,甚至在冬天被关进小黑屋里忍冻挨饿也不记仇,但这些相比他在冯太后死后的表现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从冯太后去世当天起,拓跋宏一连绝食五天,而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他几乎什么事都没做,把全部精力用在哭丧上面,朝臣也跟着没做别的事,把全部精力用来安慰他们的皇帝。
中部总监司法官首先劝说:“陛下承受祖先交付的大业,君临万国,责任至为重大,怎么能像一个平民为了讲究小节,而让身体受到过分伤害?”
拓跋宏于是吃了一碗稀饭,但之后又继续绝食。
接下来各大王爵公爵全都到宫门外跪求指定冯太后的安葬时间,并请拓跋宏遵照冯太后的遗言,安葬后赶紧脱下丧服,让国事走向正轨。
拓跋宏哭着下诏:“自从灾祸降临,恍惚之间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我侍奉太皇太后的灵柩,仿佛太皇太后仍在人世,你们竟然说把她老人家下葬,我实在不忍听!”
接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王公贵族们不断上疏请求,拓跋宏终于松口,但只同意下葬,不同意脱掉丧服。
10月4日,拓跋宏亲自前往方山的永固陵安排下葬事宜,下诏让平时出动的仪仗队全都停止,只保留武装警卫作临时戒备。
冯太后不想与丈夫合葬一起,所以几年前就在方山修建了自己未来的陵园——这在男权社会,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冯太后用行动诠释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真谛。
10月9日,死了20天的冯太后终于入土为安。
百官都以为皇帝终于不用再闹下去了,拓跋宏却仍不罢休,答应不再绝食,但坚持不脱丧服。
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拓跋丕(拓跋宏的族人,非拓跋焘的弟弟)建议说:“我们的年纪都已衰老,但事奉历代圣明君王,对帝国的前例旧典,自问相当熟悉。
回想祖先们故去之时,只有侍从灵柩的人才穿丧服,其他的人一律仍穿平时的衣服,一直遵循到今天,从来没有更改。
听说陛下三餐吃饭,不满半碗,无论昼夜,不解除系在腰上的麻带,我们捶胸顿足,坐立不安,愿陛下稍微克制亲慕之情,遵守先朝立下的旧有典章制度。”
拓跋宏说:“哀痛到极点,伤害身体是常有的事,不必特别关注,我早晚吃稀饭,健康勉强可以维持,诸公何须忧愁恐惧?祖宗在世时,专心军事扩张,没有时间讲求文化教育,我如今接受圣人教训,学习古代典范,无论时代或人事,跟先世已大不相同,各位都是国家元老,朝廷命脉所寄,然而对儒家经典和古代丧礼,恐怕并不熟知,我会把心中所挂念的问题,提出来与政府行政官游明根、高闾等人讨论,诸公可以留心细听。”
这段话才是拓跋宏的心声,尤其最后几句,是精髓所在。
冯太后杀了拓跋宏全家,包括父亲、母亲、以及母亲全家,当时他虽年幼,但并不致狗屁不通,尤其成年后,自会听说冯太后的所作所为,对这样一个大仇人,如何爱得起、孝得起?
但拓跋宏做到了,这与他自幼就被冯太后抚养,有着莫大关系,从小就产生了一种依恋,就算长大后,也被冯太后包裹得严严实实,而冯太后手握大权,能力出众,性格豪爽,颇具女汉子气质,长相还很美艳,因此很有异性缘,无数男人拜在她的石榴裙下,拓跋宏也不例外,对这个奶奶既怕又爱又敬,唯独恨不起来。
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掩盖仇人这个身份,拓跋宏自始至终都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