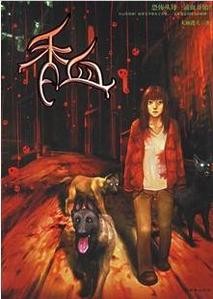香血-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别多?
在医院挂号大厅里,我被一个人叫住了。
是秀娥。
她手里拿着一本病历,分开密集的人群,慢慢朝我走来,脸上勉强露出一丝微笑。她的腿还没好利索, 仍旧有点跛。
“秀娥姐,你怎么在这里?生病了吗?”我迎上去问。她单薄的身子,看起来就不是很健康,何况以前 郭德昌也说过,她总是生病。
秀娥点点头,叹了一口气,将手里的病历在我眼前晃了晃,无力地道:“今天上午从公安局回去后,就 开始拉黑色的大便——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医生说是胃出血——以前都是德昌背我来的,我也不知道医院 的规矩。”说着她低下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捂在眼睛上,无声地哭泣起来。那条手绢已经湿漉漉了, 看来她已经掉了很多眼泪。
我也叹了一口气:“你挂号了没有?”
她摇摇头,为难地看着挂号处汹涌的人头。因为人多,那里的队伍已经变形,靠近窗口的地方挤成一锅 粥。秀娥大约已经很多年没有单独出过门,面对这样的阵势,怪不得她到现在还没有挂上号。我接过她手里 的病历,努力挤进人群给她挂了号。
“奇怪,这个小医院怎么生意这么好?”
“不知道,以前德昌带我来的时候,这里很冷清的。”
我看她一眼,带着她到门诊处。那里也排了长长一溜人,我将她的病历和挂号单交给护士,陪着她在走 道里的长椅上坐下。
“其实德昌出事,已经有过预兆了。”她沉默了一阵,忽然冒出一句话。
“哦?”
“今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牙龈出了很多血,连下巴上都沾满了,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 情——牙龈出血,是要死亲人的。”她幽幽地说,又哭了起来。
“你不是说那不是郭德昌吗?”
听我这样说,她立即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如果不是德昌,为什么会长得和他 一模一样?我……”她说不下去了,看得出她心里很乱。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终于等到医生叫秀娥的名字,她对我点点头,便进去了,手里紧紧地握着那个 装着她粪便的小玻璃瓶子。
我坐在走道里等她的时候,给江阔天打了个电话,问他有什么新的线索没有。
“有。”江阔天说。
我等了一阵,可是他一直在沉默,这让我有点恼火:“你是不是不想告诉我?”
“不是,”他终于说话了,“最后两双脚印的检验结果出来了。”
“哦?”
“男的是你,女的,”他停顿一下,“是秀娥。”
秀娥?
我惊讶不已,旋即又释然:“也许是她去探望郭德昌的时候留下的?”
那边的声音仿佛有点抑郁:“不是,根据现场分析,秀娥的脚印,应该是在凌晨一到两点之间留下的, 但是她的口供却说,她当夜10点多钟就已经睡了。”
我的心骤然沉重起来:“没有弄错?”
“没有。”
我看看走道尽头的诊室,那里站满了等待看病的人,病恹恹的秀娥,正在里面接受医生的检查。
难道这样一个秀娥,竟然会和郭德昌的死有关?
“还有其他情况吗?”我问。
“没有了。哦,对了,那把匕首的主人已经找出来了,是个惯偷,我们的人已经去找他了。”他说,“ 沈浩没事吧?”
“没事。”我挂了电话。
我将身子往后一靠,顾不得墙壁多么肮脏。
我多么希望,秀娥和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或者说任何迹象,可以把秀 娥与郭德昌的死联系起来。如果要给她下一个定义,那么最好的词应该是——卑怯。是的,秀娥就是这么一 个人,她的眼光总是怯生生的。
“东方。”又是那个怯生生的声音,秀娥不安地站在我眼前,将我从沉思中唤醒。我仔细地看着她,她 的表情也怯生生的,现在被我这样一看,更加增添了惶恐和不安——这是不是她心虚的表现?但是她平常也 是这样一副表情,似乎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东方,”她紧张地看看我,我的审视被她察觉了,她眼光闪动,慌乱地道,“医生要我去化验,如果 你没空,不用陪我了。”
我赶紧收起目光,仍旧陪着她做完了化验。
化验的结果,她的腹部大量出血,必须住院治疗,并且要输血。我没想到她病得这么严重,她也吓了一 跳,原本苍白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帮她办理好住院手续,安顿好后,我才离开。
急诊病房里,仍旧只有庄弱貂和沈浩两个人,沈浩没有知觉。我进去的时候,庄弱貂正在看病历,我咳 嗽一声,她这才发觉我来了,抬起头来,从口罩后露出一个微笑。
我本来想要和她说的话,被她的微笑融化了,吐出来变的不太连贯:“庄——庄——庄小姐!”说完这 一句,我已经满头大汗,再也不敢说话了。
我这是怎么了?我在心里暗暗甩了自己一个耳光——真是没出息。
但是庄弱貂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她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又害怕靠近。自成年以来,从来没有 一个女子这样吸引我。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
庄弱貂被我的窘态逗笑了,眼角弯得像一弯月牙,盈盈发亮地看着我,光线在那双眼睛里,仿佛会跳舞 ,具有别样的生命力。
她的笑声让我不那么紧张,终于可以正常说话了。
“你什么时候下班?”话一出口,我便后悔了——哪有这么直接问人家的?看她的气质,是那种很乖的 女孩,多半不会接受一个陌生人的邀请。
她的眼睛仍旧是弯弯的:“还有半个小时,你呢?”
“我随时——我是自由职业者。”
“哦,那我们可以一起走。”她说得非常坦然,一点也不扭捏,让我刮目相看。
“好,我在外面等你。”我喜出望外。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庄弱貂出现在医院门口时,已经换了一副装扮。她终于摘下口罩,露出了面容。
我果然没有猜错,她的确很漂亮,但不是都市中那种流行的美。她的皮肤非常细腻健康,带点微微的黑 色,有点像山地人的肌肤。脸是天然的,没有任何化妆品的痕迹,也没有任何一点瑕疵,五官精巧而细致, 凑在一起,整个脸盘就像银币一般,闪着异样的光彩。那身绿色的裙子,给她带来一丝山野气息,加上她富 有弹性的步调和柔韧的腰肢,使她看起来简直像个来自山林的小妖女。
“你身体很好啊。”我不由自主地说。
她奇怪地看我一眼:“你怎么知道?”
我微笑一下,没有回答。
我怎么不知道?你这样青春健美、朝气蓬勃,一看就充满了活力。
“庄小姐,你家住哪里?”
“叫我貂儿吧,他们都这样叫我。”
“貂儿?貂儿,貂儿,很好听的名字——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
“貂是一种很仁慈的动物,当它在雪地里看见有人快冻僵时,便会跑过去,用自己的身体将人温暖过来 。很多猎人就利用貂的仁慈,来捕捉貂。貂虽然知道那个倒下的人有可能是猎人,但是还是无法抗拒自己仁 慈的天性,依旧跑过去救人。”她说着,望着我,“你说貂是不是很傻?”
我摇摇头,她的故事让我动容:“不是貂傻,是人太残忍。”
她抿嘴一笑:“妈妈希望我像貂一样仁慈,所以给我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原来如此。
我看着她,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她,我就觉得心情愉快。
夜幕微垂,貂儿在我身边,话渐渐多了起来,呱呱叽叽说个不休,我用心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
我们都走得很慢,刻意放慢脚步,慢慢地走。
从来没有一个黄昏,有这么美好。
原来貂儿就住在我家附近的那片小区里,我暗暗欣喜——近水楼台,以后要找她就更方便了。
貂儿就像孩子一样单纯,比现在很多中学生都要单纯,她仍旧遵循着很久以前那种古老的道德,仿佛没 有被这个世界污染过,一路走来,所有的乞丐都被她施舍了个遍。
“他们也许是骗子。”我说。
她笑了笑:“也许不是。”
她仍旧继续在施舍她的钱财,我没有阻止她。我想起她所说的貂的故事,到底是她太傻、还是别人都太 冷漠?
我喜欢这样的貂儿。
在她施舍硬币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
我们走的这条路,靠近城市中心,属于繁华地带,平常都有很多乞丐在这一带行乞,他们身体的不同部 位有着残疾,肮脏不堪,有时候人们会为了结束他们的纠缠而扔给他们一两枚硬币。那些乞丐,残疾程度都 非常严重,基本上都是坐在地上,仰视着来往的众人。
但是今天,我和貂儿走了这么久,却只见五六个健康的乞丐出现,那些残疾的,仿佛都罢工了一般,消 失在他们平常的地盘上。
“怎么了?”貂儿注意到了我的疑惑。我说了出来,她笑了笑:“那不是很好吗?也许他们的病都好了 。”
我苦笑一下,没有再说。她太单纯,总是希望事情能够有美好的结局,可是我知道,那样严重的残疾, 一个乞丐,是绝没有钱来治疗的。
我叹了一口气。
手机铃声响起,是江阔天打来的。
“什么事。”
“发现了一点线索,你能来吗?”他在那边报了一个地址名,那是在我住的小区附近的一条巷子。
“好。”
挂了电话,我歉意地正要对貂儿说什么,她已经顽皮地笑了笑:“你要工作去了?我自己回去好了。”
说完她对我摇摇手表示告别,迈着她特有的弹性步伐,朝前走去。
我看了她一小会,便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上没有堵车,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在那条小巷门口,我才一下车,便嗅到了那种芳香。香味很淡,一丝丝漂浮在空气中。巷子口停着几辆 警车,一些警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几只雄壮的狼犬兴奋地跳跃着,不时发出雄壮的叫声。江阔天远远看见 我,朝我招了招手。
“发现了什么?”我走过去,一只警犬在我身边擦身而过。
“暂时没有,”他摇摇头,“指纹库里没有凶手的指纹,我们先调几头警犬来试试。”
用警犬是个好主意,这起案子最重要的线索就是这种独特的芬芳,这种芳香,连我这样嗅觉不灵敏的人 ,闻过一次也无法忘记,何况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警犬?这几只警犬毛色油亮,身材高大威猛,据说是经验丰 富的功勋犬。它们在附近走来走去,鼻子不断朝空中翕动,时不时从喉咙深处爆发出一阵阵的呜咽,同时猛 然朝上一蹿,似乎要捕捉高空中的什么东西。它们的脖子上套着结实的皮项圈,每当它们朝上蹿动,项圈便 自动收紧,将它们勒了回来,这让它们愈发烦躁不安。
“它们的表现很奇怪。”训导员一边使劲拉着它们,一边告诉我们。
功勋犬都是警犬中的精英分子,身经百战,早就锻炼了一副钢铁神经,遇事冷静沉着,从来不会因为任 何情况而惊慌失措。而这几只功勋犬的表现,十分反常,让训导员感到很奇怪。
我注意地看了看警犬们,不知道它们这样反常的举止,是不是和空气中的香味有关?
正思索间,一头警犬突然仰天发出一声长啸,宛如狼嚎,穿越城市中浮满灰尘的黄昏,传到很远的地方 。其他几头警犬被它这么一叫,也跟着叫了起来。
月亮已经出来了,夜色渐深,野性渐露的警犬们,将铁链拉得铮铮作响,仿佛随时要脱缰而去。训导员 们用两只手全力以赴,也无法控制这些狼的后代,被它们拖着,朝夜色苍茫的小巷深处狂奔而去。我和江阔 天互相看了看,也放腿追了上去。小巷十分狭窄,警车无法进入,除了几名司机留守原地外,一起来的警员 全都跑了起来。月色下,人和狗发出不同的喊声,惊扰了这个黄昏的安宁。
跑了不知多远,警犬们在一栋楼房前停了下来,原地跳跃着,向训导员们呜呜示意。
我们跟在他们身后,远远的,还没有靠近这栋楼房,便感觉香味突然变得浓烈起来。越靠近楼房,香味 便越是浓烈。
我心中忽然产生一种不好的预感,随着香味的愈来愈烈,这种预感也越发强烈,但是我无法说出那是什 么。
我们默默上楼,停留在三楼的一户人家前,香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这户人家房门打开,没有开灯, 屋内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只依稀望见一些家具的影子。
“有人吗?”江阔天叫了两声,无人应答。警犬门对着屋内狂吠,再也不肯移开半步。江阔天和我疑惑 地对望一眼,我想他一定和我产生了同样的预感,我们都模糊地感觉到恐惧,却又无法捕捉,不知道将要发 生什么。江阔天的身份和我不同,我习惯于看清形势再决定行动,而警察有时候是不能等待的,比如现在。 他看了看我,没有犹豫多久,便走进屋内,按了电灯开关,一线光华从屋顶照射下来,刹那间便驱走了所有 的黑暗,整个房间暴露在我们面前。
一个人静静地俯卧在客厅的地板上,那种姿态,十分熟悉。我默默回想这种熟悉的感觉来自何方,而江 阔天已经走上去,轻轻扳着那人的肩膀,将他的身子翻转过来,让他正面朝上——随着那人身体的翻动,空 气中氤氲的香气微微荡漾,冰冷地粘到我们的身上。
仍旧是这种奇特的芬芳!
郭德昌死的时候,沈浩受伤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