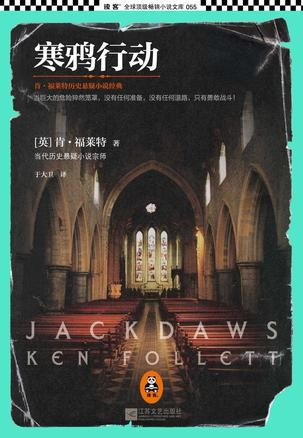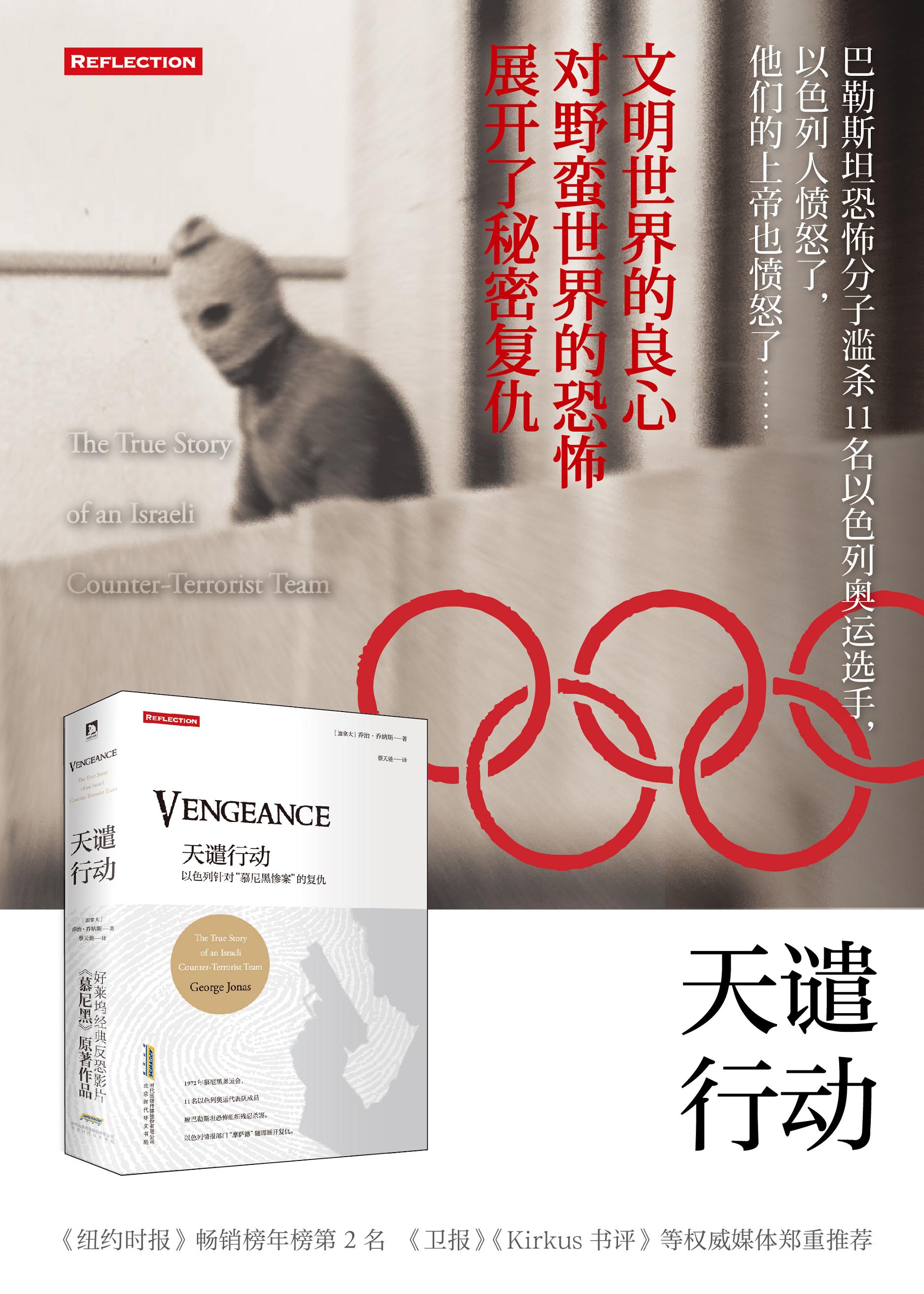寒鸦行动-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弗立克想,不知道里兹大饭店的人多久以后才会向盖世太保报告戴安娜和莫德的出现。他们大概马上会发现这两个女人不同寻常。她们的证件上写的是在兰斯工作的秘书——这样的女人来里兹干什么?在被占领的法国,按说她们的穿戴还算体面,但看上去显然不是典型的里兹主顾——里兹的客人们都是来自中立国家的外交官夫人,黑市商人的女伴,或者德军军官的家眷或情妇。饭店经理本人可能不会做什么,尤其他要是也反对纳粹的话,但盖世太保在城里的每个大饭店和餐馆都安插了眼线,他们专门靠汇报身份可疑的陌生人获取赏钱。这种常识细节在特别行动处的训练中会灌输给每个学员——但整个课程要进行三个月,戴安娜和莫德只用了两天。
弗立克加快了脚步。
35
迪特尔几乎精疲力竭。为了在半天之内印制、分发这一千张布告,他又是劝说又是恐吓,把身上的所有气力都用尽了。他可以一直保持耐心,坚持不懈,必要时他也可以勃然动怒,大发雷霆。此外,头一天晚上他一直没有睡觉。他的神经发颤,头很痛,脾气愈发急躁。
但是,当他进入坐落在犬舍门、俯瞰布洛涅森林的公寓大楼时,立刻感到一股平和的气息降临在他身上。他为隆美尔做的这项工作要求他在法国北部各处旅行,所以他必须将总部设在巴黎,但弄到这么一块地方必须采用各种贿赂和恐吓手段。它的确值得迪特尔这么做。他喜欢这暗色的桃花芯木镶板、厚重的窗帘、高高的天花板以及18世纪的餐具柜中的银器。他在凉爽、昏暗的公寓里走来走去,重新认识他的那些珍爱之物:一只罗丹雕塑的手,一张德加的粉彩画,上面是芭蕾舞女在穿舞鞋,《基督山伯爵》的第一版珍藏本。他坐在施坦威小型三角钢琴前,弹奏起爵士名曲《是否老实》的散漫变奏:
没有人倾诉,只有我自己……
在战前,公寓和大部分家具属于一个来自里昂的工程师,他靠制造小型电器、吸尘器、收音机和门铃而发迹。迪特尔是从他的邻居,一位有钱的寡妇那里得知这些的,她的丈夫曾是三十年代法国的法西斯党的领导人物。她说,这个工程师是个庸俗的暴发户,他请人选择搭配合适的壁纸和古董,但搜罗这些精美的物件只是为了取悦他妻子的那些朋友。他后来去了美国,那儿的人全都庸俗不堪,寡妇说。她很高兴这套公寓现在有一个真正欣赏它的房客。
迪特尔脱掉外套和衬衣,把脸和脖子上沾染的巴黎的污垢清洗掉。然后他穿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衣,在法国式的袖口插上金链扣,选了一条银灰色的领带。他一边系领带,一边打开收音机。从意大利传来的都是坏消息。播音员说,德国人在激烈奋战,严守后卫。迪特尔推测罗马最近几天就会失守。
但意大利不是法国。
他现在要等待有人发现费利西蒂?克拉莱特。当然,他不能肯定她会经过巴黎,但除了兰斯以外,这里无疑是最有可能发现她的地方。不管怎样,他也只能做这么多了。他真希望他能把斯蒂芬妮从兰斯带来。不过,他需要让她占着杜波依斯大街上的房子。可能会有更多的盟军特工降落地面,找上门来。重要的是巧妙地把他们引入罗网。他已留下指令,他不在的时候绝不能拷打米歇尔和鲍勒大夫,他留着他们还有别的用处。
冰箱里有一瓶唐培里侬香槟。他打开瓶塞,往一只水晶高脚杯里倒了一些。然后,带着一种美好生活的心境,他在桌边坐下,读他收到的一封来信。
信是他的妻子沃特劳德写来的。
我亲爱的迪特尔:
我很遗憾我们不能在一起庆贺你的四十岁的生日。
迪特尔把自己的生日都忘了。他看了看卡地亚座钟上的日期。今天是六月三日。今天他就满四十周岁了。他又倒上一杯香槟以示庆祝。
他妻子的信封里还装有另外两封信。他七岁的女儿玛格丽特(大家都叫她茂西),给他画了一张画,画上他穿着军装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面。画里面的他比铁塔还高:小孩子都是这么夸大自己父亲的。他的儿子鲁迪十岁,写的信更像一个大孩子,用的是蓝黑色的墨水,字体精致圆润。
我亲爱的爸爸:
我在学校里表现很好,但里希特博士的教室被炸毁了。幸运的是当时是在夜里,学校里面没人。
迪特尔痛苦地闭上眼睛。想到自己的孩子们居住的城市挨了炸弹,让他实在无法忍受。他诅咒着英国空军的杀人凶手,尽管他很清楚德国的炸弹也投向英国学校的孩子们头上。
他看着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算给家里打个电话。电话恐怕很难打通,法国电话系统超载,加上军事通话优先,私人电话可能要等好几个小时才能接通。不过他还是决定试试。他突然十分渴望听到他的孩子们的声音,让自己确信他们仍然活着。
他正要去抓电话,它却抢先响了起来。
他拿起听筒:“我是法兰克少校。”
“我是黑塞中尉。”
迪特尔的脉搏快了起来。“你已经找到费利西蒂?克拉莱特了?”
“没有,但有件事情也一样不错。”
36
弗立克曾来过里兹一次,那是战前她在巴黎上学的时候。她跟一个女友戴着帽子,脸上化了妆,还穿戴了手套长袜之类,从大门走进走出,就好像她们每天都过这种日子一样。她们去饭店内部拱廊里的商店转悠,冲着那些围巾、自来水笔和香水上标着的荒唐价格傻笑。她们坐在大厅里,装作在等一个迟迟不到的人,对那些进来喝茶的女人的穿着说三道四,而她们自己连一杯白水都不敢点。那些日子,弗立克省下每个便士去买法兰西剧院的便宜票。
法国被占领后,她听说主人试图尽量把饭店正常经营下去,尽管很多客房都被纳粹头目长期包租下来。她今天既没戴手套,也没穿长袜,但她给脸上扑了粉,时髦地歪戴着贝雷帽,她指望战时来饭店的主顾有些也跟她一样,不得不在装扮上马虎一点儿,得过且过。
在饭店外的旺多姆广场上,停着一溜灰色的军车和黑色的高级轿车。在大楼的正面,六面猩红色的纳粹旗子炫耀般地在微风中呼啦啦摇摆着。一个戴着高帽子、穿红色长裤的门警怀疑地打量着弗立克和鲁比,说:“你们不能进去。”
弗立克穿的是淡蓝色的套装,到处皱皱巴巴,鲁比穿着一件藏蓝色长衣,外加一件男式雨衣。她们穿的不是在里兹大饭店用餐的衣服。弗立克试着模仿法国女人被下等人激怒时的傲慢样子。她把鼻子往上一扬,问:“怎么回事?”
“这个入口是给高层人物预留的,夫人。即便德国上校也不能从这儿进,你绕到附近的康朋街,从后门进去。”
“随你了。”弗立克用一种厌倦的口气,颇有气度地说。但实际上,她倒十分庆幸他没说她们的装束不得体。她和鲁比快步绕过街区,找到了它的后门。
大厅里灯光明亮,两侧的酒吧里坐满了穿晚礼服或者制服的男人。交谈汇集的嗡嗡声中满是德语的辅音,而不是法语那懒散的元音。这让弗立克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敌人的据点。
她走到办事台那儿。接待员穿着嵌了不少铜扣子的大衣,仰着鼻子看着她,看出她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法国富婆,便冷冷地说:“什么事?”
“查一下罗格朗小姐是否在她的房间里,”弗立克用命令的口气说。她估计戴安娜会使用她的假名字——西蒙娜?罗格朗。“我跟她约好了。”
他后退了一步,问:“我能告诉她是谁找她吗?”
“马蒂尼夫人。我是她的雇员。”
“好的。实际上,小姐跟她的女伴正在后面的餐厅里。你可以去找侍者领班。”
弗立克和鲁比穿过大厅进了餐厅。这里呈现的是一幅上层生活的图景,白色的桌布、银制的餐具、闪烁的烛光,穿着黑色制服的侍者托着菜肴食物在屋里滑来滑去。看到这种场面,没人会想到眼下一半的巴黎人正在忍饥挨饿。弗立克闻到了真正咖啡的香气。
刚在门边停下,她就立刻看到了戴安娜和莫德。她们坐在屋子紧里头的一张小桌子边。弗立克看到,戴安娜从桌边的一个银光闪闪的酒桶里拿出一瓶酒,给莫德和自己倒上。弗立克真想一把掐死她。
她转身朝那张桌子走去,但侍者领班拦住了她。他直勾勾地看着她那身便宜行头,说:“有什么事,夫人?”
“晚上好,”她说,“我得跟那边那位女士说句话。”
他没有动。他是一个矮个子男人,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却不怕别人诈唬。“也许我可以给她传递你的消息。”
“恐怕不行,这是个私事。”
“那么,我告诉她你在这里。名字是?”
弗立克瞪着戴安娜那个方向,但戴安娜没有抬头。“我是马蒂尼夫人,”弗立克说,她只能委托他了,“告诉她,我必须马上跟她说话。”
“好的。希望夫人在这儿等一下。”
弗立克咬着牙,心里有种挫败感。侍者领班走开时,她真想冲到他的前面去。这时,她发现坐在附近的一个穿黑色制服的党卫军少校正在盯着她。她跟他对视了一下,立刻把眼睛移向别处,一种恐惧立刻涌上她的嗓子眼。他是否只是闲来无事,恰好被她跟侍者领班的争辩吸引过来?也许他见过那张布告,觉得她有点儿面熟,却一时无法把两者联系起来?或者,他只是觉得她很吸引人?无论到底是什么原因,弗立克都觉得不能在此弄出什么动静来,这实在太危险了。
她站在这儿的每一秒钟都是危险的。她把那种想掉头跑开的欲望强压下去。
侍者领班跟戴安娜说了几句,然后转身向弗立克招手。
弗立克对鲁比说:“你最好在这儿等着,我一个人过去,两个人太显眼了。”然后她快速穿过房间走到戴安娜的桌前。
无论是戴安娜还是莫德,谁都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心虚的样子。弗立克生气地看着她们。莫德显得心满意足,戴安娜则一脸傲然。弗立克把两手放在桌沿上,探身过去压低声音说:“这太危险了。马上起来,跟我走。我们出去时把账结了。”
她尽全力说服她们,但这两个人已经进入了一个虚幻世界。“讲点儿道理,弗立克。”戴安娜说。
弗立克一时火起。戴安娜怎么能这么狂傲无知?“你这头愚蠢的母牛,”她说,“难道你不知道这会要你的命?”
她马上意识到骂脏话是个错误。戴安娜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说:“这是我的生活,我有资格冒这个险——”
“你也危及我们,危及整个行动。现在就站起来!”
“可是你看——”弗立克的背后出现一阵骚动。戴安娜停下半句话,往弗立克身后看去。
弗立克回头一看,立刻惊呆了。
站在入口处的就是她在圣…塞西勒广场见过的那个衣冠楚楚的德国军官。她这一瞥将他看得清清楚楚。他身材高大,穿着优雅的深色外套,胸前的口袋里塞着一块白色的手帕。
她迅速转过身,心跳个不停,祈祷着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她戴着黑色假发,可能不会让他一眼就认出来。
她记起了他的名字:迪特尔?法兰克。她在珀西那堆档案里找到过他的照片。他以前是名警探。她记得他照片背面的说明:“隆美尔手下情报人员中的出名人物,据称此人是审讯高手,残忍的施刑者。”
这是一个星期里,弗立克第二次与他狭路相逢,距离近得完全可以射杀他。
弗立克从不相信巧合。他跟她同时出现在这儿,一定有什么理由。
她很快发现那理由是什么了。她又看了一眼,只见他大步穿过餐厅,朝她这里走过来,四个盖世太保模样的人尾随着他。侍者领班跟在他们后面,面色惊慌。
弗立克把脸侧过去,转身走开。
法兰克直奔戴安娜的桌子。
整个饭店一下变得鸦雀无声。客人们停下说话,侍者也不再上菜,调酒师手里拿着玻璃葡萄酒瓶,愣愣地定在那里。
弗立克走到门口,鲁比还站在那儿等着。鲁比低声说:“他要过去逮捕她们了。”她用手去摸她的枪。
弗立克看到那个党卫军少校又盯了她们一眼。“把枪放在口袋里别动,”她咕哝着,“我们不能轻举妄动。我们能够对付他和那四个盖世太保,但这里的德国军官会包围我们。即使我们干掉这五个,其他人也会把我们撂倒。”
法兰克在质问戴安娜和莫德。弗立克听不见那里在说什么。戴安娜的声音是目空一切的冷漠腔调,她一做错什么时就是这副样子。莫德则带了哭腔。
可能法兰克要看她们的证件,两个女人同时去拿放在她们椅子旁边地板上的手袋。法兰克换了个位置,站到戴安娜身边,稍稍侧一点儿,越过她的肩膀看着。猛然间弗立克意识到接着要发生什么。
莫德拿出了她的身份证,但戴安娜却掏出了一支手枪。一声枪响,一个穿盖世太保制服的人跑了几步跌倒了。餐厅立刻大乱。女人在尖叫,男人缩起身子乱躲。第二声枪响,又有一个盖世太保叫着倒下。一些食客往出口跑去。
戴安娜举枪朝向第三个盖世太保。弗立克脑海里闪过以前的记忆:戴安娜在索默斯霍尔姆的树林里,她坐在地上吸烟,身边放着一只只死兔子。她记得自己跟戴安娜说:“你是个杀手。”这话她没说错。
但戴安娜没有打出这第三枪。
迪特尔?法兰克仍然保持着头脑冷静。他两手抓住了戴安娜的右手腕,使劲往桌沿上一磕。她疼得叫了一声,枪从她的手中滑落在地。他一把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让她脸朝下摔在地毯上,然后两只膝盖抵在她狭小的后背上。他把她的双手拧在背后,拉扯她受伤的手腕时她疼得发出尖叫,他不顾这些,使劲给她戴上手铐,然后站了起来。
弗立克对鲁比说:“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受到惊吓的男人女人都想一块挤出去。不等弗立克挪开步子躲进人群,那个盯着她看的年轻党卫军少校早就一步蹿了上来,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等一会儿。”他用法语说。
弗立克稳住惊慌。“把你的手放开!”
他越抓越紧。“你好像认识那边那个女人。


![(综系统同人)[综系统]筛子补完行动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3/2322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