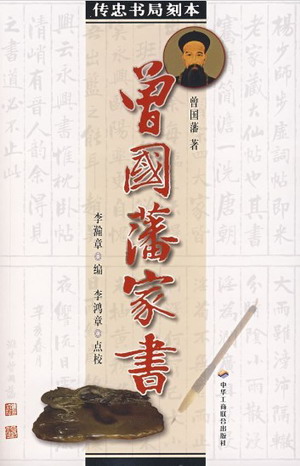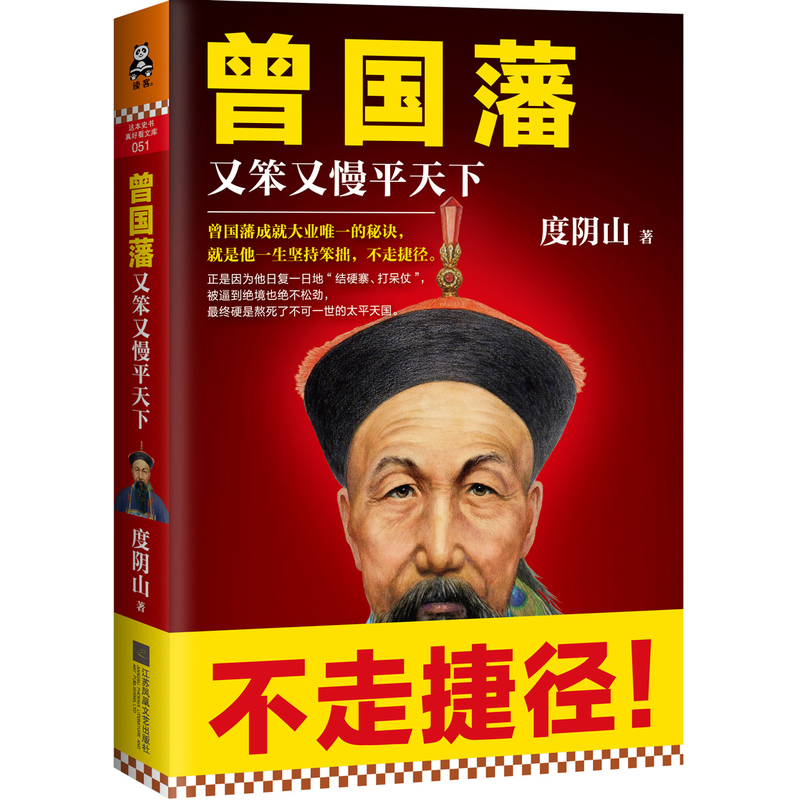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曾国藩极为痛苦,却束手无策,原因无他,主要是这些官吏不是他的亲信,就是他亲信的亲信;不是他亲手所保举,就是他保举的人所保举。所以他明知问题很大,非整顿不可,却无法下手,只能装聋作哑。
那个后来在“洋务运动”中成为标志性人物的丁日昌,在江苏常州做官时,打着洋务运动的旗号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有幕僚提醒曾国藩,若想整顿江苏吏治,必须首先从丁日昌开刀。
曾国藩长叹一声说:“丁日昌横征暴敛,是在给李鸿章提供剿捻军费,即使再坏也不能去掉。”
幕僚也长叹一声说:“那就只能让吏治继续败坏下去了。”
吏治腐败,让曾国藩渐渐失去“中兴”的信心,“中兴”的口头禅也慢慢从他嘴里消失不见。一次,某个幕僚对他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只不过现在皇帝的威权很重,割据风气还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烂掉,否则不会出现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中央政府好像正在烂掉。”
幕僚道:“祸患必是中央政府先垮台,而后天下无主,各自为政,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会超出五十年。”
曾国藩不禁皱眉:“能否南迁?”
幕僚斩钉截铁:“不可能!”
曾国藩很不服气,和幕僚大起争辩。幕僚最后甩给他一句话:“国初杀戮太重,满汉仇恨深刻,一成死灰,永不可能复燃,即令复燃,也不会长久。您就睁眼瞧着吧。”
曾国藩闭上了眼。最近,他的眼睛一直酸胀,看东西异常模糊。他知道这是病,但他不知道该从哪里治起。
就像是吏治,就像是他的癣病,还有他日益加重的肺病。
不是病入膏肓,而是命中注定,这种病会带走一个人,乃至一个帝国。
第十一章 最后没有辉煌
见慈禧
1868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慈禧太后在花园里漫步。突然,这位阴阳怪气的女人阴阳怪气地问了句:“曾国藩在金陵干吗呢?”
跟随她的人除了宫女就是太监,无人能回答整个问题。她似乎也没想得到答案,继续说道:“皇上(同治)自即位后还没见过他呢。”
伶俐的太监马上跟上一句:“您也没见过他呢。”
慈禧微微一笑:“那就让他来趟京师?”
无人应答。大清王朝,戒律森严,太监和女人不得干政。慈禧所以干政,是因为她就不是个女人,甚至不是人。
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在金陵接到圣旨,命他担任直隶总督,顺便到京城觐见。
直隶是京师的屏障,大清的总督是地方之王,直隶总督则是万王之王,太平时节,掌握最富庶的江南、供应朝廷财政需求的两江总督都在它之下。
曾国藩听到圣旨时,有如释重负之感。
他在金陵大张旗鼓地搞“洋务运动”、整顿吏治,已是黔驴技穷。正愁无处寻找出路时,慈禧拯救了他。
幕僚们却另有想法:这是中央政府要改变“内轻外重”的局面,您这任命是明升暗降,天子脚下可不好做官。
“哎,”曾国藩面无表情地叹气说,“凡事都有利弊,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出发。”
幕僚们不说话了,显然,曾国藩是非去不可了。
在把金陵事务做一番布置和交接后,1868年12月,曾国藩登上了北上的专船。
他没有直接去直隶总督的任所保定,而是先去了北京。1869年1月末,曾国藩抵达京城。
自他回家守孝直到现在,已有十七年。这十七年的沧桑风雨,把曾国藩锻造成了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也把他摧残成了一个病夫。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他感慨万千。京城仍和十七年前一样,毫无生机。
一个行将就木的京城,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京城,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京城好像沉睡了十七年,如今也没有醒。
按朝廷的意思,他将在第二天上午觐见皇上和慈禧太后。
那天晚上,残酷的噩梦把他折磨得筋疲力尽,早晨醒来时,他脸色铁青,嘴唇发紫,眼神迷离。
精神状态真差!他在路上不禁自责,第一次见新皇帝和皇太后,竟然是这副模样,真是有失大臣之礼。
他被人领进皇帝的养心殿,按规矩,他跪在一个蒲团上。蒲团冰冷,房间里虽有火盆,但离他太远。他跪了一会儿,就感觉浑身发凉,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养心殿也是老样子,丝毫不见任何改观。曾国藩叹了口气,那种感觉又回来了:这个城市好像昏睡了十七年,如今也没有醒。
已经跪了半个时辰,有太监过来拨拉了几下火盆。曾国藩感觉热气猛地上来了,他偷偷向里面的门望去,门关着,毫无动静,像是墓门。
腿开始发麻,背脊发酸,他悄无声息地直了直腰。“嘎吱”一声,他听到自己的脊柱某个关节响了一下,这声响动把他吓一跳。门口的太监马上看了他一眼,曾国藩冷汗直冒。
半个时辰后,他几乎支持不住,要跌坐在蒲团上。他的身体太脆弱,已无法支撑,唯一支撑他的是多年来锻炼出来的意志力。
又半个时辰过去了,曾国藩几乎要晕倒。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向一边倾斜,意志力失去作用。就在这千钧一发时,那个墓门突然开启。
一个公鸭嗓子喊起:“皇上、皇太后驾到。”
像是一个人猛地推了曾国藩一下,他立即跪直了。
同治皇帝出来了,畏缩的步子,猥琐的身材,空洞的双眼。他走到龙椅前,看了眼跪在下面的曾国藩。
他不认识,也毫无感情。他就孤独地站在那里,直到后面帘子里的慈禧坐定了,他才坐进龙椅。
曾国藩要脱帽叩头,帘子后面传出慈禧的声音:“免冠。”
曾国藩激动起来:“谢皇太后。”
磕头完毕,慈禧又发话:“抬头。让皇上看看你。”
曾国藩慢慢地抬头,和同治的眼神碰到一处,他迅速地低下头。刹那间,他有种感觉,同治的人生状态非常差。
“几时辰了?”慈禧问。
曾国藩算了一下,说出了正确的时辰。
“我是问你,你跪了几时了。”
“臣……”曾国藩不知该如何回答。
慈禧似乎在帘子后笑了,而且很得意:“知道为什么让你跪这么久吗?”
曾国藩当然知道,这是慈禧给他的下马威,提醒、警告他,不要以为你建下那么大的功业就了不起,在这里,你就是个臣。
她知道曾国藩明白,所以也就不必知道答案。
“江南的事办理完了?”
曾国藩回答:“办完了。”
“湘军都解散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听说有股贼人被称为哥老会的,好像湘军参加的多。”
哥老会兴起于四川,原本是个互助合作的社团,但曾国藩解散湘军后,很多湘军士兵都参加了哥老会,于是这个团体就成了黑社会。
曾国藩在金陵时一直提心吊胆这件事,特别担心哥老会连累自己,今天果然被慈禧提出。
他正准备把自己抛进深沉的思考中,慈禧已岔开话题,继续问道:“来的路上可平安?”
平安倒平安,但曾国藩一路见到百姓流离失所,盗贼横行,这不是好兆头。
“很平安。”
慈禧“哦”了一声,又问:“你出京多久了?”
“十七年。”
“带兵呢?”
“出京后就一直带兵,只是这两年才在江南做官。”
“哦。”
慈禧不再问,光阴沉寂下来,气氛有些尴尬。
“皇上可有问的?”慈禧放话。
同治急忙扭头,向帘子里说:“没有。”
慈禧啧啧:“皇上,这曾国藩可不是一般人,若不是他,咱们大清江山……”
“砰”的一声,曾国藩已把头狠狠地磕到地上,“臣应尽之责,全赖皇上、皇太后保佑,长毛贼才被剿灭。”
“不是这样说,”慈禧道,“你的功劳苦劳,皇上都记着呢。”
曾国藩又叩头,这次比上次还用力,养心殿都晃动了一下。
“直隶的事,你大概清楚吧?”
“臣已做了详尽调查。”
慈禧满意地点头:“洋人逼得紧,直隶非比寻常,你要好好做,做好!”
曾国藩再叩头,比上两次轻了很多。不是他不想再磕得那么重,而是已头晕眼花。
时光荏苒,慈禧又问了很多问题,包括曾国藩的家人和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都对答如流。后来,同治悄悄地伸了个懒腰,谈话就结束了。
曾国藩后来在日记中对这次觐见有如下评论:皇太后问的全是废话,毫无价值。皇上神情懒散,不知在伪装还真就如此,堪忧!
这是诚!但不是忠,曾国藩写完这段日记后,大为懊恼,认为自己的心灵开始生长了野草,于是急忙静坐,改过。
改过之后,他就跑出去游览京城,顺便去拜访当年的好友。这更让他心情低落,因为当年在京城的大多数好友,全都离开人世。
人最忧惧的就是这个,自己年纪已老,身体状况又差,一听到老友死了,更是情绪低落。
后来,他索性就待在寓所里,养着精神,为去保定上任而积蓄力量。
春节那天,慈禧大摆筵席,请臣子们吃饭。曾国藩获得最高荣誉:位列汉臣之首。他激动得老泪纵横,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和委屈全部消散,对大清的忠诚再上一个台阶。
1869年2月的最后一天,曾国藩觐见慈禧。他要去上任了,按规矩,应该去找最高领导人“请训”。
慈禧依然是冷冷的腔调:“你到直隶后先办何事?”
曾国藩回答:“臣按皇上和皇太后的意思,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你打算练多少兵?”
“二万。”
“够了?”
“只要配备洋人的武器,足够保卫京师。”
慈禧叹了口气:“当初僧格林沁十万人,却挡不住洋人的几千人,你现在明白我为何要你做直隶总督了吧。”
曾国藩明白,他训练出的湘军灭亡了太平天国,慈禧希望他还能创造奇迹,训练更强大的一支军队,保卫京师,最好能打败洋人。
然而他已老了,精力不济。他虽有心,却总觉得前途未卜,不知该从哪里下手。
他对慈禧说,湘军是白手起家,如今形势严峻,臣身体大不如前,我的意思是,可用绿营兵(政府军)为基础,再加入李鸿章淮军的一部,短时间内可训练出一支精锐。
慈禧微微点了点头:“你的身体如何?”
曾国藩叩头谢恩:“眼神大不如前了,其他还好。”
“还好就好。”慈禧漫不经心地说,“走吧,迟早也要走。”
是的,迟早都要走。
曾国藩第二天就离开京城,奔向了去保定的路。
去天津
保定城一潭死水,因为有官文在。官文被曾国荃弹劾后,跑回北京休闲了一段时间,就被派到保定,做了代理直隶总督。
曾国藩向他伸出饱含深情的友谊之手,官文却想在上面吐口水。他和曾氏兄弟的仇恨虽未不共戴天,却在心里发誓老死不相往来。
在开始直隶总督工作前,曾国藩用对联来表明自己的工作态度。
第一副对联是这样的: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他问人:“怎样?”
“好!”
他也觉得好,可第二天早上醒来,再看这副对联,觉得不太好。较真的人往往都是这样,一定要做到最好。于是,他又写了第二副: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愿群僚共学龚黄召社,即长官藉免愆尤。
他又问人:“怎样?”
“这个嘛,太深奥了。”
曾国藩扯碎了,捻着胡子,捻掉了几十根,写出了第三副: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幕僚们都叫起好来,“大人真是用心良苦,让人敬佩。”
曾国藩说:“诸位既了解我的心,我就欣慰了。”
这三副对联可谓是曾国藩的誓言,既要练好兵,又要整顿吏治,希望官员们能够体恤民间疾苦,认真办事,修养民力,让百姓有个喘息的时间,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
他这样希望,也这样做了。
首先是练兵,他从淮军和绿营中挑选精锐,用训练湘军的办法训练这支部队。其次是整顿吏治,难度很大。他择优录取了很多人,淘汰了很多人,但湘系的人从全国各地都跑来找他,结果,保定的吏治又和金陵异曲同工。最后,曾国藩在辖区内大兴水利,防杜河患,保证农业。
公平地讲,在保定的一年,曾国藩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治理才能。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并未立竿见影。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如同一阵暴风,把曾国藩再吹到风口浪尖,吹出了保定。
所谓教案,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绅士、民众和西方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传教士或这些传教士发展的中国教民之间的冲突。互相谩骂、斗殴是轻的,严重的则会发生流血冲突,中国人会焚烧教堂,甚至弄出人命。
最开始的传教士来中国,纯是抱着传播上帝福音的。但后来,有些传教士发现来中国就会受到如上帝般的待遇,于是鱼龙混杂。中国人首先对洋人的相貌就反感,加上儒教徒们的恶意宣传,中国人就把传教士们当成了魔鬼。冲突不断,尤其是在北京的门户天津。
1870年入夏,天旱无雨,中国人花费人力物力和金钱,祭祀龙王爷,却毫无成效。传教士们也过来凑热闹,用科学解释说,世上只有上帝,没有龙王爷,天是否下雨和神仙无关。
中国人愤愤不平,本来就不下雨,庄稼已宣告颗粒无收,洋鬼子还跑来说风凉话。于是,仇恨变成谣言。
有人说,天不下雨全是因为传教士,有谣言更进一步:教堂专门拐卖小孩,然后挖心用来做药。更有谣言登峰造极:洋人的眼睛发蓝,是魔鬼,要想保持他们的魔力,必须要吃小孩的眼珠。很多人已亲眼所见,在教堂的地窖中,盘子里盛放的都是小孩的眼珠。
当时风声已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