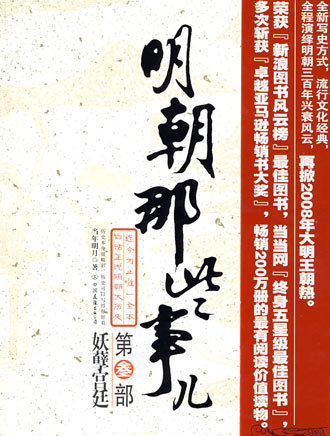这些人,那些事-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板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忽然快步走向阿圆,随手就是一个耳光,说:「你是想要他干你,然后带你去台湾啊?你想乎死啦你!」
阿圆站在那边没动,捏着衣摆低着头,也没哭,一直到我们车子开走了,远远地,她还是一样的姿势。
车子里小包沉默着,好久之后才哽咽地说:「刚刚,我好想去抱她一下……」
我们驻地旁边的公路是金东地区通往「勿忘在莒」勒石和金门名胜海印寺惟一的通道,平常是禁区,每年只有春节的初一、初二对民众开放一次。
对阿兵哥来说,道路开放的最大意义是,在这两天里金东地区的美女们一定会从这边经过,所以两百公尺外那条持续上坡的公路,在那两天之中显然就像选美大会的伸展台,因此初一的早点名草草结束后,我们已经聚集在视线最好的碉堡,把所有望远镜都架好,兴奋地等在那里。
那天天气奇好,阳光灿烂,所以上山的男女纷纷脱掉外衣,可看度以及可想象度都当下增加不少。十点左右是人群的高潮,随着各店家那些驻店美女陆续出现,碉堡里不时掀起骚动,忽然间,却有人回头说:「钦仔、小包,你们的救命恩人出现了。」
我们分别抢过望远镜,然后我们都看到了阿圆。
她穿了新衣服,白色的套头毛衣,一件粉红色的「太空衣」拿在手上,下身则是一件深蓝色的裤子,头发好像也整理过,还箍着一个白色的发箍,整个人显得明亮、青春。
我们看到她和身边一个应该是她父亲的黝黑中年男人开心地讲着话,另一边则是两个比她小,应该是她弟弟的男孩。
小包忽然放下望远镜,大声地喊她的名字,可是她好像没听见,碉堡里忽然又掀起另一波忙乱,几分钟不到简便的扩音器竟然就架设起来了。
当小包抓着扩音器朝公路那边喊着:「阿圆,你今天好漂亮!真的好漂亮呢,阿圆!」的时候,整条公路的人都慢慢停下脚步听,然后纷纷转头四处顾盼,好像在找谁是阿圆。
阿圆先愣了一下,看看父亲,然后朝我们这边望着;小包有点激动起来,接着说:「营部连小包跟阿圆说谢谢!跟阿圆爸爸说新年快乐,你女儿好棒,而且好漂亮!」
她父亲朝我们这边招招手,然后好像在问阿圆发生什么事。
我看到小包的眼眶有点红,于是拿过扩音器接着说:「阿圆,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美女……我们营部连所有人都爱你!」
公路那边的人都笑了,围着阿圆,甚至还有人鼓掌起来。之后扩音器便被传来传去,「阿圆,谢谢!」「阿圆,我爱你!」「阿圆是金门最漂亮的女孩!」……不同的声音不断地喊着,整个太武山有好长一段时间一直萦绕着阿圆的名字。
从望远镜里我们看到阿圆流泪了,她遮着嘴,看着我们碉堡的方向。
其实她是笑着的,在灿烂的阳光下。
直到现在,每年的春天我都还会想起阿圆以及她当时的笑容。
茄子——
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吃茄子。多长?算一算大约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前,三年兵役的最后一年,部队从金门移防台湾;许多资深军官和士官长忽然一窝蜂地办婚事,大部分娶的是年纪几乎可以当他们女儿的东部姑娘。
老莫好像一点也不动心,一如往常独来独往。他是空中管制无线电台的台长,和几个兵成天窝在装满无线电器材的拖车里,除了三餐派个人出来打饭之外,跟通信营的其他人好像少有接触,也常让人忘了他们的存在。
我是营部行政士官兼通信补给,挟职位之便倒常到他们那儿厮混。比起其他资深军官和士官长,老莫其实「知识」许多,看英文的保养修护手册像翻报纸,没事看他泡茶读《古文观止》;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他床铺底下那一大叠书,但坚持只能在电台里头看,绝对不借出,因为大部分是三〇年代作家的作品,还有盗版的金庸、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当年都还是禁书。
问他怎么可能没升官,他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不希罕!另一种是;不想给笨蛋管!
老是说这种话的这种人,别说在封闭的军队里,即便在社会上也注定孤绝,甚至永远有一堆人等着看他倒楣出错、出糗。
有一天我去电台核对器材账册,随口问他说:「士官长,你没想过跟他们一样娶个老婆以后当老伴啊?」
他看了我一眼,很严肃地说:「他妈的,我才不想害人!」
那是我跟他之间最后一次的交谈。
几天后电台奉军团的命令到南部支援演习,下午五点应该报到,没想到老莫六点多打了电话回司令部,说车子为了闪避牛车撞到路树,修了很久没修好,显然无法准时报到。
听说司令部的人骂他笨蛋、丢脸,说无法达成任务为什么不早点通报?说他延误军机,事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等等。
晚上十点多随车的打电话回营部,说老莫失踪了!说他六点多打完电话只交代他们有事情要办,要他们好好看着车、看着电台千万别再出错之后就没看到人了。
我跟营部的长官报告这件事,正在打扑克牌的他们说:「乘机去找女人打炮啦!」
当晚刚好是我轮值安全士官,清晨三点多营部的电话忽然响起,那种时间的电话永远不会有好事,我一接果然没错,电话那头是南部某个宪兵队的值星官,说有一个士官长阶级的人在他们辖区被火车撞死了,不过他们找到遗书,所以可能是自杀,姓名是……。
我直觉地回答说:「莫〤〤?」
他愣了一下说:「没错……,你怎么知道?」
我叫醒营部长官,说莫士官长找到了。「他不是去打炮,他去撞火车!」
我和营部长官坐吉普车一路飞奔到现场时大约六点出头,五月底天亮得早,铁轨两旁的稻田上方笼罩的雾气未散,但当我们跟着宪兵沿着铁轨走向陈尸的地方时,阳光已经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所有人都低着头没说话,只听到脚下的碎石子清脆作响,直到鼻息之间慢慢闻到些许血腥的气味时,才听见宪兵说:「就在前面。」
我抬头看到的第一眼是约莫十公尺外一只穿着黑色军用胶鞋的脚,脚踝以上不见了,只剩一些碎烂的皮肉,它的另一侧则是一只手臂,手掌不见了,扭曲得像刚拧干的衣服一般搁在铁轨旁。
所有人没再往前走,宪兵说撞他的是观光号列车,因为前一站是小站没停所以速度快,因此尸体被拉扯、散布的范围比较广;他说检察官大概九点上班后会来现场勘验,勘验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请人家来帮他收尸。
营部长官看看我说:「你在这边看着,不要让野狗把士官长的肉叼走了!我去宪兵队办文书手续,顺便找个愿意收拾的人,弄完我们直接把他送回去。」
后来他们都走了,现场只剩下我和老莫支离破碎的尸体,以及慢慢白热起来的太阳,和逐渐浓烈起来的尸臭。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奇怪气味,或许是因为随着腐败的程度,味道逐渐加强或有所改变,以致你无法像书里说的「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而是愈来愈浓愈来愈臭,特别是当火车经过,空气被强烈搧动直到缓缓平息的那几分钟,那味道仿佛不只进入你的鼻腔,而是从你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钻进你的身体中。
现场果真有野狗不时来出现,虎视眈眈,甚至还有无聊的路人三三两两掩着鼻子站在铁轨旁边看;于是我不得不在那两三百公尺的范围里来回走动驱赶,有几次甚至不小心就踩到或踢到一些散落在铁轨旁边草丛里的细小尸块,最后逼使自己不得不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注视自己的脚步,也因为这样,我几乎看遍了莫士官长碎裂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包括认得出来的外表局部以及根本无法分辨的内脏部分。
我看到他被撕裂成一半的信,看到他此刻已完全裸裎并且和身体完全分离的阴毛及阴茎,看到苍蝇慢慢聚集在上头,我一走过便一大片嘤嘤飞起,甚至飞到我的脸上、我的嘴边。我看到那些尸块逐渐改变颜色,清楚还可以清晰分辨出来的血或肉,随着我来来回回的脚步一次一次加深颜色,最后都成了一模一样的暗黑或深紫,只有从皮肉里穿透出来的骨骼勉强维持可以分辨的白色。
十点了,但检察官还没出现,我继续来回走着,好像失神一般停不下来,好几次都要听到连续的尖锐鸣笛才发现火车都已经冲到眼前来。
十一点,检察官来了,他和营部长官站在远处,才抬头看了一眼就听见他说:「可以收了!」
负责捡拾尸块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沉默老人,他惟一的工具是一个用两片麻竹中间夹着石头做成的夹子;大的尸块他直接用手捡,放进原本装肥料的塑胶袋,小的才用夹子夹。
他一边挥赶苍蝇、一边要我帮他仔细看,说尽量不要漏掉任何一小块,那是我们对亡者最基本的责任;他要我不要怕,说我们以后不管怎么死,最后也都和他一样,「再大块也都变成粉。」他还说:「虽然我不认识他,但可以这样相逢也是缘分。」
尸块收全之后,老人自在地用连洗都没洗的手掏出香烟抽,然后点起香要我请士官长跟我们回去,一边帮衬似地用士官长绝对听不懂的台语说:「怎样来就怎样回去哦……,如今做神了,心内不要有怨……,乖乖跟着观世音菩萨走……,不要回头,不要留恋。」
然后我们两个一人提着一袋士官长走下铁轨,检察官走过来问说:「都收净了?」然后下了一个指令说:「打开让我看看。」
老人看了我一眼,顺从地打开他手上的那一袋,我则打开我的……
当塑胶袋一拉开的那一刹那,我只记得里头的颜色和扑鼻而来的温度和气味,之后一如电影的反白效果,只听到检察官说:「好,收起来!」之后完全没有记忆。
回到驻地已经黄昏了,吉普车先放下我,然后直接开去火葬场;我恍惚地从营区大门走向营房,我看到很多人慢慢走向我,远远地问说:「怎么样?」
我才一靠近还没开口,没想到他们反而先倒退后几步,说:「你怎么这么臭!」
我进浴室把自己刷洗了好几遍,衣服从里到外全换掉,没想到走进餐厅还是有人说:「你怎么臭臭的?」
晚餐的菜打上来,有鱼、红烧豆腐以及一盘炒茄子。
军队的大锅菜,茄子炒得烂烂的,暗黑带深紫,中间还有白色的葱段……,我只觉得:啊,该死,士官长的尸体怎么没收干净没收完?但才一回神,我已经忍不住冲到餐厅外大吐特吐,一整天没吃东西的肚子能吐出来的好像只有胃液和胆汁。
夜晚我开始发烧,营舍外的卫兵几次敲我的窗子,说我一直乱喊乱讲话,「还装那种外省腔!」
高烧不退连续了好几天,最后和士官长同乡的副营长受不了了,在士官长头七的夜晚,他把全营集合起来,我在床上听见他在念士官长的遗书,断断续续地听到:「任务不成……败军之士……我军之耻……,然后听到副营长开始边哭边飙脏话,说败军要死也轮不到他!操他妈的他以为他是谁?」
后来有人进来寝室,说副营长要他们扶我出去集合场,副营长暴怒的吼声倒吓得我差点腿软,我看到他指着天空大骂,说:「是这孩子守着你一天,不让你进了野狗的肚子,是这孩子盯着,一块不少地把你找回来,你不知足、不感恩……,你有不平你他妈的来找我……,你再不让这孩子平安,我明天就把你的骨灰倒进猪圈里喂猪!你看我敢不敢!……。」
半夜,一身酒味的副营长走到我床头,跟我说:「我骂他了,你没事了,他这辈子就怕我一个人。」然后把一个东西塞到我枕头下,说:「这人也没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我捡了一样给你,让他保佑你一辈子。」
那是一根极其普通的铁梳子,黑色随身型,不过,上头竟然认认真真刻了字,刻了兵籍号码、士官长的名字,以及购于金门阳宅和购买的年月日。
这梳子跟了我好几年,一直到一九八四年我写了一个有关老兵娶少妻一番曲折之后有了圆满结局的剧本,或许潜意识里希望士官长也能有这样的人生吧,所以把男主角的名字干脆取做「老莫」,不久之后,当我有一天忽然想起那把梳子的时候,就怎么都找不到了。
梳子不见了,但某些记忆却始终难忘,尤其是茄子和士官长的尸体与气味的关系。我不否认那种联想几乎成了我一种病态的强迫性反应和行为,总之,只要看到眼前出现茄子这道菜,无论什么煮法,最初的几年是直接反胃,而后几年则是自我说服,我会先跟自己说:
「这是茄子,你看,它是很香、很下饭的鱼香茄子,这跟当年士官长那一袋尸块一点也没关系……,然后开始反胃。」
五十几岁过后,我好想遗传了妈妈当年的毛病,嗅觉慢慢丧失,或许是这样吧,这两三年来我已经可以安心地接受茄子,虽然只剩下口感和味觉。
或者是……经历过太多亲人的死亡现场之后,我已经无感了……,或是……故意遗忘?
爱——
阿春小我两岁,所以是在我三年兵役的最后一年他才下到我们的单位来,不过,报到之后,也不知道是他「造型惊人」,还是在中心的时候有过逾假不归的记录,各连竟然没人要他。
记得那天营部都已经开饭了,人事官还在大声小声地打电话协调各连「收容」,最后营长开口了,说:「没人要就留在营部吧!可以把没人要的兵带好,那才叫本事!」
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瘦得像一根签,却偏偏穿着一身改得几乎完全贴身的军服的家伙,走进餐厅。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行李,除了随身军品之外,他还带来两个大皮箱、一把吉他以及一个质感看起来相当高级的小箱子,后来我们才知道里头装着的竟然是量「手」订做的保龄球一颗。
「啥名字?」营长问他。
「Haru。」他恭敬地答。
全场愕然之下,我连忙跟营长解释,那是日文「春」的发音。
「我操你妈,你当日本兵啊?」营长开口骂,他才紧张地说出他的全名,不过随后又加了一句:「报告营长,我妈不见了!对不起!」
这话一出,整个餐厅已经完全严肃不起来了,连营长都笑着骂说:「你这小子不是傻子就是彻底装傻。」
后来我们当然知道他不是傻子,也没装傻,他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