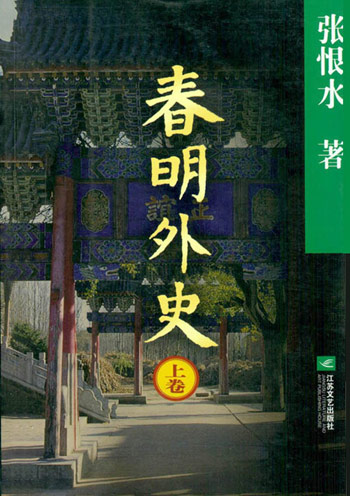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所谓无声色嗅味触法,木然无动,而不知身所在焉。若就此而为文以纪之,则十
百倍于《春明外史》之多可也。然而,今何在者?皆已悠悠忽忽,仅留千万分之一
作为回忆而已。不亦哀哉?吾如是,吾知读《春明外史》者亦莫不如是也。不但如
是而已,则在此五十七月中,爱读《春明外史》者,生离者或当有人,死别者或当
有人,即远涉穷荒,逃此浊世,或幽居国地,永不见天日者,或亦莫不有人。是皆
吾之友也,吾竟不能以吾友爱读者,献与得卒读之,使其生平,多亦未了之缘,此
又吾耿耿于心,揪然不乐者矣。
由前言之,可乐也。由后言之,乃不胜其戚矣。一下里巴人之小说成功,其情
形且如此,况世事有百千万亿倍重于此者乎?信夫,天下之事有相对的而无绝对的
也。
吾书至此,人或疑而问曰:然则子书之成也,乐与威乃各半焉,果将何所取义
乎?吾又欣然曰:与其戚也,宁悦焉。夫人生百年,实一弹指耳。以吾书逐日随写
五六百言,费时至五十七月而书成,似其为时甚永也,然吾于书成后之半岁,始为
此序,略一回忆,则当年磨墨伸纸,把笔命题,直如昨日事耳。时光之易过如此,
人生之岁月有涯,于此一弹指,弃可用心思耳目手足不用,听其如电光火石,一瞬
即灭,不亦大可惜耶?今吾在此若干年中,将本来势将尽去之脑之目之手,于其将
去未去以成此书,造化虽善弄人,而吾亦稍稍获得微迹,而终于少去须臾,是终可
庆也。且读吾书者,因而喜焉,因而悲焉,因而相与讨议焉,亦将其将去未去之脑
之口之目之手,以尽一时之适意,亦未始非好事也。不宁惟是,而最大之效用,且
又可于若干时候忘却日日追逐之死焉。夫人生之于死,拒之有所不能,急而觅死,
人情又有所不忍,坐以待死,亦适觉其无聊者也。然则人生真莫如死何矣。兹有一
法焉,则尽心努力,谋一事之成,或一念之快,于是不知老之将至,直至死而后已,
遂不必为死拒,为死不忍,为死而无聊矣。识得此法,则垂钓海滨,与垂拱白宫,
其意无不同。而吾之作小说,与读者之读小说,亦无不同也。容有悟此者乎?则请
于把盏临风,高枕灯下,一读吾书。更不必远涉山岛,而求赤松子其人矣。
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由沈阳还北平,独客孤征,斗室枯坐,见窗外绿野半黄,
饶有秋意。夕阳乱山,萧疏如人,客意多暇,忽思及吾书,乃削铅笔就日记本为此。
文成时,过榆关三百里外之石山站也。
张恨水序
第一回 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 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
春来总是负啼鹃,披发逃名一惘然!
除死已无销恨术,此生可有送穷年?
丈夫不顾嗟来食,养母何须造孽钱。
遮莫闻鸡中夜起,前程终让祖生鞭。
这首诗,是个羁旅下士所作,虽然说不出什么好处来,你看他满腹牢骚,却立
志甚佳,在作书的这部小说里,他却是个数一数二的人物呢。这人是皖中一个世家
子弟,姓杨名杏园。号却很多,什么绿柳词人啦,什么沧海客啦,什么寄厂啦,困
庐啦,朝三暮四,日新月异,简直没有一个准号;因此上人家都不称他的号,都叫
他一声杨杏园。
在我这部小说开幕的时候,杨杏园已经在北京五年了。他本来孤身作客惯的,
所以这五年来,他都住在皖中会馆里。这皖中会馆房子很多,住的人也是常常拥挤
不堪,只有他正屋东边,剩下一个小院子,三间小屋,从来没有人过问。原因这屋
子里,从前住过一个考三次落第的文官,发疯病死了,以后谁住这屋子,谁就倒霉。
一班盼望升官发财的寓公,因此连这院子都不进来,谁还搬来住。杨杏园到京的这
年,恰好会馆里有人满之患,他看见这小院子里三间屋,空堆着木器家伙,就叫长
班腾出来,打扫裱糊,搬了进去。会馆里也有人告诉他,说住不得的。杨杏园笑道:
“我本来倒霉,不搬进去,不见得走运;搬进去倒落得清闲自在,住一个独院子了。”
人家见他如此说,也就由他。其实这个小院子,倒实在幽雅。外边进来,是个月亮
门,月亮门里头的院子,倒有三四丈来见方,隔墙老槐树的树枝,伸过墙来,把院
子速了大半边。其余半边院子,栽一株梨树,掩住半边屋角,树底下一排三间屋子,
两明一暗。杨杏园把它收拾起来,一间作卧室,一间作书房,一间作为好友来煮茗
清谈之所,很是舒服。一住五年,他不愿和人同住,也没有人搬进来。
说到这里,正是三月初旬的天气。北地春迟,这院子里的梨花,正开得堆雪也
似的茂盛。窗明几净,空院无人,对着这一捧寒雪,十分清雅有趣。杨杏园随手拿
了一本诗集,翻了几页,正看到那“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之处。忽
听见有人喊道:“杏园在家吗?”杨杏园丢了书本望外一看,却是他影报馆里的同
事何剑尘。连忙招呼道:“请进来坐,请进来坐。”何剑尘看见他桌上放了一本诗
集,笑道:“你倒兴复不浅,其实我们难得有这一天假期,应该出去逛逛才是。”
杨杏园道:“何尝不是呢!但是我就想不出一个消遣的地方来,二来我这院子里的
梨花,正开到好处,多多赏玩一会,我觉比逛那龙蛇混杂的游艺场,却好得多。”
何剑尘道:“难道北京之大,就没有你消遣之所吗?这未免矫情太过了。这样罢,
我来做个小东,请你吃小馆子,吃完了,我们去看中国电影戏儿,好不好?”杨杏
园道:“吃小馆子我倒赞成,哪家好呢?这却是个问题。”于是彼此讨论半天,后
来是何剑尘硬行主张,要到九华楼去。杨杏园道:“九华楼的扬州菜,倒有几样不
含糊,就是地方窄小的不堪,老等没有座位。”何剑尘道:“去早一点,总可以不
至于等座位的。”杨杏园道:“吃馆子要等座位,那也是个虐政。不过我常见一班
吃学专家,越是窄小而又拥挤的地方,越是爱去,好像有什么学问似的。于是开馆
子的人,他有展开局面的机会,也不展开了。”何剑尘笑道:“你能看到此层,也
就于吃学三折肱了。”说说笑笑,不觉已是七点钟,二人便坐着车子向九华楼而来。
杨杏园一进门,便觉油香酒气,狂热扑人。那雅座里面,固然是乌压压的坐了
一屋子人,就是雅坐外面,柜台旁边,三三两两的包月车夫,有的拿着毡条,有的
披着洋毯,排班也似的站着。杨杏园回头对何剑尘道:“如何?我不说是无望吗?”
那柜上掌柜的,不待何剑尘回话,便道:“楼上有座位,二位请上楼罢。”何剑尘
对杨杏园道:“且上楼看看。”二人上得楼来,见这三间单间,早放下了帘子,里
面杯盘争响,人语喧哗,闹成一片。外面散座,四张桌子,也全坐满了人,二人大
失所望。正想下楼,一个伙计正从一个单间里出来,见了何剑尘,满面堆下笑来道:
“三爷,你好久不来了啊。”说时,顺手搬两张凳子过来,把他肩膀上的手巾拿下
来,就是一顿乱擦。口里说道:“您二位请坐,这单间已经在算账,说话就得。”
说到这里,何剑尘正要问话,只听见左边屋子里,一阵筷子敲盘子声,当当的直响,
意思是叫伙计,或者催菜。那右边屋子里又喊道:“伙计!拿花卷来。”这伙计接
连答应了两个喂字,转身就走。杨杏园笑道:“这伙计的职务,要是叫我干一天,
我必然肝脑涂地。亏他三百六十天,朝朝如是,居然乐此不疲。”何剑尘道:“什
么乐此不疲,也是为吃饭二字所迫罢了!好像夜静更深,人家都睡的甜蜜蜜,我们
还是睁着两只大眼睛,在那电灯底下,什么内阁问题,什么国会风潮,把人家瞎账,
正研究得个不了。扩而充之,彼此境况,都是一样啊。”杨杏园道:“言归正传,
你看还是等一等座位呢,还是另走一家。”何剑尘道:“我是几天想吃这里的松鼠
鱼和烧鸭炒芽菜。还是等一会罢。”杨杏园没法,也只好坐下来等,不免用目光射
到散座上去。只见西角席上,坐了两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的,穿了一身的哔叽衣服,
胖胖的脸儿,嘴唇上养一撮短胡子,神气很足。一个年纪轻些的,穿了一身西装,
戴了一副茶青色的克罗克斯眼镜,头上分发,梳得光溜溜的一丝不乱,雪白的一张
脸,一根胡桩子也没有。杨杏园正在打量他们,那个穿西装的也回头向这边看来,
他见了何剑尘,忽然站起来道:“何剑翁好久不见了。”何剑尘一看,原来是内务
日报的主任凌松庐。便也站起来道:“久违!久违!”凌松庐道:“你是两位吗?
我这席上正有两个位子,这面坐罢。”何剑尘道:“不必,不必,各便罢。”凌松
庐哪里肯,再三再四,硬要何杨二人坐下,何剑尘没法,只得坐上这边来。大家介
绍之后,才知道那位小胡子系樟脑局局长,他的职务系在福建地方专办樟脑事宜,
姓江,名大化,是把南洋华侨资格来作官的。这时添了杯筷,凌松庐点的菜,一碗
一碗送上来。凌松庐对何剑尘道:“我虽然是福建人,就爱吃江苏馆子,北京空有
几家闽菜馆,全不是那一回事。剑翁对于江苏馆子,自然是内行了,请你点几样罢。”
又对杨杏园道:“我们虽然初次见面,却不必客气,请杨先生也点一两样。”何杨
头里少不得谦逊一番,后来点了几样炖鲫鱼红烧鸽子之类。不一时,饭毕,凌松庐
在皮夹里拿出一支雪茄,一面擦洋火,一面吸着。吸了两口,仰在椅子上,将右手
大指食指,夹着雪茄,却用中指不住的弹烟灰。抬头望着江大化道:“吃过饭,哪
里去玩?”江大化道:“还是胡同里走走罢。”凌松庐对何剑尘笑道:“你看如何?”
何剑尘道:“我却是一家相识的没有。”江大化道:“过于客气,这里拐弯就是韩
家潭,何不走走?”杨杏园看见何剑尘那个样子,是有点动心了。因对他们三人道:
“他处无不奉陪,逛胡同我却是个十足门外汉,那是要除外的。”凌松庐道:“要
去自然大家同去,一个也不能少。”何剑尘道:“杏园!你就去罢。你不是说过,
北京各级社会,连车夫聚会的小茶馆,都得实地调查一下吗?那么,像这南北驰名
的八大胡同,怎样能不去一广眼界呢?”江大化道:“包你去了一次,还想第二次
呢。”杨杏园心里想道:“果然这八大胡同,只徒闻其名,究不知里面是怎样一回
事,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实地去调查看看。”他这样一犹豫,何剑尘笑道:
“没有什么问题,去罢去罢!”这时,伙计算上账来,凌松庐抢着会了账。杨杏园
觉得决然而去,对不起人,只得随着他们下楼。一行四人,出了九华楼,凌松庐的
马车,何杨的包月车,早都拢了过来。江大化对凌松庐道:“这一点路,我不要坐
你的车子了,我们走了去罢。叫车夫在松竹班门口等如何?”何剑尘不觉失声道:
“呀!松竹班吗?”凌松庐道:“这个呀字,下得可怪,我们非到松竹班玩不可!
看是怎么一回事?”何剑尘只是微笑,一声不响。杨杏园对他们这些话,却完全莫
名其妙,只得低头跟着他们走。
不一会,来到松竹班门口,江大化早一脚跨进大门。杨杏园见那院子拐角上,
几个穿黑布袍子的人坐在几条板凳上,见他们进门,都站了起来,内中有一个人,
忽然提起嗓子,喊了一个似何非何似黑非黑的字音,如雷贯耳的响了出来,不由得
吓了一跳。看何剑尘他们,却丝毫不为介意,杨杏园也就装做没事似的,跟了他们
进院子。杨杏园一看,那些屋子,都是电光灿烂,素帘低垂。有几间屋子,玻璃窗
里的窗纱,掀起了一只角,有几张雪白的面孔,在那里向院子里张望。这时跑过来
一个穿黑袍子的,低声下气的对江大化道:“诸位老爷有熟人吗?”江大化正要答
话,杨杏园只见南屋子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骂那穿黑袍子的道:“饭桶!
人也勿认得。”便走近了一步,笑盈盈的对何剑尘道:“今天是哪一阵风,把你何
老爷吹来了?”凌松庐笑道:“今天是我把他拉来的,哪里是什么风。”那姑娘便
笑着对凌松庐点点头道:“谢谢你。”那穿黑袍子的,早站在南屋子门口一边,把
一只手高高的将帘子掀起。那姑娘就让着大家进屋子。杨杏园在这个所在,还是破
题儿第一遭,进得屋来,少不得四围观察一番。这屋子是两间打通的,那边放了一
张铜床,上面挂着湖水色湖绉帐子,帐子顶篷底下,安了一盏垂缨络的电灯,锦被
卷得齐齐整整,却又用一幅白纱把它盖上。床的下手,一套小桌椅,略摆了几样骨
董。窗子下,一张小梳头桌,完全是白漆漆的,电灯底下,十分的亮。小桌上面,
一轴海棠春睡图,旁边一副集唐对联,上写道:“有花堪折直须折,君问归期未有
期。”上衔写着“花君校书一粲”,下衔是“书剑飘零客戏题”。杨杏园想道:
“原来这位姑娘叫花君。这副对联,却是集得有意思。”再看那边,三面三张沙发
椅,中间也是一套白漆桌椅,窗子边一张小条桌,上面也有笔砚文玩之类,一个小
铁丝盘,里面乱堆着上海流行的几本杂志。右角上一架穿衣镜,镜子边一架玻璃橱,
桌后头斜叠着一架绣屏。壁上除挂了四条绣花屏外,还有一副集唐的对联,是“却
嫌脂粉污颜色,遥指红楼是妾家。”杨杏园正在这里观察,一个三十来岁的娘姨,
递了一枝烟卷过来。他本不抽烟,但是拒绝不抽,一来不好意思,二来又恐怕犯了
规矩,只得接了。那花君便擦了一根火柴,替杨杏园燃烟,一面含笑问道:“贵姓?”
杨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