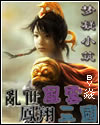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题,阿塞拜疆各区的夺权问题,伊朗边境设施遭到破坏的问题没有被委员会里无数夸夸其谈的废话空话所淹没的话,那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应该在这些问题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立刻着手解决它们——既用政治手段,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用行政手段。
至于说到公众,特别是外高加索的公众,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有的很冷淡,有的则显然支持武装暴徒。而且有的加盟共和国国家政权机关也并没有遵循国际主义原则。例如,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个委员会,于当年2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上就1990年1月19日、20日巴库事件所作的调查发表过一个声明,现引一段如下:
……刑事犯罪分子利用这样的局势,于1月13日在巴库策动打砸抢和骚乱,导致大批人员死亡,主要受害者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民和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对罪行加以愤怒谴责,要求对组织者和肇事者给予严惩。
然而巴库以及共和国全国出现的复杂局势,不应评估为强行夺权的图谋……
居然是这样看。没有强行夺权的图谋。那是什么?是朋友们气氛和谐的约会?
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搞不明白,那要么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废物,要么就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者。意图夺取政权的人们在民族主义狂热大发作的时候,同他们所仇恨的中央展开了斗争,因为阿塞拜疆的国家地位正是中央赋予的。
是的,这时你不由得就会想起,老百姓说的话真是充满了智慧:发动战争的是肮脏的政客和残忍的冒险分子,遭罪的却是普通老百姓。
当笔者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时候,俄罗斯电视上正在播放巴库事件。护法机关的强大队伍正在平息人群的愤怒。这是阿利耶夫总统在现实地行使他的权力,制止国内出现混乱和破坏法制现象。任何一个正常的统治者都关怀他治下人民的安宁和国家的完整。
我们为了认识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外高加索的熊熊烈火不能不影响到国家整体上的稳定。多年冲突造成的裂痕。延伸到苏联所有的共和国。立志破坏国家的人们希望苏联衰弱,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希望搞得它道德扫地。人们讲起充当宪兵角色的苏联军队和它的将军来,一个个义愤填膺,说一定要把军队非政治化,决不允许利用它来消除国内冲突。所有这一切都是所谓“激进民主分子”口号中的内容。他们正是在这些口号的帮助下攫取了政权,然后又唱起了别的调调儿。在经过了第比利斯和巴库这两次事件之后,他们恨不得把亚佐夫元帅和罗季奥诺夫将军剁成泥,而“民主派”的将军格拉乔夫呢,他在北高加索视察的那些部队,虽说已经换成了俄罗斯部队,可完成的不还是同样的任务吗?就在不久之前,车臣牺牲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呢?
“改换颜色”的沃尔科戈诺夫将军在进入“民主”俄罗斯掌权后,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过:俄国军队起着“稳定国内局势的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宪兵”的概念又该怎么办呢?在一次俄联邦武装部队领导干部的集会上,叶利钦令人印象深刻地声称:
“今天的部队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它还具有保障稳定、保障俄罗斯经济政治改革的天职。”
这些说过的话全忘了。这位“宪法保障”在他的讲话中,居然也公然号召要用军队来保障经济政治改革了。在人民和祖国最艰苦的那些年月,难道不正是他和自己的那伙人,在恶毒地诅咒苏联当局和军队领导的行动吗?
国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机体。特别是在一个具有联邦体制的多民族国家,经常会出现各种特殊状态——翻起分裂主义的浊浪,出现民族冲突、恐怖主义等等。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国家的完整和人民的生活产生影响。
为了消除这种局面,当局有义务充分利用护法机关,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还可以动用军队。我们都非常明白这一点,而且也这么做,为此,却遭到了一些人的疯狂攻击。可是,几年之后,这些人却让公众明白了:必须得这么干,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却是为了一己之利。所有这些就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别的定义我实在找不到。
1990年悲剧过后,又过了一段时间。
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分子制造的混乱局面已逐渐成为过去。这种局面之所以能够来临,只是多亏盖达尔?阿利耶夫成为国家元首之后。人民又要求他出来工作。国家的管理走上了正轨,国家的前途又变得可以预料。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他的才华和意志帮助他解决了许多问题,其中也包括民族问题。
我非常了解阿利耶夫。我们是1982年11月的同一天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而我是中央的经济工作书记。三年后,当我领导苏联部长会议时,他成了我的第一副主席。而且,工作非常出色。
现在阿利耶夫已经去世。但我们相信,他对阿塞拜疆的领导政策将由他的儿子继承下去。
本书叙述的1990年1月发生的巴库事件,只是其中的某些场景。我想,研究者一定会把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全面真实地再现出来,并对其影响巴库的后果作出评估。而且,人民迟早会把一切恢复本来面目。无论人们怎么说,所有事件之间都是直接有联系的。不过,应该记住一位诗人的话:“时代对历史学家越是有趣,当代人就觉得它越是悲惨。”
第6章 雪崩前奏:波罗的海三国(上)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我国在民族土壤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带有地区性。但它们却成了几年后造成雪崩式毁灭性发展过程的推动力。
在这些事件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加盟共和国起到了特殊的催化剂和起爆器的作用。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率先宣布自己拥有国家主权,提出要退出苏联。而中央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对策上的平庸无能,却向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表明,任何破坏国家统一的行动,其组织者实际上都不必承担什么后果。
我要阐述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凭着道听途说得知的。
这些政治势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掀起了猛烈的风暴。其最终结果,就是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八九月间签署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命令。
民族主义运动坐大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国内积累的问题已经相当不少。因此苏共中央总书记倡导改革,实行对国家生活各个方面开展革新的方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赞同。于是,涌现出不少支持这一方针的社会运动。显然,运动的参加者对当时的国家形势各有各的看法,而且各自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地方领导人,特别是各州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得出结论,认为在党和国家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改革派与“保守”派正在进行着尖锐的斗争。
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为这种结论的产生提供了口实。我想,许多老一辈的人都还记得他去视察西伯利亚时发出的号召:各地方应当“自下而上”对改革的敌人施加压力,而我们(指政权的“先进”部分)则要“自上而下”施加压力。这个号召一出台,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运动自然就更加积极地活动起来。“自下而上”的压力当然就要触及到苏共。普通党员和非党人士于是开始向“上层”——苏共的州委领导和市委领导施压。我还记得戈尔巴乔夫是多么兴高采烈地谈到在萨哈林发生的事情:那里的一个群众大会把党的州委书记赶下了台。总书记公开在电视上对此事加以赞许的第二天我对他说:这样的行动可能导致非常悲惨的结局。有问题,包括党内问题,应当用别的办法解决。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已经动手干起来了!”
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戈尔巴乔夫确实是激发了不说上百,至少也有几十个反对现存制度的派别,包括党内和人民代表内部的小组乃至形形色色的小派别。对于“左派”和“右派”,他总是常常作出小小的或不小的让步,以此来求得他们之间的平衡。对于那些要求他要有明确具体行动纲领的人,总书记总是愤怒地进行驳斥。他没有,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不想有这样的纲领。他是一个即兴做事的人,可以说这种即兴的办事作风过于经常地支配着他的行动。
以我看,改革年代(1985—1991)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着手进行必要的民主革新,对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放松硬性控制,实行公开化等等的阶段。
第二阶段我认为应该从1989年年中算起。它的特点是激进民族主义的抬头和夺权斗争的展开。这一阶段的“开篇”之作,是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指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种“民族主义”的癫狂相对于全苏整体来,开始得更早,即从1988年年中就开始了。当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预警信号。正在开始实施改革的国家领导人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正为头顶上的荣誉光环而得意洋洋。1986年他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宣布说:“如今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涵盖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党的以及我们全体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改革是一个大容量的字眼儿。我们将推动改革……大踏步前进。”
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支持了他的行动。戈尔巴乔夫陶醉了,他忘记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考虑到最主要的东西——我国的特点。请注意,苏联有近三亿人口,民族和信仰的构成都非常复杂。国家的历史之所以不简单,还在于它虽强大而富饶,但相当一部分人民对此却毫无知觉。在这样的条件下,改革者必须得一步一个脚窝,无论是方向、规模、速度还是时机,都要找得特别准。也就是说,行动必须要有具体的、切合实际的纲领。但总书记却没有纲领。
戈尔巴乔夫着急了。现在很难判断,当时他是受到什么力量的推动,不知是出于性格,还是受到谁不断催促:时间不等人哪!我看是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那些“改革”的策划者们利用总书记性格中的某些特点,推行他们自己的路线,以更快地动摇国本,消灭他们所仇恨的社会制度。当雅科夫列夫及其一伙牵着总书记的鼻子走到对国家已构成危机的第二阶段时,总书记束手无策了。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我想,他掉进什么圈套,他自己是明白的。于是就开始乱套了,权力也丢了,改革初期建立的威信也丧失了。这恰好应验了一句富有哲理的格言:“从爱到恨只有一步之遥。”
在这一阶段,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进反对派转入进攻,社会公众对改革的支持蜕变为民族主义运动,其代表性例证,就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8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立陶宛的“萨尤基斯”,以及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人民阵线。正是它们引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个共和国的“进军”:最初是要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独立经济核算,而后就是退出苏联。
最具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是“萨尤基斯”。它在夺取政权和争取立陶宛退出苏联的斗争中,显示出极大的破坏力。其实,“萨尤基斯”通过由它掀起的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浪潮,在该共和国攀上政治巅峰之后,却并不善于解决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仅仅过了三年多时间,它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就遭遇了覆灭的下场。甚至连立陶宛取得独立也难以挽救它的危亡。类似情况实际上发生在所有民族主义社会运动身上。特别明显的是到了90年代,他们的领头人如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彼得罗相等人纷纷淡出政治舞台。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上,他们的活动都留下了否定的评价。
当然,客观地讲,“萨尤基斯”之类的大型社会运动,其产生的基础,都是广大居民对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中央及地方官僚行政领导作为的不满,以及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中出现的偏差。改革的作用正是要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但为此需要时间,并应采用深思熟虑的方法。
“萨尤基斯”于1988年夏季开始举行一次次群众大会,其决议中提出了要求更多社会民主、独立自主、社会公平(“要对上级党任命的干部说不,要断了他们捞油水的路子!”)、恢复“历史真相”之类的口号。不过后来才明白,像“萨尤基斯”这样的运动,虽然提的是在各共和国开展改革的口号,但要达到的却完全是不同的目的:它们想要破坏现行社会制度,并夺取政权。
正是由于当时有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和共和国克格勃高层领导的参与,“萨尤基斯”才相当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实体。该组织近95%的成员是立陶宛人,其行动特点是效率高,组织性强,战术步骤周密。在外国“朋友”的帮助下,财政问题和物质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得也不错。
运动迅速积蓄了力量。1988年6月初,它还是一个刚组建的只有36名成员的自发组织,仅过了10天,就掀起了一项政治行动:对1941年驱逐200人出境的决定提出抗议。全苏第19次党代表会议前夕,它在格底米纳斯广场举行了一次两万人的集会,为参加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送行,并以新运动拥护者的名义向他们提交委托书。7月9日,又有好几万人前来迎接这些代表归来。“萨尤基斯”运动的积极分子以这样的姿态完成了在公众面前的亮相。1988年8月23日于维尔纽斯举行的万人大会上,这一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并在组织上开始成形,这一天正是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签署条约的纪念日。在这次群众大会上首次宣布了“萨尤基斯”的纲领性宗旨。
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被他们从民族利己主义和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