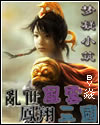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0—15分钟)。民族广播电台给俄语的广播时间也只有一小时。
在立陶宛,白天只有国家广播电台——“俄罗斯之声”?——一家播送节目。不错,那些较比富有的人,拥有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人,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所有主要电视频道。但基本的俄罗斯群众却很少能有人充分就业,即使能有活儿干,也是辅助工作,因此他们对看这类节目连想也不敢想。
俄文报刊的出版也有类似情况。最容易读到的便是《Etyboc Ptac》、《立陶宛信使报》、《述评》、《共和国报》等几份周刊,但它们出版的数量不多。可是,第一,这些报道谈的不是俄罗斯人在立陶宛的生活,而是用俄语讲述立陶宛的生活;第二,整个材料最好的部分是“昨天的”俄罗斯报刊文摘。在报刊亭里花费商业高价可以买得到个别的俄罗斯出版物,可是它们缺乏针对性和及时性。
由此观之,立陶宛当局的政策从不考虑俄语居民在立陶宛居住的历史条件,他们学习立陶宛语的困难,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困难。立陶宛当局实际上是在推行对这些居民的强制同化政策。
立陶宛政府文件中只字不提俄罗斯学校中俄罗斯文学课时急剧减少的状况,在教学大纲中,除了作为独立学科的俄罗斯历史地理,这些课程目前都放到世界史和世界地理中去讲授。
立陶宛官方材料断然说,为学习国语创设了良好条件。但却只字不提这种为居民开设的短训班是收费的。
存与邻国拉脱维亚对比的情况下,乍看上去,立陶宛的俄罗斯学校和俄语教学等问题,状况要好得多。可实际上立陶宛的一些事态进程——其中包括俄罗斯学校的“改组”——同样令人担忧。
各级官员中都有一些人对不民主的国语法随意加以解释,在执行中随意性也很大;少数族群的民族文化空间遭到急剧压缩;加之他们所执行的学习和教育体制——这一切无疑都促进了“非主体民族”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加速同化。在这种条件下,许多家长也认为自己的孩子在俄罗斯学校学习已无前途可言,于是把孩子转入立陶宛学校。社会学抽样调查表明,在10所维尔纽斯立陶宛学校的低年级,有25%—30%是非立陶宛学生。俄罗斯学校的生源已经呈现萎缩倾向,人数大为减少,学校的最后关闭指日可待。
据生活在立陶宛的专家的看法,必须通过一项比较民主的国语法,扩大立陶宛非主体族群的信息文化空间,制定少数族群学校章程,方能保留少数族群的民族同一性,和谐地达致与立陶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
从道德和政治的观点来看,立陶宛既不应该允许以损害某些族群学校的利益来解决另一些族群学校的问题,也不应该允许行政当局在这个问题上仓促行事。政治家和专业人士在解决这类微妙敏感的问题时,作为出发点的设想应该有足够的根据。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应以其他文明国家为榜样,必须放弃在熔炉中“熔化”立陶宛少数族群的思想。只有每个民族都保持自我,都能珍视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各民族有机团结一致的局面才能出现。
爱沙尼亚 在爱沙尼亚,俄语的处境同其两个南部邻国一样令人担忧。看来,对发展爱沙尼亚文化和爱沙尼亚语言的必要性未必有人会持有异议。但是,这不应该靠伤害俄语族群来实现。任何人都不能根据护照封皮和族属来随意“理解”国际法和人的自由权利。
必须特别强调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传媒手段的景况不容乐观。如果说在拉脱维亚尽管要通过有线电视,但总算还能看到俄罗斯电视节目的话,那么在爱沙尼亚,全共和国规模的俄语电视节目就根本没有。这种节目只能靠几个现有的爱沙尼亚频道来转播。而这一切却发生在居民有1/3是俄罗斯人的国家里!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主要定位在宣传鼓动单一民族国家,以及对非本土居民开展同化的意识形态改造。
上世纪80年代末,拉脱维亚出现了一个新词——“阿特莫达”,翻译成俄语的意思是“觉醒”——当然是民族的觉醒。如果“阿特莫达”这个词的始作俑者不是雅?彼特斯,那么我本来不会去注意它。
我们清楚地记得,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罗斯居民同拉脱维亚人一道参加“觉醒”群众大会,喊出的口号是:“为了你们的和我们的自由”。现在自由了。可是,接着就出现了最初的怀疑:“怎么会这样呢,在一起并肩战斗过,而现在我们却成了二等公民?”“你们根本连公民也不是,”——“民族意识苏醒后的”往日同志回答他们说。于是,不得不与这种新生活妥协。更有甚者,他们居然又成了“占领者”,而且,那些反法西斯老战士还要受到审判,在他们的个人护照上还要注明是“非公民”。
随着北约一道,又来了一些身着军装、佩戴星条小旗的先生。他们到此并不是为了欣赏多姆斯克大教堂的管风琴,也不打算把里加电影制片厂变成一个新的好莱坞,更没有在寒冷、荒凉的沿海地区为他们建造创作之家,没有把安?乌皮特、雅?莱尼斯的作品翻译成“莎士比亚的语言”。甚至连我们说过的“觉醒”的教父雅?彼特斯的作品也同样遭致冷落。这些新来的先生蔑视民族天才,若是新修建一些妓院,新开张一些麦当劳嘛,他们倒是会感到需要的。
在结束评论我们的同胞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民主”国家的遭遇、他们的公民权利和语言问题时,我不禁想起一句英明的箴言:“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然而,这些国家当局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这句箴言。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宣布自己拥有主权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年。遗憾的是在这些年里,问题的状况已经变得“稳定”了。俄罗斯强国被人吐了满身口水,可是这个强国却装模作样,说这是上帝施予的甘露。据说,今后还要表现出克制力,要等待里加、塔林和其他的“政治家们”成熟起来,等待他们学会国际上的礼貌。等着瞧吧,一旦它们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成员,那里的成年叔叔一定会罚他们站在墙角反省的,因为他们侮辱了最可敬最可爱的伙伴俄罗斯,要知道,这个伙伴已经是“八国”成员之一,是与北大西洋公约、欧盟等合作的各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了。毋庸置疑,北约和欧盟暗中是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对俄语居民的歧视和对俄语的排斥的。否则的话,他们早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波罗的海的家伙揍个鼻青脸肿了。只需欧盟的主要和平缔造者索拉纳(下令轰炸南斯拉夫的正是此人)眉毛一扬,那里的一切就都会得到调整。
如果把各种“开心事”(如俄罗斯加入了“文明国家”俱乐部,与这些国家签订了无数的伙伴和合作条约等等)抛在一边,那么欧盟和北约不顾俄罗斯外交部的抗议、说服和痛苦呻吟,执意东扩,便是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的余波了。我们这些亲爱的伙伴连续不断地强化苏联解体的成果,造成不可逆转的态势,迫使俄罗斯为了民族利益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占领的阵地撤出,向东方后退。
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纳入北约和欧盟,这为改变欧洲政治领土地图又向前跨进了一步。这一步是有意识迈出的,具有挑衅性。长期以来,北约和欧盟一直未敢迈出这一步,直到确实认定,不必把我国对北约集团提出的不得越过“红线”的警告认真对待,才有了这个动作。
说到这儿如何能教人不想到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的“分界线”呢!难道北约和俄罗斯地理上划定的“红线”,不就是1939年划过的那条线吗?为什么如今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主权国家却一言不发,默不作声呢?答案很简单,今天的新主子——欧盟和美国使他们称心如意。可是历史证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这些朋友朝三暮四,瞬息多变,这不会吓退新伙伴吗?或者新伙伴需要的只是这些国家今天针对俄罗斯的政治决定?其实,所有这一切,世界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都经历过!
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这些北约和欧盟的新成员来说,为了巩固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政治领土新格局并使之具有进一步的稳定性,一个要素就是从这些国家排挤出当地俄语居民的主要部分,并强制同化剩余部分。这一政策具有长期、整体的性质,绝非无足轻重。这里讲的是针对受歧视的非主体族群采取的极其广泛的措施。问题的实质在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相当大一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原住民,实行的是按民族特征划分的民族歧视。
如果认为北约和欧盟似乎看不到和不明白这一点,这种想法是愚蠢的。他们看在眼里,心知肚明,默默地鼓励赞许,不过又在一旁监视,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在国内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方面,事态不至发展到严重过火的程度。时至今日,这种严重过火的行动还没有发生,于是,大规模歧视俄语居民的政策便得以继续顺利进行,并不断完善。
波罗的海三国与东正教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东正教的特点是这样的: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东正教一直处于与天主教和新教的直接接触和斗争之中。无疑,这不能不在整体上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以及同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俄罗斯的关系。
当地许多人对俄罗斯东正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把它看成一个使该地区俄罗斯化,向本土居民传播他们所不熟悉的“野蛮东方”文化和信仰的工具。与此同时,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德国人,以及某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长达近两个世纪的过程中,一直都在系统地为日耳曼骑士团和西方宗教在该地区历史上起到的丑恶作用进行辩解。
天主教和路德派新教在很多方面促进了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压迫和奴役。为了使这些民族驯服,天主教神甫和牧师放下十字架,拿起了皮鞭和长剑。然而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仍然企图把天主教和新教描绘成促进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接近西方文化的一股力量。
而东正教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历史,尤其是在爱沙尼亚的历史,证明东正教的学说在各个时代都是主张和平友好的宗教信仰。它不以强制和恐怖手段强加于人。东正教宗教促进教育,支持民族利益,抵制随天主教和新教来到该地区的奴役者。
近年来,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获得主权以后,采取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做法,肆意歪曲国内各族群宗教生活的实际情景,千方百计在信仰东正教人民的生活中排斥传统的宗教信仰。我用以写作本节的材料说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东正教,无论其起源还是生存发展,都与俄罗斯、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密不可分。这种联系是政治家们用任何办法也无法破坏的。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基本宗教信仰并不单一,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在爱沙尼亚,路德派新教信徒占居民的 70%,东正教教徒——20%;在拉脱维亚,路德派新教教徒占 40%,东正教教徒——35%,天主教教徒——25%;在立陶宛,天主教教徒占90%,东正教教徒只占4%。
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三国中,态势对东正教最不利的是爱沙尼亚。这个国家对东正教的势不两立看来有其历史根源。正如我们所知,早在13世纪该地区就被条顿骑士团所征服,因此受到日耳曼人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深,不过这种影响却远非时时都能起促进作用。
在爱沙尼亚,教会和国家在人们生活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尤其明显的是一些政治活动家希望利用宗教信仰来挑唆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的仇恨。
在20世纪90年代,爱沙尼亚成了东正教最热的“热点”。爱沙尼亚的东正教教会陷入了困境,尝到了苏联解体以后民族主义崛起的苦果。1999年5月,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写给爱沙尼亚教区委员会的致敬信里说:“从民族联系和民族文化联系的观点来看,获得独立的过程和爱沙尼亚公民民族意识成长的过程并非时时一帆风顺,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爱沙尼亚政府当局实际上并没有制止对俄语居民——几万名东正教耶稣信徒——信仰自由的伤害。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的神职人员和信徒受到压力,他们被要求自发地切断由教规所规定的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联系。
爱沙尼亚的东正教教会被彻底分裂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非单一民族、非单一宗教信仰的爱沙尼亚社会内部出现严重不和。但有一个事实却很引人注目,就是无论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派新教教徒,都没有遭遇分裂的悲惨命运,因为天主教的精神中心在爱沙尼亚境外,而路德派新教,和东正教一样,在苏联时期有着平行的国外教会。
为了让读者对各教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世俗国家不应介入这一冲突的宪法规定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有必要大致介绍一下爱沙尼亚教会冲突的历史。
1992年4月,按照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的决定,科尔尼里大主教向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提出报告,要求恢复爱沙尼亚东正教教区于1920年由大牧首吉洪授予的独立地位(自治地位)。与此同时,全体与会者一致表示,希望保持与莫斯科大牧首教区的合乎教规的从属关系。
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科尔尼里大主教收到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决定,其中重申了1920年神圣大牧首吉洪授予爱沙尼亚东正教独立地位的决定。该决定认定,爱沙尼亚东正教是在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开展活动。这一决定还任命科尔尼里主教为教区住持主教,授“塔林及全爱沙尼亚”主教衔。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神圣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决议在爱沙尼亚宗教人士中引起的反响不一:有些人高兴,有些人愤慨。爱沙尼亚东正教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反映出与会各方还完全没有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