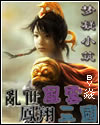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瓦?伊万诺夫早就应该从立陶宛被赶出去,并把这个问题忘掉。最好能把他和拖延驱逐出境的内务部长罗马西斯?瓦伊特亚库纳斯一同赶出去。”立陶宛自由联盟主席维塔乌塔斯?舒斯塔乌斯卡斯如是说。
独立党领导人瓦立扬基纳斯?沙帕拉斯声称:“伊万诺夫在我国无事可做,再说,他也不想停止自己的反宪法活动。”
“1月13日进行过犯罪活动,而且还反对立陶宛独立(?!)的人怎么能生活在我们的国家。”议会中右翼报业的代表拉斯?拉斯塔乌斯科内的观点也是如此。
1995年1月,前“统一”组织的几位领袖伊万诺夫及其同志向立陶宛内务部长递交了对市移民处决定的申诉,并请求颁发居民身份证。
1996年5月,伊万诺夫来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出版社为其《立陶宛的监狱》一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该书在国家杜马送给了议员和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伊万诺夫回答了许多问题,其中有对维尔纽斯1991年一月事件的亲眼所见,表达了他在1991—1994年整个调查和审判期间所持的观点。在参观国家杜马期间,瓦?伊万诺夫会见了“人民政权”议员党团领导人雷日科夫,杜马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及其他议员。
瓦?伊万诺夫很快便感到了新闻发布会的反响。6月中旬,立陶宛总检察长弗?尼基吉纳斯通过媒体宣布:“目前总检察院正在进行认真调查,其间将对瓦?伊万诺夫在杜马的讲话以及其他材料进行详细分析,根据调查结果将决定追究伊万诺夫责任的问题。”
1997年 7月,维尔纽斯法院“以诽谤罪”判处瓦?伊万诺夫强制劳役一年,并向1991年 1月 13日的 7位死难者家属偿付民事诉讼费 7万立特(约两万美元),因为这些家属觉得受到了“侮辱”,正像法庭“查明”的那样,伊万诺夫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在那个悲惨的夜里死于苏军之手。判决宣布后,法庭立刻给伊万诺夫戴上了手铐,就像对待罪恶的杀人犯那样,又把他送进了监狱。
1997年 9月维尔纽斯的上诉法庭举行二审,仍旧维持原判。这次庭审为伊万诺夫进行辩护的是亚历山大?克里格曼,莫斯科州律师委员会成员。他在发言中对判决书援引的 1996年 5月 21日伊万诺夫发言速记稿表示异议。对该文件进行的研究表明,杜马没有这份东西。那里只有一份新闻发布会的简报。编辑、整理这份简报的人是谁,他转达被告的意见究竟准确到什么程度——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说这一点只不过是个表面问题。1997年10月由《立陶宛信使报》刊登的克里格曼律师的演讲才道出了对伊万诺夫的原则态度:
今天谁也无法明确说出那些人是在何种情况下丧生的。情况只能根据每个死者死亡情况的详细事实,经法庭依法判决后方能生效。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判决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根据个人观察和文件来发表对事件的看法。我援引一个著名的司法案例说,尽管沃伦委员会确定了肯尼迪总统死亡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最近 20多年来各种各样人物对其死因的种种说法。1991年 1月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一定也会是这样,它将成为历史学家、政治家、新闻记者、司法界人士关注的目标。
判决书中写道,伊万诺夫“做这一切的动机是出于对立陶宛国家的仇恨”。这不符合事实,我的当事人也坚决否认有这种动机。况且,在追究被告责任的命令中和应该详细列举被告人违反法律的起诉书中,也并没有对仇恨立陶宛共和国动机的证明。法庭把此点写入判决书,超出了公诉范围,是文明诉讼所完全不能允许的。
判决书中还断言,伊万诺夫知道立陶宛共和国对所述事件的官方评价。简而言之,就是指伊万诺夫无权对事件作出不同于国家的评价。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也都经历过。这是对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人权的最粗暴的践踏,也违反了立陶宛共和国的宪法……
……上述各点导致的结论是,瓦?伊万诺夫的诉讼案是政治案。作出的判决残酷无情,显然是在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
上诉法院批准了对伊万诺夫的判决,它的这一决定是它固持己见的铁证。
1997年9月,伊万诺夫被发配到阿利图斯强制劳动营,当月末,伊万诺夫的母亲收到儿子的来信说可以探视,并可转交食品。10月4日,伊万诺夫的母亲带着小孙子和食品前往探视,但被拒之门外,代交的食品也不接收,因为伊万诺夫不服管教,正在接受惩罚,不许他进入会见刑事犯的营区。
的确,伊万诺夫自到劳动营后,并没有进入刑事犯的监管营,因为,正如所知,该营中有 300多名刑事犯都感染了艾滋病。此外,作为一名政治犯和外国公民,他又要求当地监狱行政管理部门按立陶宛现行关押囚犯规则把他安置到另一个地区。可是他不但没有得到照顾,反而被关进了单人禁闭室,即强制区,半年内失去了所有应得的待遇——他没有暖和的被子、暖和的外衣,不能听收音机,不能收探视带来的物品,不能与母亲和儿子会面。“秋天,牢房里只有15度,阴冷潮湿,每隔 10分钟就要走一走,暖和一下——这是中世纪的刑法。”他为此写道。该牢房的面积只有0。78×2米这么点大!
让我把瓦?伊万诺夫写给他母亲的信引在下面。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解释,太恐怖了。
立陶宛、阿利图斯,监狱 11号牢房(来自坟墓的信件)
最亲,最爱的妈妈,你好!
这已经是我在这可怕的牢房中写的第二封信了。从面积来看,这就是一座坟墓,差别仅在于这里不是地下,入口处——门旁边有一个臭“马桶”(进门要跨过“马桶”)。这就是我在法庭的抗议中提到的那间牢房。在这间没有取暖设施的墓室里(有一组暖气片,但它是冷的),有一张可以从墙边放下来摆在地上的板床,它根本不是人睡的床,而是摆放棺材或尸体的停尸台,太压抑了。一股霉味,不见天光,夜间老鼠不停地乱窜——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名字就叫做墓穴。
上次出庭回来后,我在这里又过了5天。我尽量把这里整理得像个人待的地方。想到在这座活人墓里还有别人也生活在类似的条件下,我的心又振奋起来。人毕竟是一种群体动物。甚至进了坟墓,只要一想到旁边还有人也待在这活人墓里,一样也在忍受,也在故意跟那些折磨自己的人对着干,只要一想到我在这里离他们不太远,同样也是躺在这么一张灵台上,还活着,还没有被打垮,其实是为了讲原则才把这么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扛到自己肩上,心里就轻松了许多。
看守们总是很难过地对我说:“伊万诺夫,转到刑事犯的监禁营去算了。”怎么跟他们这些天真的年轻人说呢?我只能沉默,无言地接受从牲口槽里打出来的那份口粮,等待着每天唯一的乐趣——30分钟的放风时间。那时我就把浑身的劲都使出来——用力做操,让全身的血液都奔流起来,让心脏、肌肉都紧张起来……谢谢你很快就寄来的这个邮包,有报纸,有油笔芯,还有纸。东西全部收到,看报真是一种享受。
紧紧地拥抱你,吻你。你的儿子瓦列里。”
1997年 12月 28日。
按照“文明的”立陶宛政治家的意图,这个人权保护者本该死在那里。但是,俄罗斯公众对他的命运极其关注,致使他们无从下手。
总之,正如所见,在如此“民主”、如此“文明”的当代立陶宛,只要你向往真理,只要你敢对官方的规定产生怀疑,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不仅你的人身自由会受到威胁,就连生命也极其危险。布罗克亚维丘斯对瓦?伊万诺夫的评语非常简短,但含义深刻:“够格的人!”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一崇高的评价。
在法院和监狱的通力合作下,一度被视为波罗的海沿岸最强大的左翼反对党目前在立陶宛遭到了彻底镇压。眼下,立陶宛当局没有新的敌人可找,为了清算那些不合心意的人——便开始在自己人当中找上了旧日的克格勃人员。
像外交部长瓦廖尼斯这种昔日立陶宛“欧洲大西洋主义”的“大亨”,如今也列入了被怀疑者的名单,此外还有议会副主席皮基亚柳纳斯、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局长波秋斯(他不久前才就任这个职务),也紧随成功地把帕克萨斯总统“赶下台”的劳林库斯之后上了名单。据立陶宛新闻界公布,仅1989年的克格勃名单上就有324个男子的姓名,其中波秋斯名列第218位;瓦廖尼斯居第289位。预计整个“克格勃后备干部”的名单都将被公布出来。为了认真调查立陶宛这一次又一次的丑闻,在劳动党成员帕别金斯卡斯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议会委员会。立陶宛共和国的“猎魔行动”开始了!
爱沙尼亚当局和拉脱维亚一样,首先开始对居住在共和国中的俄罗斯人动手,不仅对他们的社团歧视,而且对为权利平等而斗争的俄罗斯公民联合会的社会活动家进行迫害。为证明此事,我举1992年1月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副会长奥列格?莫罗佐夫“案件”为例。
从出生起一直居住在爱沙尼亚的莫罗佐夫(他的三个孩子也都出生在塔林)拒绝承认爱沙尼亚当局有权根据1992年通过的法律而剥夺他的权利。为此,他和其他数万人一样,被宣布为不合法的人。
1996年,安全警察人员穆鲁来到“少先队员”工厂干部处,之后,莫罗佐夫就被解雇了。他被指控在强制迁出俄罗斯公民沙乌姆亚诺夫多子女家庭时反抗警察,这一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从1996年一直继续到1997年。一桩表面上的日常民事小案子,居然有好几个政治警察的侦查员介入进行调查。莫罗佐夫后来被法庭宣告无罪,因为他只不过是保护了被警察毒打的少年。
从1997年到2000年,对莫罗佐夫又提出了一项新的刑事指控——说他挑起政治纷争,其表现就是莫罗佐夫在参加退休人员纠察线活动时,举的牌子是“打倒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种族隔离”。这个案子又是由政治警察提出指控的。法庭再次宣告莫罗佐夫无罪。
国籍和移民局于1999年和2000年曾两次向莫罗佐夫发出让他从爱沙尼亚离境的正式命令。1999年 8月,根据国籍和移民局(“非法逗留”)的法令,并经行政法院判决,莫罗佐夫入狱20天。其间他一直以绝食表示抗议。过了一年,2000年7月,根据国籍和移民局的法令,行政法院又把他送进监狱蹲了5天。他再次以绝食抗争。
在马特维延科与爱沙尼亚总理拉尔会见前夕,我作为国家杜马议员,向俄爱政府间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致信,请她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莫罗佐夫的问题。
下面是俄联邦外交部副部长古萨罗夫给我的回信:
鉴于您向俄联邦政府副总理马特维延科提出关于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副主席莫罗佐夫被捕一事,现通报如下。
马特维延科在同爱沙尼亚总理拉尔于今年7月4日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爱政府间经贸、科技、社会、人文、文化合作委员会两主席会谈框架内,郑重地提出了莫罗佐夫的问题。她强调说,爱沙尼亚当局的官方行为,其中包括监禁这位俄罗斯公民的行为,带有对俄罗斯不友善的色彩,对俄爱双边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政治和社会组织、我国的个别公民都曾多次致信为莫罗佐夫进行辩护,外交部也发表过尽人皆知的声明。马特维延科呼吁拉尔在决定莫罗佐夫的命运时,体现出友好的意愿。
拉尔确认,在力争使莫罗佐夫得到爱沙尼亚居民身份证的同时,爱沙尼亚当局还要履行现行的法律要求。从爱沙尼亚方的陈述可以得出结论,爱沙尼亚共和国官方集团对围绕莫罗佐夫发生的矛盾根本不感兴趣。
俄罗斯外交部将根据现有的原则决定,考虑到我国公民和同胞在爱沙尼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调整与爱沙尼亚的关系。
在马特维延科对拉尔强硬地提出停止迫害莫罗佐夫家庭的问题之后,曾经 “平静”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后,地方当局就决定施加经济压力。开始,出于政治考虑把莫罗佐夫在学校里教俄罗斯语文的妻子裁掉了。
莫罗佐娃是学校中最有能力的教师之一,她的学生在俄语和文学奥林匹克竞赛中经常获奖。但是有人却给学校领导打报告,说她教的班级对爱沙尼亚国家不忠诚。这个多子女的家庭失去了最后一点生活来源。
由于莫罗佐夫不可能找到正式工作,所以家里欠下了数目不小的房费。国家房产局在一年半时间内曾三次约莫罗佐夫谈话,在莫罗佐夫请求颁发居民身份证的申请被拒绝后,又曾三次对他课以罚款,每次的罚款额都是 6000克朗。因为莫罗佐夫没有缴纳这些罚金,国家房产局于是把文件转交法庭强制执行。房产部门的官员宣布将把莫罗佐夫的住宅卖掉抵债。
莫罗佐夫一家居住的集体楼房管委会主任收到当局有关部门的建议后,决定通过法院来索债,实际上就是要把住宅廉价卖掉(为了抵债),把一个拉家带口的家庭赶到大街上去。
爱沙尼亚当局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推行将不合心意的俄罗斯人从国内“迁出去”的政策。莫罗佐夫的凄凉事件就是例子。他既没有亲属,也没有住房,更没有生活来源,他甚至从没有跨越过俄爱边境,他真诚地相信,他完全有合法的理由居住在这个出生并生活了几十年的国度里,他根本就没有一点额外的奢求。
发生在莫罗佐夫身上的这一事件,就是爱沙尼亚的所谓“非法居留”问题的表现。这个问题是人为造成的,它涉及数万人,这些人既不可能,也不情愿按当局的规定来履行所谓的国内居民合法化的要求。爱沙尼亚当局对莫罗佐夫境况的态度将导致一个极端危险的案例。他所触及的是一大批所谓“非法外国人”的命运,而其中的大部分则是说俄语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