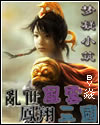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母系来看,弗拉季米尔?别纳尔特是俄罗斯人,在独立的爱沙尼亚执政者眼里,他的“罪行”又加一等。1953年他担任民警局科长时,曾下达过消灭抢劫当地商店,以恐怖手段恐吓百姓的匪徒的命令。如今的爱沙尼亚却以他下达过消灭这三名今天被称之为“民族英雄”的恐怖分子和“森林兄弟”的命令而对他提起公诉,并威胁要判他 8—15年。目前别纳尔特得了中风,他的一只胳膊已经无法活动。
俄罗斯外交部在正式声明中非常公正地指出,在爱沙尼亚,“对二战期间及战后时期国内各种事件带有政治色彩的主观评价”占有统治地位。
或许,有人能见到或听到这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的西方监护人中,会有人出面也就这种状况说点类似的公道话?我想,过去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
让我再就这个题目,简要地提一下立陶宛所发生的情况。1999年6月,法院对刑事案“人民保卫者”一案作出判决,判处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前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巴尔托谢维奇、库拉金、苏里宁、沙卡里斯监禁,因为战后年代他们曾同武装匪徒“森林兄弟”进行过战斗,保卫了立陶宛苏维埃人的和平劳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死在了立陶宛的监狱里。法学博士库切罗夫教授、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副总检察长克列姆波夫斯基,以及前波罗的海苏维埃共和国的其他一些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在开庭前就已经故去。
在为本章的叙述进行总结时,我想再次强调说明:上世纪90年代,这些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初都是些打着民主旗号为主权而斗争的人,后来他们又采取卑鄙的手段,开始对自己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进行迫害,对他们提起政治诉讼。90年代下半叶,他们开始对卫国战争游击队老战士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加盟共和国护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大肆进行迫害,对他们提起控告。与此同时,却对德国法西斯帮凶们“平反昭雪”,对他们的“功绩”予以肯定。在此期间,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不断壮大力量,他们在新一代和国际社会的面前,给苏联拯救了这些民族和国家的事实抹黑,竭力否定这些国家在加入苏联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上升到一个新水平的事实,把苏联说成是一个“入侵者”。
不,谁要是不想学习历史,也不善于学习历史,就无法从历史学到任何东西。遗憾的是,为此受到惩罚的总是普通百姓,而那些人,却以人民的名义掩盖个人利益,为无法无天的行为辩解。
这些先生忘记了哲人在圣经中说的话:“你们怎样议论人,也必怎样被议论。你们怎样度量人,人也怎样度量你们。”(马太福音第7章l—2)
第9章“独立”乌克兰的怪现状
奔向“独立”
对戈尔巴乔夫宣布的改革,乌克兰的态度有点不一样:这个共和国由全国公认比较得力的领导人谢尔比茨基领导,日子比较好过,并没有率先大肆宣告变革开始。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首先必须完善国家经济发展的这种相当成熟的必要性,在实行起来时居然会成为威胁到苏联存在的整个政治基础的一颗地雷。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关于“欧洲大家庭”的理想,不过被看成是向他所青睐的西方在努力表现一下自己罢了。
形形色色在改革口号下追求分离主义、民族主义、反苏目的的运动、阵线,长期以来在乌克兰未得到广泛支持(乌克兰西部加里西亚各州除外)。
然而其他一些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阿拉木图、费尔干纳、杜尚别)发生的事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充当“教师爷”的密使们的定期来访,使当时还不敢公开发表言论的“独立斗士”们深受鼓舞。在此之前,所有这些运动还都披着拥护改革的外衣。
甚至当时已经成立的、最具影响力的组织“鲁赫”(乌克兰人民改革运动)在其纲领中也声称,它是“全民赞同和支持由革命的、创造性的党所发动的改革的体现”,是“共产党和无党派人士联盟的新形式”等等。
应该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基辅还是在大多数州,“鲁赫”都没得到官方承认:人们知道那是些什么样的人搞到了一起。给“鲁赫”发放通行证的正是那位改革的总头头。
戈尔巴乔夫在参加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解除谢尔比茨基中央第一书记的全会(1989年9月份)之后,在街上与“鲁赫”领导人相遇,这些人向他告状,说不许他们登记注册。鲁赫分子把他吹捧了一通,说是如何如何爱他,如何如何尊敬他,戈尔巴乔夫听完之后,“建议”不要为自己这批新冒出来的拥护者在登记注册问题上设置障碍。站在一旁的谢尔比茨基只能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在苏共中央工作时对谢尔比茨基深有了解。他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而我是负责经济事务的中央书记,我喜欢这个稳健的、具有不屈不挠性格和坚定信念的人。
关于这个人可以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但我只想谈其中的两件。1986年5月份,当政治局讨论反酗酒政策决议草案时,他所持有的是相当坚定的现实主义立场。在他看来,提出这个草案的害处要比好处多。但是很遗憾,他和与他持有类似看法的人,其中也包括笔者,都是属于少数派,“不理解时代的呼唤”。
他不喜欢廉价的民众主义——领导人搞所谓“深入民间”那一套。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谓出色。正如所见,正是他把通行证发给了那些毁灭乌克兰的人。有一个事实为例:谢尔比茨基曾跟我一道奉派出席罗马尼亚举行的一次党代会。当齐奥塞斯库作报告时,听众起立达60次,向报告人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当我们同机回国时,谢尔比茨基在飞机上对我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参加过这次代表大会后心情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有种感觉,觉得离开他往回飞的时候,浑身上下好像都沾满了臭狗屎!”
所以他在街上看到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才叹气。
就这样,又一个觊觎政权、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人民的魔鬼,从瓶子里被放了出来—那就是把乌克兰从苏联分裂出去,为班杰拉分子恢复名誉的路线。
“鲁赫”正式登记之后,各式各样的政党和运动有如魔鬼,纷纷出笼,它们无一例外,全是现存制度的反对派。不过,当时它们还只是刚刚在基辅知识界和乌克兰西部各州诞生。
虽然“鲁赫”也极力想在国内的工业区和农业高度发达的东部地区建立分部和支部,但对冶金工人、矿工,还有普通的庄稼人而言,他们的许多口号都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鲁赫分子决定对“莫斯科佬”的堡垒进行“改造”。成千上万“自由”“独立”的“鼓动家”打着纪念扎波罗什哥萨克500周年的口号,乘坐火车和汽车,涌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什州、赫尔松州的城市和乡村,为首的便是“鲁赫”领导人。
这些身穿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制服的不速之客搞了上千人的游行,他们手举神幡,还有这里从未见过的班杰拉、舒赫维奇、彼得留拉的肖像,唱着民族主义赞歌,闹得老百姓莫名其妙地问:这都是些什么人?干嘛跑到这里来?闹到最后,群众大会也好,“结盟会见”也好,所有的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村里的人更干脆,把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全赶跑了。
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乌克兰东部的人似乎对西部人说的话听不太懂:这种话倒也似乎也是本族语,可就是里头有不少词,不少短语和重音,都是乌克兰西部被奥匈帝国和贵族制波兰占领的一百来年中从国外传入的。顺便说一句,当你看到乌克兰电视时便会发现,现在的乌克兰语同科沃罗达、舍甫琴柯、科秋宾斯基、贡恰尔、特奇纳、奥列伊尼克等这些公认的文学巨匠的语言已经有了多大的不同。
而且还不得不承认,在东部,“班杰拉分子”一词始终都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词。上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由当地向西部地区派出了数万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无党派人士,去建立村苏维埃、集体农庄、民警机构,去当教师和医生。其中成千上万的人受尽折磨,躺在棺材里被运回了自己原来的城市或乡村。从那时开始,乌克兰所有的政治事件中,便出现了公开或不公开的反抗的影子。遗憾的是,煽起反目、号召从莫斯科“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脱离苏联(请看,这一切不是都被戈尔巴乔夫自作多情、引以为荣的多元论证实了吗?),先取得经济独立,继而是政治独立——所有这一切,均未被苏联宪法、已经通过的各项法令和刑法所制止。地方各级党委警告说,局势发展下去非常危险,但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却认为这是对改革怠工,是危言耸听,等等。
政治不稳定,破坏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人们又本着“越糟越好”的原则行事,展开了目标明确的行动,造成经济状况逐渐恶化。在此背景下,社会上的蛊惑宣传便被相当广泛的群众所接受。
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筹备期间和大选期间。此前,反对所谓“各种特权”和反对把意见强加给公众的斗争已经具有广泛规模(众所周知,这里少不了叶利钦的功劳),而享受特权的全是“党的机关干部”。这里还要加上戈尔巴乔夫的一个著名的提议,即“你们自下而上地整他们,我们自上而下地整他们”。党的基层干部是为党干活的马儿,可是区委也好,市委也好,都被认为是改革的怠工者。先是《真理报》,接下来由于有雅科夫列夫撑腰,又有《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文化报》等(此前它们从来没有对党组织唱过反调),开始向所有的干部展开攻击,说他们“怀念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中央广场上和体育场上举行了成千上万个要求州委下台的群众大会,这股风席卷了乌克兰的许多州。那些由于仇恨变得野兽般凶狠的民族主义者在集会上发表演说,使听众如醉如狂。如果有人发表几句正确看法,疯狂的群众便会有节奏地高喊“格季广(打倒!);“甘巴—甘巴—甘巴”!(可耻!可耻!可耻!)。请看,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多元化!
共和国内出现的局势本来就够严重的了,可还有更加火上浇油的事:中央各报的特派记者接到指示,凡有状告州委书记的材料,都作为急件处理,发在头版头条。材料只要一发表,再辩解也是白搭。看来谢尔比茨基算是看透了这种“民主大潮”,所以不得不提前退休。
苏共中央在选举前夕为“鲁赫分子”提供了一张有力的王牌——通过决定提高党的机关干部的工资,甚至还公布了新的工资额。顺便说一句,我是政治局里少数反对提高工资的委员之一。尽管提出要政府也这样做,但我拒绝给苏联部长会议下属机关涨工资。
这样,在短时间内,党的干部不得不停止日常琐细的工作,放下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泡在没完没了的群众大会上,为解决罢工问题而烦心。
大家知道,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是头一次以差额的办法进行的选举。反共的候选人不仅得到地方上的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还为乌克兰印制了“揭露”党政干部们的宣传画、标语口号、传单。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还可以从为数众多的境外民族主义中心得到源源不断涌入的物资。
在乌克兰各民族主义机构团体组织框架内建立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加拿大基金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全力促进乌克兰“非殖民化”,促进乌克兰脱离苏联。比如,1990年,多伦多成立了“援助乌克兰慈善基金会”、乌克兰—加拿大“救助乌克兰”基金会,著名的“鲁赫”领导人乔尔诺维尔、戈伦、卢基扬年科等都是理事会成员。在艾尔伯塔大学乌克兰艺术学院加拿大研究所名下,挂靠了一个所谓的“援助乌克兰科学发展永久基金会”,其目的是为“乌克兰新一代领导人”进修提供资金。这一时期还建立了加拿大“人民运动(鲁赫)拥护者协会”,下设13个分部。
民族主义报纸《胜利之路》1990年12月份报道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其组织成员和同情者以及前乌克兰起义军军人……对乌克兰主张独立的力量提供支持,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还列举了这一“援助”的某些数字:“仅1989年,便为乌克兰各种事件和斗争的需要拨出近40万美元,其中为采购必需的技术手段拨出5万余美元,为同乌克兰爱国主义人士保持定期联系拨出15万余美元……为直接帮助乌克兰个别活动家和组织拨出近5万美元。”
为数众多的反对派运动和政党都从其他一些国家取得经费的支持。慕尼黑出版的“德国乌克兰侨民中央代表处”简报(1990年第 2期)就报道过为乌克兰个别“护法人员”筹集“捐款”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无人对这些事情保密了。比如所谓的“救助乌克兰”这个乌克兰加拿大基金会在《新路》报上(1990年11月3日)便报道过“捐款”的消息,从1千到100万美元都有,在结尾处又补充道:“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共和国出现的这一局势,使我们可以公开从事旨在使我们祖国摆脱莫斯科,获得经济、文化、政治独立的活动”。不管是苏联和乌克兰的内务部,还是克格勃,均未制止此类粗暴干涉内政的活动。
获得这些组织和美国类似组织资助的,主要是“鲁赫”、乌克兰共和党,还有其他一些反对运动,以及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等地新成立的地方机构。
中央电视台组织了一些地方电视的专场实况转播节目,对那些最卖力气的“斗士”——人民代表候选人——提供支持。事实上他们所有的人在当选为代表之后,都参加了“跨地区代表组合”,成为瓦解“帝国”的热心领路人。不论是在全苏电视台,还是在共和国电视台,他们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