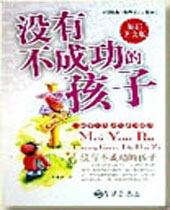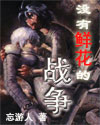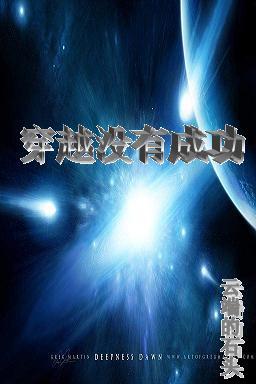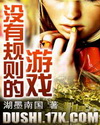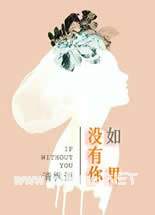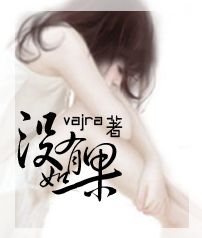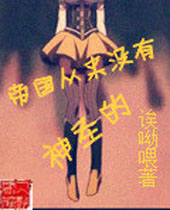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论文章。
前不久,我与一位朋友合拍的短片《明天》,获得了“三星”数码专题片优秀奖。这个短片还被推荐参加纽约短片节,最近,我们已得到了入围通知。
最近,我又构思了一个短片,正在筹备拍摄。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荒诞的故事。一位疲惫的男人,推开一扇熟悉的门,他发现那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他又推开了一扇熟悉的门,发现仍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他执著地推开一扇又一扇熟悉的门,最后发现自己站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大街上。我是想通过这个片子说点什么。其实我们的生活常常充满了这种荒诞。比如说,我苦读了12年就是为了能考上大学,可是进了大学后却发现,那不是我想像的大学,我走进了一个让我陌生的莫名其妙的地方。
这一年,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可是却过得充实和快乐,每一次创作的过程都是一次神秘的游历,充满了探索、困惑和喜悦。那天,父亲笑着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其实,在这22年的人生中,我最欣赏的也是这一年里的自己。
说到这里,小路舒心地笑了。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3)
窗外,风已经停了,一缕夕阳正奋力穿过云层,似乎要给这个灰蒙蒙的下午抹一笔亮色。
小路说他的朋友里,有不少是像他一样逃出大学的。他说前不久那个跟他一起逃出大学的S君到北京来了,他带着S君几乎跑遍了北京城里所有的音像店,S君喜滋滋地买了一大堆CD、VCD,直到兜里只剩下返程的车票钱才罢手。临走时,S君对他说:“我也许不会成功,但是我很快乐,这就足够了。”
我送小路出门时,他告诉我,他正在法语培训中心学习法语。他说:“我想去欧洲学习电影摄影或电影导演,但是我一定会回来,因为,我想拍的东西是中国的。”当我在“服从调剂”一栏上签字后,我就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利与王姗见面的那天,太阳像个火球挂在天上,空气燥热得彷佛一点就着。路边的树上,那些往日爱扯着嗓子嘶叫的蝉儿也热得失了声。
我和王姗相约在学院路附近的一家酒吧见面。
这次见面缘于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我为何逃出大学》,在那篇文章里,我讲述了小路的故事。稿子见报的当天我就接到了十几个电话,他们中,有在校的大学生,也有已走出大学的年轻人。有向我诉说不喜欢所学专业的苦恼和茫然无措的彷徨,有的向我抱怨大学里生活乏味、教材乏味、教师乏味。也有的向我打听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年轻人的电话及通信地址,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勇敢者,做出了他们想作而不敢作的选择,走了一条他们想走而不敢走的路。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不断接到类似的电话,并收到了一摞来自四面八方的信。
王姗没有给我打电话,她的信也姗姗来迟。收到她写给我的信时,距离发表那篇文章已经一个多月了。那是一封字迹娟秀的信。信很简短,却一下抓住了我的心: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提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
在世人眼里,在父母和亲友的眼里,我是一个幸运儿,我考上了我一直希望考上的这所名牌大学。可是两年来,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痛苦中,因为我不喜欢我现在所学的专业,一点也不喜欢。开始,我也想培养自己对这门专业的兴趣,希望自己能喜欢上它,结果发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每天仍必须面对这些令我憎恶的面孔:一本本教材和讲这些教材的老师。痛苦中,我选择了逃课,选择了沉沦,选择了玩世不恭,可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总在向我呼唤,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我知道,如果这样下去,我也许连文凭也拿不到,即使拿到了文凭,走出大学校园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又如何在社会立足?写到这里,我的心又沉入了黑暗……
我很佩服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大学生,我也曾无数次地想逃出去,但是面对父母期望的目光,面对校园外那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我缺乏像他那样的勇气和胆量。我正站在十字路口,很迷茫,也很恐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后面的两年时间如何度过。
给您写信,我并没有期望能得到您的回信,我只是想倾诉,因为我心里实在太压抑,太痛苦。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告诉您吧,就是想当一名像您那样的记者。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看这封信。
我的呼机号是:191××××××××苦恼的叶子
第二天,我试着拨出了那个呼机号,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没想到一会儿她就给我来电话了:“您好,我是叶子。”“叶子,我看了你的信,知道你很苦恼,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
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后说:“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您要写文章,请不要写我们学校的名字好吗?”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正准备放下电话,她说:“我不叫叶子,我叫王姗。”
见面地点是王姗定的,那里离她学校不远。当我裹着一股热浪走进那间酒吧时,发现靠窗的一张小桌旁已坐着一位女孩儿,虽然她背对着门,但我猜想那一定就是王姗了。我径直走到那张小桌旁。女孩儿站起来笑了笑,说:“您是吴老师吧,我是王姗。”
面前的王姗,高挑个儿,肤色白皙,细眯眯的眼睛,笑起来像一弯月亮,很温柔,很妩媚。可是那天下午,我只见她笑过一次。
我们的交谈开始有点滞涩,后来才渐渐流畅起来———在父母眼里,我是个乖女孩儿。因为从小到大,我几乎没让他们操过心。上小学时,我是老师宠爱、同学羡慕嫉妒的好学生,小学毕业那年,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招生,我轻轻松松地就考上了。
那时,我的理想是多彩的,也是多变的。上初一时认为医生救死扶伤很伟大,穿上白大褂也很神气,便想当医生。初二那年迷上了刘德华,成了追星族,又想做一夜成名的歌星。
初三时,读了夏绿蒂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便一心想当作家。一直到高一下学期我的理想才算定型。
那个学期开学不久,班上组织了一次班会,题目是“新闻幕后的故事”,前来讲故事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女记者。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她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更是让我激动不已。我喜欢那种每天都有激情撞击的生活,喜欢那种具有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我讨厌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更讨厌死水一潭的生活。如果说过去的我,理想是孩子气的,是模糊的、摇摆不定的,那么,那天下午,那位女记者就像一支火把,照亮了我理想的隧道,我第一次严肃地思考理想和未来这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热爱的是什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在那天下午,我将做一名记者的理想装进了心里。参加高考那年,我所在的省实行考前填报志愿。有人说高考靠实力,填志愿靠运气,因为即使考出了高分,如果志愿没填好,兴许也会落榜。每年都会有一些因志愿没填好而落榜的倒霉蛋为此而痛不欲生。所以,也有人说填报志愿是赌博,敢赌的人,要么赢得莫名其妙,要么输得精光。就好比扔手中的骰子,抛出去是六点还是一点,全凭运气。说到这里,王姗一脸苦笑。
考后填报志愿,仍有如此大的风险,考前填报志愿,风险就更大了。我们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15日~16日。那两天,父亲、母亲和我将1996年~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省招生录取统计资料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报考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大学。这是一所我心仪已久的大学,它的新闻专业也是在全国叫得响的。
我之所以敢报这所竞争性很强的大学,是因为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在那所重点中学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前20名。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新闻,后面几个志愿分别是汉语言文学、社会学等。总之,都是文科类专业。志愿表上,有“是否愿意服从调剂”一栏。我犹豫了,久久不敢下笔。因为在此之前,我听到了太多的带有悲剧性的故事。不喜欢学地理的被调剂到地理专业,不喜欢学数学的进了数学系,喜欢学生物的被调剂到机械制造系,喜欢法学专业的被调剂去学中国革命史。可是我父亲坚持认为,应填上“愿意服从调剂”,应该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这样就会多一份被录取的希望。他说,假如你前几个志愿都未被录取,如果不愿服从调剂,你的档案也许马上就会被抛给第二批院校,这就等于你与重点大学无缘。
父亲的话不无道理,可是我仍很犹豫。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是16日下午6点。6点钟,在向老师交志愿表的最后一刻,我咬咬牙填上了“愿意服从调剂”几个字。那时我心存侥幸,觉得那倒霉的事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可是没想到,这种倒霉的事还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是7月24日,当查分热线报出我的成绩是615分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虽然我的成绩比第一批文科重点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几十分,但是我所报考的这所大学在省里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却一直徘徊在610分左右。8月18日,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取我的学校正是我填报的学校。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马上就跌入了失望的深渊,因为我看到在录取专业一行写着:图书馆系。我的头一下就大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录取我的怎么会是图书馆系?虽然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我也曾作过种种不好的假设,比如,如果不被新闻系录取,也许会去中文系;如果中文系不被录取,也许会去社会学系;可是从就没想到过会去与我的爱好风马牛不相及的图书馆系。这时我才痛心疾首地认识到,我填写了“服从调剂”,就等于交出了自己的意愿,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填写了“服从调剂”,就不得不接受任人摆布的命运。我的心被一种深深的失望笼罩着。当我的老师、同学和亲友兴奋地向我表示祝贺时,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父亲和母亲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也知道我想当一名记者,所以接到录取通知后他们也有一点遗憾,但是他们仍然很兴奋、很激动,因为他们的女儿考上的毕竟是一所令许多人都羡慕不已的重点大学。
父母他们看重的也许是面子,是我给他们带来的骄傲,因为人们问起来,总会说“你女儿考进了哪所大学?”却很少有人问“学什么专业”,何况,图书馆专业和新闻专业也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兴趣、你的爱好,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理想。在千军万马仍在挤独木桥的现实中,能考上大学已是幸运了,能考上重点大学就更是幸运中的幸运。当大多数人还在以能上大学为第一目标时,个人的兴趣、爱好、理想便成了一种很奢侈的东西。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扼杀了多少人的梦想,埋没了多少人的兴趣和爱好啊!
拿到录取通知书虽然很失望,但是那时候,我仍抱有一丝幻想,因为我听别人说,有些学校允许学生入学后调换专业。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四处向人打听转系的事。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虽然学校允许学生转系,但却有严格的规定,最关键的一条是,你想去的那个系具有扩容的空间。那一年,是大学实行扩大招生的第一年,全国招生计划一下就增加了30万,在校舍、教师、学生宿舍基本都没增加的情况下,一下就多招进了30万大学生,几乎每所学校都喊挤。新闻系的招生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计划数,由于招生人数多于往年,已经没有扩容空间。转系的希望破灭了,我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我甚至后悔不该来报到,后悔没有回校复读第二年再考。但是,如果我真的不来报到,真的回校复读,一定会有不少人说我有病,考上了重点大学不去上,而要回校复读,说什么他们也不能理解。
也许是我在电话中无意间透露了我的消沉和失望,父亲给我写来了长长的信,满纸的担忧和勉励。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一定要学一行爱一行,他告诉我,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既然现实已经无法改变,我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像父亲告诫的那样,学一行爱一行。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4)
在中学,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帜在前方不远处高高地飘扬着。每当我在茫茫题海里游得累了、困了,我就会抬头看看那面旗帜,它像一剂解乏治困的药,让我又重新兴奋起来,拼命地游起来。每当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狱般的生活时,我就会看看那面旗帜,它让我有了忍耐的勇气和力量。
可是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我记得进大学后的第一节课是政治课。那位头发已经有点花白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得唇干舌燥,并在黑板上写满了板书,可是我看见教室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觉和看别的书,可老师似乎没看见,他目中无人地自说自听。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位老师也许认为讲课是他的一项任务,他只是将他应该讲的内容讲完,至于学生愿不愿听,在不在听,他并不在乎。这样的政治课听得索然无味。后来,每次上政治课我都带一本书去看,有时是小说,有时是随便抓到手的一本杂志。进了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这里与中学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还是在搞应试教育那一套,教师还是满堂灌,学生还是埋头刷刷地记笔记,考试还是考背功,谁能背,谁就能得高分。
前不久,我在西单图书大